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讲稿《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下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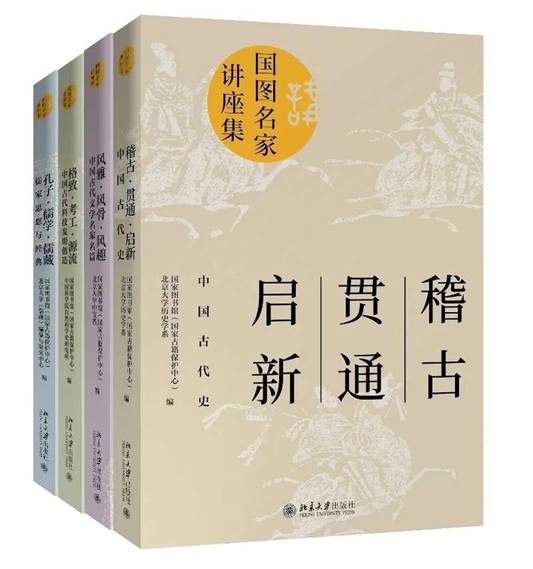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三、《儒藏》的编纂
先说历史上关于《儒藏》的思考以及《儒藏》立项的情况。《儒藏》显然是把儒家经典都汇总起来成为“藏”。有《佛藏》,有《道藏》,像《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所以现在编《儒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种把儒家经典汇编到一起的传统。刚才我们讲“十三经注疏”系统发展的脉络就可以看出来,几代传下来,慢慢汇编到一起。中国有这个传统,这样一种惯性。而《儒藏》呢,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孙羽侯,他希望能够“囊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明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四《孙鹏初遂初堂集序》)。所以,首先提出“儒藏”这个名字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孙羽侯。
到了明末,曹学佺提出,“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清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五“儒藏”条) “吾儒无藏,可乎?”这是一种观念,一种传统观念。当然有的人不太吃这套,说这很可笑,释道有藏,儒就必须有藏?
到清代还有一个周永年,撰写了《儒藏说》。据学者们考证,后来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可能是受到了《儒藏说》的影响。当然,没有他提出的这一些,《四库全书》的编纂可能也还会进行,但是我想至少给皇帝提了醒。这样有明代的人,也有清代的学者提出,最后乾隆皇帝没有完全采纳编《儒藏》,而是编《四库全书》,这中间既有他们认为的提出编《儒藏》的必要性,肯定编《儒藏》这个观念,也有他们不编《儒藏》而编《四库全书》的一些思考。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内在陈云同志的关怀下,在中共中央1981 年37 号文件的号召下,深入开展了古籍整理工作。“佛藏”有《中华大藏经》的初编和续编。而“道藏”,也有好几家出版社找人整理,最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华道藏》。
相形之下,儒家的经典怎么办?其实儒家经典多年来一直在整理,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比较窄一点的儒家经典,比如“十三经注疏”系统、“四书五经”系统等等。其实儒家的经典涵盖在各个部类中,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窄的部类。甚至许多文章,别集类里面某一家的文集,都有不少儒家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很难区分。有些诗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当然你说有些诗人,比如苏轼,他的诗到底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有的说得清,有的说不清。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是无孔而不入的。所以从八十年代,佛、道两“藏”开始整理,也给了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一种压力。
到了九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提出来要编《儒藏》。到了2002 年,北京大学接受汤先生的建议,组织了一个班子来着手编纂《儒藏》。2003年,教育部批准《儒藏》作为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这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和认识过程。目前《儒藏》的分类体系,采取的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就是《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同时《儒藏》的编纂团队对四部的经典、典籍又有所取舍,着重选择的是经部、子部的儒家类的著作。刚才介绍的其他部类的著作也有所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更严格一些。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关于《儒藏》的思考以及《儒藏》立项的情况。
第二个小问题,关于目前《儒藏》的进展,实际上是“精华编”的编纂。
因为《儒藏》启动以后,先编“精华编”,再做《儒藏》的全编,或者叫所谓“大全本”。“精华编”包括了中国部分和域外部分。中国部分收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传世典籍的下限定在了清朝结束,也就是1911年以前,出土文献是包括了简帛文献与敦煌纸质的文献,这样加起来有五百多种,编为283册,这是中国部分。域外部分,所谓域外,是包括韩、日、越南三国,他们在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我们选了150多种,分编为57册。这样加起来是340册,2.3亿字。这是《儒藏》的“精华编”,不是全部的《儒藏》。目前说的这个数字,因为它还没有最后全部出版,所以最后也可能会有一点调整。
《儒藏》(精华编),是由北京大学的学者牵头,联合了国内外50多家合作单位400多位学者共同进行的,是一个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合作项目。目前的进展,《儒藏》(精华编)的稿件已经全部交稿了,就是点校完成了。“精华编”采取的整理方式是,选择一个好的底本,有校本,有参校本,然后在底本的基础上标点、校勘。目前稿件全部交稿了,而且绝大多数完成了通审工作。也就是初稿完成以后,校点者点校完了,要送到《儒藏》的编纂团队来,这个团队要审稿。审稿非常费力,反反复复,有时候稿件不合格的,再退给点校者来修改。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很费时间,非常烦琐。目前绝大多数完成了通审的工作,已经出版见书的是160 册。a 刚才前面讲了340 册,是《儒藏》(精华编)的目前估计的全部,目前出的是203 册,另外还有近40 册,计划是在2019年出版,剩余部分也尽快完成。可以说,《儒藏》(精华编)的编纂目前已经到了收官的阶段。
刚才提到,《儒藏》(精华编)采用的是加标点、校勘、竖排、繁体的形式。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经过反复讨论,多次商量,最后才确定下来的。既要考虑到将来方便读者的阅读使用,也要考虑到和文献的数字化接轨,做成电子版。这就是目前《儒藏》编纂的具体情况。
关键是,在这些年编纂《儒藏》的过程中,感觉到《儒藏》的编纂,点校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有许多《儒藏》(精华编)的内容此前一些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比如在2003 年《儒藏》立项之初,当时计划收传世文献是450 种,当时里面就有120 种是别的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的。这120 种怎么办,是用原来的已经出版的,还是另起炉灶?这个问题,从指导思想上讲,当然不一定另起炉灶,用原来的,但是要和作者商量。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原作者不在了,连家属甚至都找不到了;有的是原作者在,不愿意给你《儒藏》去出版;有的非常友好的合作,跟你合作出版,再修订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有120 种是人家出版过的,我们请原校点者也好,另起炉灶也好,都要力争超过原来的点校本。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别的出版社也在做。比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儒藏》这个本子出版好几年以后,中华书局又新出了一个整理本。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华书局后出的,是不是后出转精呢?还是我们原来的更好呢?要有个比较。所以在校点之初,就力争做到最好。还有一个例子,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整理本,我们是后出的,是在原来的中华书局整理本的基础上又加工的,应该说是吸收了中华书局原来点校者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但是中华书局又推出了新整理本,正好我们《儒藏》的这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现在还在出版的最后阶段,我们也准备吸收新整理本的内容。这种情况就是促使我们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吸收别人的长处。
我具体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儒藏》是怎么抓质量的。像阮元的《揅经室集》,中华书局有个整理本,是以《四部丛刊》所收的五十四卷本作底本,这个点校人可能没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底本更好,是六十三卷本,不是五十四卷本。六十三卷本是收录了阮元一直到83岁时候的作品,离阮元去世只有三年。《儒藏》就是以六十三卷本作为底本,就比用《四部丛刊》五十四卷本在底本上更好。
再比如,明代曹端的《曹月川先生遗书》,中华书局有整理本《曹端集》,校点的人大概没有注意到有个明代的刻本。我们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一种明刻本,但是它收在了丛书部而不是在集部,原来点校的人没有用它可能是失察,没有看丛书部,以为它在集部。那我们找到了,用了这个,这也是《儒藏》在底本使用上的一个长处。这些例子,是目前进展里面《儒藏》还比较注意的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关于“全本《儒藏》”的思考。
现在做的“精华编”已经到了收官阶段了,近年在筹划《儒藏》的全本,在“精华编”基础上扩大。这个怎么做?我们有一点想法,或者说编法,提供出来。
就收书范围而言,按照“精华编”确立的分类体系,如果“全本”把这一体系的著作全部收齐,我想大概不可能,也没必要。当年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它收的书是3461 种,而《四库存目》是6793 种(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而且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它每本书的工作量,比目前的《儒藏》要小,因为它不校勘各本,不标点,还没有出版社编的各个环节,它抄了七部,北四阁南三阁。即使这样,它只收了能见到的书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作为存目。它是有选择的,主要就是看书籍的重要性。
我想编“《儒藏》全本”所面临的选择基数,首先是《四库全书》三千四百多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千五百多种,明代以前的典籍大略齐备(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清人著作)。再加上清人的著述,清人著述的总量在22 万种以上,经部的比较少,也有20404 种,其中传世的多达11729 种。我们现在“精华编”只收了五百多种,现在光是清代的传世的就一万多种,这么多的传世经学著作,再加上经部之外的,量更大。清代的,再加上清代以前的,我想,如果把这么大体量的著作都整理进“全本《儒藏》”,既很难完成,也没有必要。我想“全本《儒藏》”虽然名字叫“全本”,但一定还是一部在内容上经过精心遴选的丛书。具体选多少种书,达到多少字数规模,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认真细致地讨论和甄别。因为我们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的可能性出发,量力而行。这是就收书范围而言。
就整理方式而言,全本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一个是像“精华编”一样,慎选底本,再选定两三个有代表性的校本,经过校勘,以繁体竖排加标点、校勘的形式出版。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次性地把一本书整理得比较到位,也方便读者利用。缺点就是这个活儿很细,一定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如果全本的规模又比较大,那这个工程就旷日持久,结项也遥遥无期。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整理方式可能会节省一点时间和精力,就是选择清晰的底本进行影印,在影印件上再加简单的句读,不是详细的那种现代标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了校点环节的工作量,不需要查找原文。因为它是在原书,也就是线装书影印的基础上加句读,不用再校。当然,你一定要校,选主要的校本和参校本,在后面单出校记,也不是不可以。总之,这种整理方式会大大提高出版速度。多少年前,北大刚上了《儒藏》(精华编)不久,四川大学也在做《儒藏》。我的一个朋友,山东大学的一位老教授见了我说:“老安,四川大学做《儒藏》,比你们北大做得聪明。人家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原书基础上影印加标点,还不是句读,是加标点。你们是自己排版加标点。人家出的肯定快,抢在你们前面。”我就赶紧跟汤一介先生报告,说某位教授有这么个意见。我们说的这种办法就类似四川大学那种。但是这种整理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书的内容会受制于一个版本,读者利用起来毕竟不如排版本方便,也更不容易和电子版接轨。所以“全本《儒藏》”的做法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思考论证。
北京大学现在是下定决心来做“全本《儒藏》”,怎么做法,还需要思路更清晰,还需要从实际出发,真正地能够出成果。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儒藏》的编纂。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20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