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关键词】科大卫 明清 华南 宗族
【文章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全球客家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海斌
陈海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讲师。
在近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宗族已经成为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华南地区修祠堂、修族谱、拜祖先和拜神的盛行,宗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而其中以华南学者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在华南研究中,科大卫(David Faure)的华南宗族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科大卫的华南宗族研究,学术界先后有过相关评述。这些评述多以书评的形式对其单本著作就内容、材料和理论等进行介绍评论,而从学术史视角去讨论其宗族研究的成果,则偏重于对理论和方法的渊源、内容和影响等问题的探讨。抑或从人类学与社会史对话的视角,梳理其宗族研究的学术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及其对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超越。但既有的研究大多未注意到科氏前后研究的延续性和内在脉络,也未能清楚展示其如何推动华南宗族研究、与其他华南学者在相关研究上的共性和差异,及其研究对中国宗族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梳理,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一、“口述历史计划”与华南宗族研究的发轫
科大卫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兴趣和专长包括华南宗族、中国商业史、香港史、中国各地之地方史,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大卫对华南的研究区域主要包括香港新界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研究主题涉及宗族、民间信仰、族群、宗教仪式和商业经济等。主要成果包括:《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1986)和《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2007)两部专著,以及数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如《宗族作为一种文化的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The Lineage as a Culture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1989)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刘志伟合著,2000) 、《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2003)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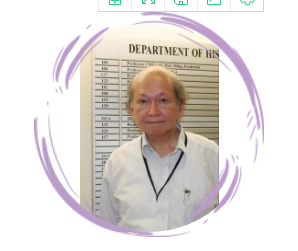
科大卫
1976年,科大卫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之后不久便认识了许舒。在许舒那里,他看到了许多香港新界的地方文献,由此开始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和研究。此外,由于70年代后期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刑科题本还未发表,而当时研究租佃问题的文献又较少,科大卫便开始意识到需要系统地收集地方文献。此后,他和陆鸿基、吴伦霓霞便组织了香港碑文抄录计划。到后来,碑文抄录计划就变成了“口述历史计划”。
这个计划开始于1979年,其出发点是“透过乡村的口述和文书资料,甚至是宗教祭拜仪式,来探求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调查的结果,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有关明清之际宗族制度在新界及邻近地区普及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传统的华南社会归化到以官僚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架构之内,亦即地区性的团体,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演变为中国社会之部分。”该计划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一书中。本书是科大卫对明清华南宗族研究的第一本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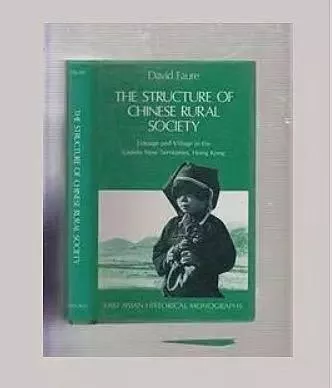
《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
本书大约在1984年写作完成,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研究香港新界地方历史的著作,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15世纪到20世纪早期,侧重于对地方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书中,作者试图揭示香港新界地区宗族与乡村之间的沉浮关系、宗族之间的联盟及其相互对抗,以及宗族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科大卫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香港新界乡村社会整体历史的发展,而非单个的宗族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科氏认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宗族作为农村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因而特别重视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中作用的研究。本书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口述历史计划”期间在新界乡村收集到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账簿和口述资料,以及政府部门留存的档案文件。
《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入住权”的概念,通过入住权来理解整个村落的历史,对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补充。科大卫认为“弗里德曼虽然提出了要区分地方氏族和高层氏族这两个概念,但是怎样区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把地缘关系弄清楚,一村一姓可以代表地方氏族,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是凭什么根据来决定某个群体是一个乡村?”“弗里德曼对我们了解宗族社会最大的启发在于区分了抽象的宗族和对财产权有控制的宗族。然而,弗里德曼既然把控产放到宗族概念的核心,不把入住权和田产分开,就无法说清楚地方宗族与高层宗族的分别。”因而,科大卫认为“入住权的概念,不是反对弗里德曼,而是补充他的论点。”
在他看来,“弗里德曼虽然区分了抽象的宗族和控制财产的宗族,并以控产机构(corporation)来表示后者。但首先,他没有发现有一类宗族是没有可以买卖的财产。小乡村里有许多宗族,这些宗族不一定拥有很多财产,但可以决定哪些人可以在这里住,哪些人不可以在这里住。其次,弗里德曼讲的,另一类是不可以买卖的,只有参加到宗族层级的概念里面,才能拿到入住的权利”。对于这两个问题,科大卫认为必须要加入“入住权”的概念才能说清楚。他在新界乡村调查问及村民们关于村落的构成时,他们常以一种模式化的程式回答:“祖先从哪里来,住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个儿子,哪个分支后裔又到了哪里,谁在、谁不在坟墓或祠堂里祭拜祖先。”由于村庄由很多的姓氏组成,且被分成很多个部分,科氏认为只有进入到宗族的历史中,才能区分谁是或谁不是宗族的成员。因为宗 族历史是村民判别和认定宗族成员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根据在村落调查访问获得的回答,科大卫对“入住权”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村民是个在乡村有入住权的人,乡村就是有入住权的人的群体。入住权是村民最重要的权利。”“入住权是指在一定疆域内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包括在乡村建房子的权利、使用废弃土地的权利、进入市集的权利、在山坡上拾柴火的权利、能够自由处置村落中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屋的权利,以及死后能够葬在乡村里的权利。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入住权,有入住权的是村民,没有入住权的居住者是不属于村子里的人,是被排斥在村落之外的。”“拥有入住权的理据是:这些权利是祖先传下来的。他们的祖先可能据说由皇帝钦赐土地,或者移居至此地而耕种这些土地,或者建造房屋而子孙居住至今,或者购买了这些土地,或者与本地人联姻,或者把原住民赶走。凭着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他们的子孙因此拥有这些土地,而且只要不搬走,就拥有入住权。这些关于历史的观念,对于村落的组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村民们正是通过追溯祖先的历史来决定谁有没有入住权、是不是村落的成员。”“由于这些权利是由迁入或继承而取得,而迁出则中止,所以防止入住权为外人所占的社群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和族谱”,而其中族谱则包括书面的族谱和口述的族谱。科大卫认为“族谱只是作为入住权的一个参考,是村民拥有和开发土地的一个凭证。然而,这个入住的历史,在没有书写记录的情况下,村民也往往可以口述出来。”此外,对于一些村落中有多个姓氏的村民来说,传说对于入住权的拥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科大卫认为“必须在领土和入住权的背景下理解宗族,而又不应把宗族视为一个仅仅为精英服务的组织,宗族的职能不只是维护士绅的地位和权利,同时也照顾到普通族人的利益。”他认为“新界乡村社会的领土观念并不依赖于宗族,宗族及其使用书面谱牒、追溯共同祖先、在祠堂祭祀祖先等各种行为,是被引介到新界的乡村中,把新界乡村联系到国家的工具。只有在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乡村社会时,宗族制度才会扩散”。新界的乡村社会之所以会采取宗族的形式主要与16-18世纪的社会形势有关。“由于宗族作为一个制度,能够保护成员免受外界的威胁、包括来自官方的威胁,因而宗族的语言被使用起来。宗族就是被视为把乡村社会组织起来的主要制度形式。”本书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新界东部乡村的宗族乃至华南的宗族都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宗族不仅是地方的团体和绅士的工具,同时也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历史变革下制度变化的产物。在对新界乡村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之后,科大卫还讨论了传说和历史、仪式与政治、民间宗教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对华南宗族及华南研究的推动
科大卫对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史研究开始于其在1988年主持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历史文化调查计划”。1991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启动,在这个研究计划中科大卫负责的研究区域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促成其此后选择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的重要因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科氏先后发表了数篇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发展的初步研究》(1987) 、《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1989) 、《佛山何以成镇?明清时期中国城乡身份的演变》(1990) 等。
《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是1987年8月应广东历史学会的邀请,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所作的学术讲演,后由陈春声整理发表于《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 。叶显恩、陈春声、刘志伟、罗一星和郑振满等学者参与讨论。在此次讲演中,科大卫从宗族的观念、珠玑巷的故事、佛山宗族的发展和宗族的经济功能四个方面阐述了对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和宗族问题的看法。对 于“宗族”问题,他认为“并非宗族的功能问题,而是宗族观念发展之时所创造的语言表述的问题。”珠玑巷的传说实际上反映出移民获得“入住权”的过程。佛山宗族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宗族发展的过程。从佛山的历史,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规律性的演变,即从以神祇祭祀为中心的地缘社会,变为以宗族和神祇祭祀同样重要的地缘社会。”“宗族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文化的发展。”这是科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明清宗族研究的初步成果,对宗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并运用“入住权”理论解释了珠玑巷传说。同时,他还将宗族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相联系起来,提出了宗族研究的新视角。
《佛山何以成镇?》则是 1989年3月17-19日在华盛顿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主要以佛山的族谱和《佛山忠义乡志》为依据,讨论了“明清时期佛山镇内的权力架构如何从里甲之下的头目演变到依靠科举考试争取社会地位的乡绅手上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士大夫成为佛山主导力量的考察,科氏认为“佛山不仅是一个经商买卖的世俗之地,也是士大夫灵感的来源地。佛山的文化不是一种纯然的城市文化,而是一种笼罩于宗族和科举考试的文化。”科氏将佛山的城市文化与宗族及科举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展现出国家制度在基层社会运作所产生的影响。
同年,科大卫又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上发表《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一文,讨论了宗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印证了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提出的“宗族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观点,并提出“明清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创造”的独特见解。科氏从文化层面去理解中国宗族,超越了以往的功能主义研究,使中国宗族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在《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刘志伟合著,2000)一文中,两位学者阐述了对华南宗族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明清以后在华南地区发展起来的所谓宗族,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制度,也不是所有中国人社会共有的制度。这种‘宗族’不是一般人类学家所谓的‘血缘群体’,宗族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先及血脉的观念。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的扩展过程。这个趋向显示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宗族的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推广他们的世界观,在地方社会建立起与国家正统拉上关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一观点几乎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族是血缘群体的社会组织”的传统说法,进而提出“明清华南宗族是历史建构的产物”的论点,并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从来就有宗族这种制度,反驳了宗族作为中国社会一种古老制度的观点,对中国宗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们还将华南宗族的意识形态基础归结为:师传和正统、文字和教化、法术和礼仪、神祇和祖先,以及科举的影响,否定了宗族的意识形态是祖先和血脉的观念。他们认为考察明清华南宗族的历史,必须超越“血缘群体”和“亲属组织”的角度,同时与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相联系,并提出“要了解宗族在社会史上的作用,归根到底,必须掌握两方面的关系--宗族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宗族所存在的不同形态和性质,这可以说是科大卫和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研究的最重要贡献。
早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的写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科大卫就已经在思考书中的这套观点在新界以外的地区是否适用的问题。《皇帝和祖宗》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在新界研究中的观点,探讨“宗族作为一种制度,如何在香港新界以外的地区演进?对于采用宗族这种组织的社区而言,宗族意味着什么?”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大卫将新界研究的论点进行检验的一次尝试。科氏进一步发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中的理论和方法。如“入住权”理论的运用、宗族和国家的联系、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和整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结合的方法等,尤其是宗族和国家联系的观点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当中可谓得到了完美的演绎。
《皇帝和祖宗》是科大卫积二十年之功所撰,可谓明清宗族研究的力作。本书旨在探讨近世中国华南地区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叙述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国家与地方社会通过整合而在地方社会建立起宗族制度,儒家思想如何逐步渗入地方社会并成为主流,地方社会如何借助正统礼仪与王朝国家进行互动。本书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就是宗族如何成为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之间联系的核心制度。作者的目标是将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放到华南的历史情境中去,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对其进行检验并超越其理论。在本书中,科大卫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作为一个制度的宗族,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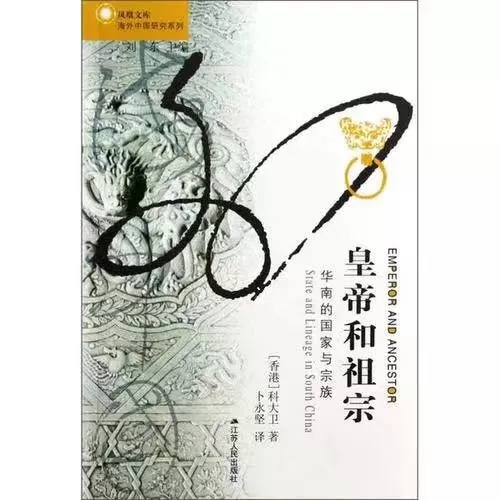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本书共有23章,分为序言、历史地理、从里甲到宗族、宗族士绅化、从明到清、十九世纪的转变、尾声。全书以历史发展过程为主轴,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尤其是佛山镇及其周边村庄。探讨了从12世纪到20世纪早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即宗族制度逐渐在地方社会确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并成为地方社会与国家联系的纽带,以及在 20世纪初期成为被批判和打倒对象的历史过程。全书展现出的是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和整合,宗族在珠江三角洲的诞生、发展和衰弱的历史图景。对此,萧凤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说,“在华南,皇帝和宗族的语言相互发明,成为适应于身份、地位、财产所有权、商业惯例、流动性和社区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大卫以丰富而多层次的研究成功地整合了这数百年来的变化。”萧氏的评论认为科大卫已经成功地建构出了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整合的过程,而事实上,科氏的研究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
本书是建立在新界乡村宗族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扩展了弗里德曼的研究,并且展现了国家的变化与宗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与以往宗族研究偏重于结构和功能不同,科大卫从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整合的过程入手,围绕着宗族制度在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历史演变,动态地展现出宗族与国家相互发明的过程。科氏对明清华南宗族的研究,超越宗族是血缘组织的概念,将视野扩展到国家的范畴,关注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研究的主轴。
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史研究延续了新界研究的方法。他收集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契约文书、商业交易合同、碑刻、族谱、日记、宗教科仪文书,以及各种口碑传说等资料。科氏将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揭示出明清时代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相互作用的权力斗争的过程。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细致梳理展现出具体的历史细节,科大卫让我们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实态。他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对于这一方法所达到的效果,萧凤霞评论道:“历史学家强调国家建构和社会融合的法律规则,而人类学家则专注于实地的仪式和日常的行为习惯。科大卫以广泛的历史包含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描绘了两者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有意识的区域建构。”从这一评论可以看出,科氏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达到了其应有的效果。
在科大卫的明清华南宗族研究中,“礼仪”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架构。在科氏看来,“宗族制度的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社会潮流与礼俗演变过程的结果。宋儒的礼仪改革因为这个潮流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功,虽然没有真正取代以神祇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但是在以神祇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之下,把祭祖的规则和士绅的活动结合起来,再加上以祖先为中心的地方管理模式,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宗族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可能是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最重要的演变之一。宗族制度的发展体现了乡村社会中以礼仪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其中牵涉到国家在礼仪上的推进作用、礼仪和宗教的分异化、由文字普及而达至的文化统一等。”“礼仪”成为科氏理解宗族制度发展和明清社会变迁的重要视窗。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礼仪”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被视为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联结的纽带。王朝国家礼仪如何进入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又如何利用礼仪进行宗族建设,以及宗族如何通过对礼仪的操弄,如修族谱、建祠堂、参与正统性神明的祭祀、巡游活动等仪式行为,拉近与王朝国家的关系。科大卫认为,礼仪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扮演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宗教和法律的结合往往是透过礼仪表达出来的。经济的演变、赋役制度的更替、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都推动着礼仪的修改。通过礼仪的改动,中央和地方相互之间的认同得到加强。从南宋到明中叶,礼仪改革是权力交替理性化的表现。地方社会依靠接受以中央为核心的士人政权,从而延续其本身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项目申请书中,科大卫提出了“关键性的礼仪标签”的概念,其定义是“地方社会人士认为关键性的客观而可以观察的礼仪传统表现。主要包括:①称谓;②祭拜核心( 神? 祖先?);③建筑模式;④宗教传统;⑤控产合股;⑥非宗教性的社会组织。”科氏认为“这些‘礼仪标签’是历史人类学探讨历史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礼仪的实践,建立在‘正统’的概念之上。当不同的‘正统’传统碰撞的时候,就会形成礼仪的重叠”。它们“对于探讨地方历史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纵观《皇帝和祖宗》一书,这些 “关键性的礼仪标签”贯穿于其中,成为建构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整合过程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对于“礼仪标签”的概念,赵世瑜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好的切入点,并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内涵。“首先,这些‘礼仪标识’往往体现了历史上不同人群的意向,体现了各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包括国家、士大夫、地方民众、族群、宗教组织,以及传统的因素和新的因素。换句话说,集中展现了多样性与整合性的统一;其次,由于他们往往是以文化与生活表征的面目反复出现,所以比政治性或经济性事物存在得更久远,它们也往往成为地方历史的重要见证。”赵世瑜的评论阐明了“礼仪标签”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作用和影响。它是科大卫研究地方制度与国家关系的媒介,目的在于阐明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其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科大卫认为,“礼仪组织是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整合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央与边陲关系的协调,以及地方社会的重新界定,是在礼仪的转变中达成的。”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进程中,礼仪的转变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先是从北宋开始,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在这个基础上,到南宋时期,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到明代嘉靖年间,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地方社会建立起正统礼仪的过程。通过正统的礼仪,王朝国家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整合,地方社会也建立起对王朝国家的认同。
通过对莆田和珠江三角洲的比较研究,科大卫发现国家与地方的礼仪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很不一样。“在莆田,宋朝国家给地方的承认在于透过对地方神祇的封敕,在珠江三角洲,明朝给地方的承认在于地方人士有权力以祖先的功名为据建立‘家庙’形式的祠堂。”“家庙”式的祠堂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这种祠堂把祭祖的重心从坟墓迁移到乡村的中间, 成为一种很明显的建筑标志。其二,建立和维持这种祠堂配合地方合法控产,它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合股机构。其三,从明中期到清中叶,这种建筑和附带的家族模型有明显的改变。明中叶还代表达官贵人地位的建筑物,到清中叶在珠江三角洲随处可见。这个过程代表上层社会习俗的往下移,人口的往上流动。”科氏通过对作为宗族象征的建筑物的变化,即从墓祭到祠祭的礼仪转变,说明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变化。
对于理解宗族在明中期到清中叶的功能,它何以成为维系社会和推进经济的制度,科氏认为“必须要和礼仪的运作联系起来,了解礼仪在同一时期的发展。而要了解礼仪的变化,除了研究礼仪变化的历史材料和文献记载的礼仪程式外,还必须考察地方社会象征的演变。”在他看来,“华南的所谓大族,并不只是通过修族谱、控族产,更通过张扬的家族礼仪来维系。作为家族礼仪的中心,就是后 来人们一般称为‘祠堂’,在明代制度上称为‘家庙’的建筑物。对家庙成为地方社会建筑象征过程的考察,对于进行明代以后宗族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华南研究发展的过程中,科大卫还广泛地参与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当中。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主持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大陆学者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赵世瑜等都受邀参与。会议的主题是“以福建省福州地区、莆田地区和广东省潮州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围绕各地历史上的宗族和庙宇,探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个会议被视为“华南学派”的正式形成。同年,科氏与萧凤霞合编《植根乡土:华南的地缘》(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总结了当时很多人的研究。对于书名的选择,科氏认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把地域关系放到主体上,另一方面是强调把文献和田野研究结合起来才是‘脚踏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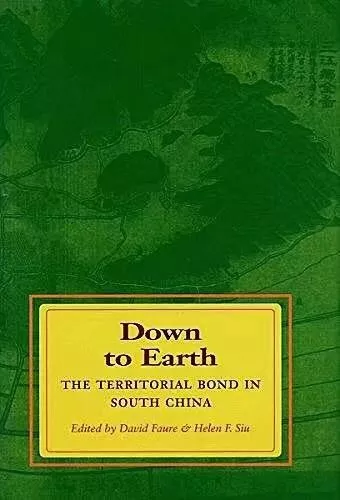
《植根乡土:华南的地缘》
2001年3月,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并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华南研究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此,科大卫与华南研究群体便被学术界贴上了“历史人类学”的标签,历史人类学也被认为是代表了华南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该中心还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历史人类学学刊》,由科大卫担任主编,到目前为止共发行16卷31期。从2003年暑期开始,中山大学每年举办一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科大卫都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2006年,以科大卫为代表的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重新定义西江:明清时期的国家建构与地方社会的演变”的研究。该研究计划的目的在于试图重建具有地方特殊性的礼仪与社会变化的时间脉络
《历史人类学学刊》是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半年刊,创办于2003年,每年4月与10月定期在香港出版。本刊发表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的论文,以及对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研究著作的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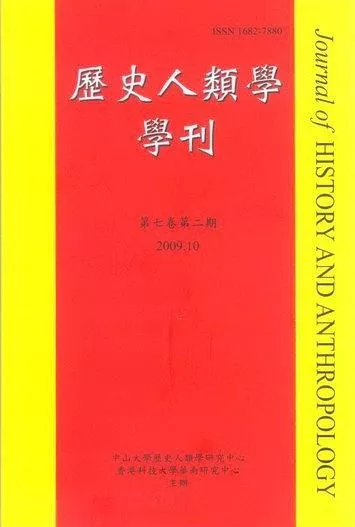
《历史人类学学刊》是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半年刊,创办于2003年,每年4月与10月定期在香港出版。本刊发表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的论文,以及对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研究著作的书评。
2010年,香港“卓越学科领域”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资助,由科大卫担任总主持人。该项目计划“以历史文献与田野研究为依据,复原各地参与大一统的历史。”“试图通过区域的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与时空特征。”同年1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举行揭幕典礼并签署合作协议,由科氏任研究中心主任。他表示“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开展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的研究项目,并在广泛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积累中国社会的研究资料,探讨关于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科大卫的带领下,课题组将研究区域从华南扩展到了西南和华北,实现了其在《告别华南研究》中所提出的“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到华北和云南、贵州去,以验证通论是否经得起考验” 的目标。
在三十多年来华南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推进,还是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等方面,科大卫都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成为华南研究的领军学者。也就是在这一长期合作研究和相互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科氏引领和推动着华南研究的发展。
三、从科大卫看华南研究范式的得失
科大卫三十多年来的华南宗族研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他始终立足于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结合的方法,将“礼仪标签”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架构,关注地方社会历史的变迁、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强调从地方社会出发理解国家,将宗族置于明清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宗族的语言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笔者以为这便是科大卫华南宗族研究范式的内涵,而这一范式的形成则是与华南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密切关联的。
科大卫的华南宗族研究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但在与其他华南学者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诸多共同的理念。如对华南宗族形态和性质的认识,科大卫和刘志伟认为“明清华南宗族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先及血脉的观念。”他们还提出“应当将宗族放在礼仪和意识形态里面去理解”的观点。尤其是在研究范式上,包括科大卫在内的华南学者对于明清宗族和社会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架构下展开,注重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关系,而这一范式也成为华南研究运用最为普遍的分析架构。
然而,由于科大卫与其他华南学者学术出身的不同,又导致了各自之间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差异。从学术渊源来看,科大卫更多地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而刘志伟和郑振满的宗族研究则从一开始便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重视王朝典章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呈现出鲜明的制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特色。在学术思想方面,科大卫与刘志伟、郑振满对于“礼仪”和“意识形态”看法的差异便明显地表现出受学术渊源的影响。科大卫对于礼仪的理解是从西方社会的思想出发,通过中国历史的研究,最后明白要理解礼仪,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法律。刘志伟和郑振满则主要从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出发,注重礼仪由上而下庶民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如郑振满提出“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观点,便是将宗族制度的形成放在宋以后宗法制度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来解释。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科大卫深受华德英“意识模型”理论的影响,而刘志伟在此之外,重视意识形态还有一个渊源便是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
不过,科大卫与其他华南学者的华南宗族研究,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以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其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便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分析架构。它是科大卫与华南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族与社会时所普遍运用的分析模式。不可否认,这一模式确实为华南宗族及中国社会研究建立起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体系。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其所存在的缺陷。人类学者杜靖在检讨这一分析架构后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他认为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并提出超越这一分析模式可以尝试的路径是“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杜靖的这一看法可谓非常敏锐,他在政治和经济的范畴之外,看到了宗族的文化属性和内涵,超越了功能论的束缚,同时还提出了宗族研究的新路径。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分析架构,成为包括华南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分析模式。但是,当这一分析架构被普遍运用到华南宗族及华南研究时,便呈现出模式化和结构化的特点。在科大卫与其他华南学者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同一种历史叙述,即地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宗族、士绅、民间信仰及其他社会组织等成为地方社会与国家交流的平台,在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皇帝和祖宗》便是运用这一分析架构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典范,为我们展现出宗族、士绅等地方社会力量如何成为联结国家的纽带,进而促成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及整合。这样一种既定的模式造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便是地方社会都是主动地进入王朝国家体系当中,而忽视了地方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实际上,地方社会也存在着消极和被动的一面,也有逃避统治的可能性。如斯科特对东南亚山地的研究便表明山民并不想被纳入国家的统治,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这一研究范式,遮蔽了地方社会的自主性,强调的只是国家制度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和地方社会的接受过程,而没有突显出地方社会对制度拒绝接受的过程。
对于科大卫华南宗族研究的贡献,乔素玲、黄国信在《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一文中给予了高度的称赞。作者认为“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并认为“中国宗族研究发生了从社会人类学向社会历史学的转向”。对于乔、黄的这一观点,杜靖则表示质疑并进行了反驳。
首先,对于“入住权”的问题,科大卫的基本观点是:“只要是被确认为是宗族的成员,便拥有入住权。”杜靖则从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梳理了“入住权”理论的学术渊源,认为“入住权”并非宗族所独具,就村落层面也成立,只要是一个村落内的成员,就拥有入住权。入住权问题首先应该追溯到里弗斯和梅因,因为他们都讨论到了一个人如何在村落内获得产权的问题,指出“入住权”理论并非科大卫的发明。杜靖将入住权问题放在村落的层面进行讨论,突破了宗族的限制,为解释那些不属于宗族或没有宗族的人仍然拥有入住权提供了依据,补充了科大卫的论点。
其次,对于乔、黄一文所提出的学科转向问题,杜靖指出:“科大卫等社会史学家对功能论的宗族研究确实有所超越,功不可没,但若从理论的新锐性和进展考虑,说宗族研究从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发生‘转向’(除非是从研究成果数量和从业人员规模上去理解) ,上述说法值得商榷。另外,弗里德曼一人不代表整个社会人类学。弗里德曼之后,不论是中国的人类学还是西方的人类学,在关于中国宗族问题上,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而且就理论范式来说,也更换了好几个理论模型了。”杜靖充分肯定了科大卫等社会史学家对功能论的超越,却并不赞成乔、黄所说的中国宗族研究由此发生了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学科转向,并从中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反驳。
本文赞同乔、黄和杜靖对科大卫超越功能主义论点的论述。正是由于科大卫提出“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创造”的论点,中国宗族研究才突破了长期以来功能论的束缚,实现了宗族研究范式的转变。至于学科转向的问题,乔、黄一文主要是从研究方法转换的视角所作出的结论,而杜靖则主要从人类学史的视角梳理中国宗族研究范式的转变,指出科大卫及华南学者等历史学家只是借鉴了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进而认为并不存在乔、黄所说的学科转向。乔、黄一文所提出的学科转向问题,虽然值得商榷,却也表明中国宗族研究已经在学科和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历史学和人类学出现了汇流的趋势,而这也表明中国宗族研究的路径得到了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