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人们对全球化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有了很多认识,时间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新大陆发现以后的世界体系的运转,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来自世界市场的白银大量流进中国。明代后期从各种渠道流进中国的白银数量,很多学者的估算出入很大,我想大约在一万万两上下的规模。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学者主要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做了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认为,16世纪这些白银流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更深层的还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过的两个问题入手:第一,中国社会如此强的白银吸纳力是怎样产生的?第二,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何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两点,在王国斌先生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提出的:
(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期、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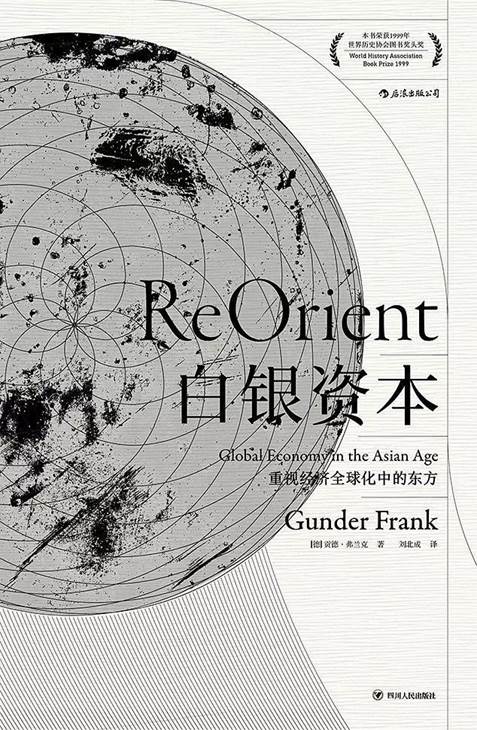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后浪出版公司出版)
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对白银的“无限渴求”,全汉昇教授很早就引用过一位长期在菲律宾传教的教土的话,其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白银流入中国就被禁锢在那里,如同一个永恒的监狱(The kingdom of China is the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and w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world’s treasury, sincethe silver is imprisoned there, and is given an eternal prison)。
在世界上已知的各民族中,中国人着实是最渴望取得银子和最爱好银子的一个民族。他们把银子当做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来抱有它,因为他们甚至输出黄金来换取白银,也在所不惜(They are the most greedy for and affectioned to silver of any raceknown. Theyhold it in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they withdraw the gold from their owncountry in order to lock up the silver therein)。明代中国对白银的这种“无限渴求”,与其具有如此强的白银吸纳能力,实际上是同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当做一个问题来思考,引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吸收那么多的白银的容纳空间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了解的是,王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性质上是一个“食货体制”,这个体制是由“赋入贡棐,懋迁有无”构成的,而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事役均”。这个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对我们认识中国王朝时期社会结构至为关键,但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只能指出,这样一个体制,内在地以货币流通为贡赋经济和国家管治的运作手段。明朝立国时,以画地为牢的里甲赋役制度和缺乏相应金融制度的大明宝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行政体制,不到几十年就破绽百出,随之开始了一个以追求“事役均”为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过程。
这个转变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的发展。这里也许需要特别指出的,学界有一个大家以为是常识性的说法,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其实是不对的。一条鞭法是一个从明宣德正统年间开始、自下而上的变革过程。一条鞭法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系形成的转型过程。所谓国家或社会的转型,具体而言,就是王朝国家怎样去控制社会中的人,王朝统治格局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组织方式。

刘志伟教授
要在这十多分钟内讲清楚白银在明代国家与社会转型中的角色是不太现实的,这里只能尝试简单概括地说明。
在刚才说的王朝汲取财富资源的非财政性方式下,明朝各级政府运作的资源,主要来自差役(人力和物力)征调,而差役征调的体制是建立在一个以家户为单位的承当差役的社会组织系统(里甲)之上的,各级政府根据这个体系中各个家户的人丁事产多寡(即是承当能力的大小)征调和派办人力和物质。根据“事役均”的原则(朱元璋具体表述为“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大户负担重,小户负担轻,其轻重的差距不是按比例派,而是以类似累进的方式,重者赔累或至倾家,轻者或悠游免役。
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第一是由于户的规模尽可能减小,可以让赋役负担最小化,因此,作为差役供应单位的户的规模,总是趋向于以小家庭为单位立户;第二是政府与编户齐民的关系,通过户籍体系直接控制家户中的个人;第三是负担的轻重,即不可预算,也难以做到均平合理;第四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开支来源,是一种无定额的推派,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这些特点造成了第五,社会上大量的人口,脱离国家统治体系,以无籍之徒的社会身份存在;而这样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第六,明朝国家的统治模式和社会秩序发生动摇,而中央各衙门和各地的地方官员陆续采用各种变通的方法来获得行政资源。
各级衙门采用的办法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借助可以预算定额和可以按比例摊征的一般等价物作为计算和支付的手段,取代原来的无定额、无比例的索取,而这种手段最有效也最能够被接受的就是白银货币。这样一来,明朝立国建立的体制下,国家政治与行政运行的资源,大部分都来自非财政性的机制,即差役征调,到明代中期,这种资源汲取的机制,转变为越来越依赖用白银货币作为核算和支付手段,来达到“事役均”的社会管治目标,结果是非财政性的差役转变为货币化、定额化的比例赋税化的财政性收入。
由于原来通过差役获取社会资源的规模相当巨大,由差役转化形成的财政性货币收入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随着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和收支的手段,构成明代国家库藏的主要形式,形成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我粗略估算,明代中后期由原来的各种征派改折形成的白银财政规模大约为1500—2000万两左右,加上同时带动起来的田赋折银,白银财政的规模估计达到3000万两的规模。如果我们估算当时最大宗的商品运销规模一般都在百万两级的规模,就可以知道这种财政性的货币流通,是非常巨大的。这种以贡赋体制主导的货币需求,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商品交换与流通,是中国市场吸纳大量白银的秘密所在。
白银成为赋役缴纳手段后,改变了整个赋税财政体系的运作机制。明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要的白银,更多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发挥职能,而是作为支付手段,被用于处理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白银确实被广泛应用,但流通的结果是白银大量流入权力运作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通就不必然伴随着市场发育,甚至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当然,长期来看,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进入政府资源运用领域,最终还是一定会拉动市场的扩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白银为运作手段的国家与依赖控制关系来运作的帝国是不一样的,国家权力与老百姓的关系以及整体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转变。
所以,在我的理解上,白银流通的意义就不是主要在市场和商业领域体现出来,而是体现在社会和国家结构层面。此前帝国运转的资源是以国家权力对具体人户的控制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控制又不是国家基层政权州县对民众个人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里甲制实现的。纳银之后,老百姓与州县的关系转变成为类似纳税人和现代国家的关系,国家可以不控制具体实在的家户,而通过控制一个纳税账户来实现,这就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各种中介力量的空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和组织的新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代替里甲制度,新的赋役摊派征发的组织和机制成为必要、成为可能,并有可能普遍化起来。
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国家控制加强或者削弱来描述这个变化,这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的结构性转型,王朝国家跟乡村基层社会、跟一般的编户齐民老百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它不可能不控制人,当它控制不了的时候,白银的运用使它实现控制的时候,可以靠社会上的中间这一层力量。正因为国家有了这个转变,乡村就可以自治,就可以有所谓的自治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治化不是国家的削弱,而是国家的转型。如果没有自治化,王朝国家就会失控。从明代中期到清初,我们似乎看到国家有些失控。但实际上,社会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在失控的同时,它总有一些办法使得控制能够再度建立。问题是,这个再建立的方式,不是政府再去抓里甲户应卯听差,而是在乡村中大量出现了各种中介的力量,宗族或士绅什么的,去控制地方的秩序,保证国家运作的资源获取与调动,使得地方秩序可以按照国家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去运行。
这里面当然会有无数冲突,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来看,例如五百年这样的时段来看,其实是几个不同的结构一直在或者缓慢地或者激烈地发生变化,变出了一个新的结构,变出一个我们看到的,在清代至迟到雍正、乾隆以后成型的那样一个社会。嘉道以后的动乱,是在这个结构下面的动乱,它跟明代的动乱完全不一样。明代的动乱是以逃户的方式来表现,它针对的是政府对个人、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体制,一直到李自成都还是,李自成的口号就是“不纳粮,不当差”。但清代嘉道以后叛乱,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背后还有宗教等因素,不再见以抗拒“纳粮当差”为口号的了,这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从明到清,无论是从国家形态、地方社会组织还是动乱,你都可以看出社会的转型。
这样一种格局,简单地概括的话,可以在弗兰克所说的“全球性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这句话之后,再加多一句:“中华帝国的社会转型和国家的新运转机制,是用主要来自世界市场的白银来驱动的。”
本文选自刘志伟教授著作《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