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主导中国史学界数十年的史学形态,其影响超越了史学领域,重要性自不待言。实际上,即便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其深层思维方式可能也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展开客观理性的探讨,寻绎其深层学术意蕴,具有不可轻忽的学术意义。目前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仍不够充分,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体现其研究深度与创新意识,是亟须面对的难题。 一
近年来,概念史研究通过国内学者的译介,引入中国学界。一些中国学者结合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更契合中国近代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陆续形成了“知识考古”、重要政治术语之考察、“历史文化语义学”“新名词研究”、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各具特色的研究路数。概念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在理论方法探索上颇有创获,其领地亦不断拓展。
对马克思主义术语概念的研究,始于德国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所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这一研究取向在中国学界产生回响,近十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的个案研究渐趋丰富,也有学者将概念史的治学取径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领域。《近代史研究》于2018年推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史”专栏,对“封建”“唯物史观”“帝国主义”等关涉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概念加以考辨。这些研究多注重从革命理论建构的角度来梳理概念之演变,对于揭示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书写中的意涵仍显着力不够。
笔者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也是具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兼具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概念、文本、语境、思想、意识形态等概念史研究最核心的要素都沉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史学著述,也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素材。概念史研究并无固定模式,在坚持概念史研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研究旨趣不必强求一致,不妨各有取舍侧重,不拘一格。若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切入,将考察的视角聚焦于史家对这些概念的认知以及史学研究与历史书写实践中对这些概念如何运用,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便会浮现。这一研究取向既可以探析概念的思想意涵与历史脉络,亦可考察不同史家学术思想之特点,动态把握同一史家思想与学术的变化轨迹,探究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寻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把握概念所辐射的社会历史面相,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历史叙事总是通过概念得以呈现,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民族”“阶级”(次级概念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斗争”等并非有形的抽象概念,其聚合了与历史相关的重要信息,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理论的关键概念,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体系、解释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石和骨架。若没有这些概念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将会是另一番模样。对于这些概念,学界以往多从其翻译传播中的移植与嬗变来探讨,或从政治史角度阐发其含义,若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视域下,将概念置诸历史研究实践,深入梳理分析史家对这些概念的接受、认知、争论、运用之缘起与流变,并结合20世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实践,审视概念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密切关联,则可拓展研究视野,使研究摆脱平面化而趋于立体,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样态有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还须看到,这一研究取向之意义并不局限于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密切相关。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重要概念的研究,也有必要深入考察史家对这些概念如何理解和运用,这样才能对概念本身有动态而深入的解析和透视。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界定,无疑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命题。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获得较多认同,后经毛泽东在其论著中进一步阐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遂成定论。李泽厚在1986年提出质疑,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此后不少学者纷纷参与讨论,但一直众说纷纭。讨论者着眼于单纯的学理分析,都难以说服对方,且难以提出取而代之的概念。笔者以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论证,与其着眼于“循名责实”进行本体论意义的学理辨析,不如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场域,细致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渊源与衍化,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此概念的接受、理解与运用,如此则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此概念的认识,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正本清源的效果。桑兵就指出,“循名责实”的概念史研究取径存在局限,近代不少经由翻译而来的概念,在不同的语文系统当中各有其因缘社会历史文化而来的名与实,“一旦被翻译转用,便发生以此之名应彼之实的转折,这样跨文化转移的名实,本来就很难完全对应”,“所谓循名责实,大体心中自有一是……所以,应当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要以概念勾连历史”。[9]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方能避免师心自用,亦可将研究落到历史叙事的实处,将抽象概念还原为历史,避免纯理论讨论的空疏之弊。
对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具有较明确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概念,以往研究者多从经典论述出发进行理论探讨,或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而不予深究。若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角着眼,这些概念均大有探讨的余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亦非铁板一块,存在相当热烈的争论。进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历史具体问题认识之分歧,往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之分歧。例如对于“生产工具”这个理论概念,史家的认知就有微妙差异。
根据《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的解释,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工具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标志着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也是区分各个经济时代的标志。马克思曾形象地把它比喻为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说它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经典作家均重视对生产工具的考察。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强调:“人类经济的发展却依他的工具的发展为前提。大抵在人类只知道利用石器或用青铜器的时候,他的产业是只能限于渔猎和牧畜,他所能加工于自然物的力量只能有这一点。当时的社会便是由动物般的群居生活进化到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他认定周初因铁器的使用而使农业得以发达,堪称“产业革命”,并由此导致殷周之际由原始共产制转变为奴隶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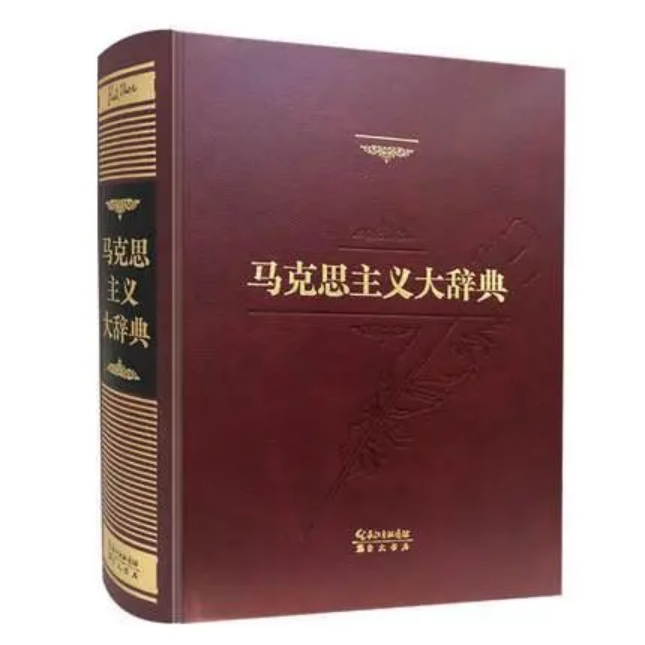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图源:网络)
范文澜在1940年撰写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强调:“人是制造工具的,而新工具之制造,又必须依靠前一辈人所已有的成就,逐渐改善,才有可能。”他不认同将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形态变化的关键标志,表示不能认为“殷代还没有发见铁,所以殷代决不会是奴隶社会”。1949年后他对生产工具之认识进一步明确。1950年初,他在所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明确提出:“人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里当然不是说生产工具不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力占更重要的地位。”在1953年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他强调指出:“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最重要的因素。”1953年,范文澜撰文进一步申说:封建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生产力得以前进,铜器和铁器,固然不必过于拘泥,甚至使用残存的石器,也不妨碍封建制的发生”。他因要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自然更强调构成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人的作用,“如果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这就难免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衡的自行发展”。范文澜对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认知与解读,被吴大琨尖锐批评为忽视生产工具的变更而单独强调“人”的因素,与斯大林之论断不符。范文澜并不服气,1957年他撰写《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进一步申论:“劳动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生产力”,劳动者是否具有“劳动积极性、自动性、热情、兴趣”,“劳动组织的守旧或革新”,劳动者是否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革命要求”更能决定生产力的强弱。范文澜的这些看法,坚持其以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因素之认识且有所发挥,但仍力图将生产工具、劳动者与生产力的关系讲得圆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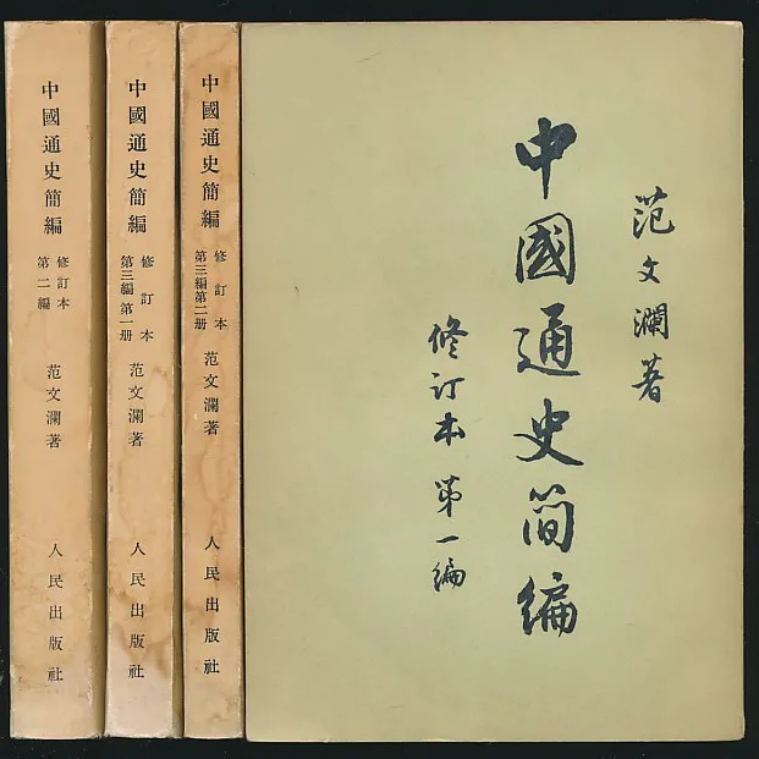
《中国通史简编》(图源:网络)
梳理史家对关键概念的认知与运用,可以揭示其史学思想,也可透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据李新回忆,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中国通史简编》隋唐部分时,利用描写隋炀帝的骄奢以“史谏”“大跃进”。李新此说影响颇广,可能未必确切。范文澜究竟是否“史谏”,难有定论。但从前文梳理范文澜对“生产工具”概念之认知与运用,可以看出其思想倾向与当时的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内在契合之处。范文澜对“生产工具”的认知,亦是其历史著述中对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浓墨重彩而相对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刘大年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批评曰:“全文看不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总起来是没有社会经济”,“不能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在于其总能呼应时代关切,与时代共振,因而对其史学实践的概念研究,亦有必要结合社会政治变迁以把握概念的历史语境,梳理其渊源流变。如“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概念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观”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对“阶级斗争”概念的研究已然相当丰富,但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史家“阶级斗争”观念的源起流变以及不同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如何认知和运用“阶级斗争”概念,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总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接受、认知“阶级斗争”的概念,并运用此概念进行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李大钊等人于五四时期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当时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尚较浅显,李大钊还试图以“互助论”调和“阶级竞争说”。“斗争”与“合作”可谓“阶级斗争”的两翼。30年代后,随着现实政治中阶级斗争趋于激烈,马克思主义史家进行历史研究时的阶级观念逐渐强化。这一强化过程亦受到现实政治革命理论之影响。毛泽东在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具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其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得以不断激化。但随着日本侵略加剧,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趋于平缓。虽然仍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但“阶级合作”的一面——统一战线——在政治实践中亦体现出其价值。革命斗争实践与革命理论,自然影响到史家的史学研究,但这种影响并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史家将革命领袖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也有一个过程,且由于当时对史学并非强制规约,史家对阶级斗争的认知与运用自然亦非整齐划一,而是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个性。对此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分析,可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性的体认。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现实政治的阶级斗争应该说趋于缓和,但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趋于强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一言说,将阶级斗争提升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仍紧绷阶级斗争之弦,“阶级斗争”也成为历史书写的核心概念。中国近代史领域“三次革命高潮”诠释体系高度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尤其强调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这也是其在当时背景下能获得各方认同的重要原因。1958年“史学革命”后,“阶级斗争”理论愈益强化,“史学革命”中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亦即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内容,“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
但即使在突出“阶级斗争”的时代氛围之下,不同史家对“阶级斗争”的认知和运用仍存在差异。1960年代史学界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争论颇具声势,至1965年初,国内报刊就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发表的文章有30余篇。对于此次争论,《历史研究》曾对一些著名史家进行调查,不少学者仍持保留态度。邓广铭认为:“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讨论来讨论去越弄越玄。”邵循正认为:“关于史学界前些时候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并未得到解决。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并未结合实际进行讨论,而是专在概念上作文章。如果想把这个讨论搞好,首先就要结合实际,否则越讨论越空,没有什么结果。”贺昌群直言:这些争论“有些近于诡辩”。汪篯回复:“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讨论应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出发,应提高到理论上探讨,不要停留在名词和概念上打圈子,概念化的讨论是大家都不欢迎的。”概言之,学者普遍认为60年代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争失之空洞、概念化。
我们今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自须不局限于单纯的理论概念,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现实政治中的阶级斗争形势、政治领袖的论断如何影响史家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认知,史家如何将“阶级斗争”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若对比分析范文澜与胡绳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即可发现二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微妙差异。范文澜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超越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上的“最主要的矛盾”,对人物史事的评价以民族大义为最高标准,因而对统治阶级内部反抗列强侵略的人物给予较高评价;而胡绳则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着力强调列强与中国统治者相互勾结,在以阶级分敌我的思维定式之下,统治者阵营内即使如曾纪泽、左宗棠等反侵略人物亦皆在贬斥之列。以往研究者惯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分析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并将其分别与共产党、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联系对应,看似简单明了,实则可能似是而非。莫若从“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切入,以揭示“革命”叙事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相当强的革命性,研究历史同时也是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与革命形势和现实政治可谓息息相关。尤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进而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塑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转型”。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旨趣,不仅在于回顾所来之径,梳理前辈史家所思所虑,反思史学发展历程,察其得失之由,也在于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思想与学术资源。
将概念史这一学术工具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从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实践来考察、辨析概念,分析史家运用概念的种种考量,实际上可谓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史研究。这种研究取径,以解析概念为支点进行贯通整合,打破以往以单个史家史著为中心的史学史研究范式,拓展了研究范围与视野。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些关键概念的认知与运用,往往因时而变,因此对之进行研究须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静态分析,有必要回到彼时的时空语境,通过梳理其源起流变的脉络加以动态把握。
中国历史学近年提出以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笔者认为,构建史学体系还须从概念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键概念的梳理解析,无疑是前期基础工作。历经百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至今仍然保持相当强的解释力与活力,仍在今日的历史叙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有一些史学概念如今受到质疑。对于受到质疑的概念之研究,须避免以今律古的后见之明,力求了解之同情。相对于本体论意义的纯粹“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取向更侧重于对概念作认识论层面的探讨,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的多重面相。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2021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