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作者庾向芳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
中国近现代史学
试论北大国学门内阁大库档案整理
的成就与不足
庾向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摘 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这四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风范,为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北大国学门作为最早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学术机构,在整理档案过程中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档案整理;
我国现代专业史学机构的设置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下简称国学门)始,国学门的成立是近代史学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北大国学门诞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主义”思潮盛行之时,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潮流中,为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国学门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以下简称内阁档案)的整理与公布,是受近代科学观念影响最为直接且成就最突出者,同时国学门整理内阁档案的工作,也为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国学门是第一个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学术机构,在整理档案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遗憾和不足,因此,其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重视。
壹 确立科学的史料观
“任何科学或学科都包括材料与理论二者的统一。历史事实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而无可更改,但历史学(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却必然不断地在更新。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原来的史料就被转化为新史料并给予新的诠释而获得新的意义。”虽然我国古代史学有重视搜集、整理史料的传统,但是对于史料的概念和范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对史料与史学著作的区分都不够严格。因此,学者们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认识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新旧学者存在巨大差异,实为传统史料观向近代史料观转变的显著标志,也是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特征。
20世纪初,内阁大库档案随着“八千麻袋”事件进入公众视线。这批档案在教育部存放多时,传统学者只注意夹在其中的宋版书。如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于是派人试行整理。宋版书“只要能够找出书册一本,便会现钱交易,立时赏以铜元四十大枚。其余的乱纸,自然,也就视同废纸了。”这是当时部分传统学者对于档案价值的典型认识。他们认为书本文献高于一切,注重宋版图籍,对于档案的史料价值大多认识不足。
北大国学门学者多有留洋背景,学贯中西,他们对于档案的价值认识,充分体现了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一代学人在历史观与史料观上与传统学者迥异的旨趣。他们认为这些与传统文字记载不同的资料,犹如科学家面对自然界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明末及内阁档案,如奏本,謄黄,报销册,试卷……,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此外,档案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校勘旧史,为学者开辟新的研究理路。他们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概括国学门的研究工作“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习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材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也成为促进民国学术发展的直接因素。顾颉刚认为民国时期学术进步的“泉源固不止一端,而最重要的则为直接史料的发现和利用……清代档案的保存,这是近代直接史料的大本营。”
国学门学者对于档案史料价值的高度重视,来自于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胡适认为“西洋近百年史学大进步,大半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并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上。故要建设中国的现代史学,必须首先推进方法的科学化。在“科学”大旗的号召下,国学门学者提出要在平等的治学理念下对待一切的学术,扩展学术研究的范围。1923年胡适在被称为“新国学研究大纲”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学门的研究方向是“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认为“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因此当“八千麻袋”事件出现之后,国学门学者将收集整理内阁档案视为突破传统学术藩篱,走向外拓展之路的重要契机,“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在广搜材料,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并强烈要求学部将“八千麻袋”之外剩余的档案拨给北大保存与整理。
此外,国学门学者重视档案史料的价值,还源自民国初年学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20世纪初期,欧美、日本学者凭借从中国流失的大量珍贵文物,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有些领域甚至领先中国。这给民国学人以强烈的冲击。沈兼士曾经说:“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敦煌石窟之秘籍发见于外人后,法、英、日本,均极重视,搜藏甚夥,且大多整理就绪;中国京师图书馆虽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余剩之耳;又如英人莫利逊文库,就中搜藏中国史学上贵重之材料极多,中国亦无相当机构主持收买,遂为日人岩崎氏所得;近闻已嘱托东京帝国文学部整理研究,不久当有报告公布。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因此,当内阁档案“八千麻袋”事件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学术界纷纷谴责北京政府倒卖档案。内阁档案的去向成为国学门同仁关心的焦点,“当民国十一年余方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闻罗叔言斥赀赎内阁大库档案,有慨于心,因与马叔平、陈援庵、朱逷先诸君共谋以其劫余归于研究所,此为学术机关整理档案之嚆矢”。这部分内阁档案经过蔡元培、陈垣等人共同努力,最终使北京政府教育部接受了北大的请求,于1922年5月运到北京大学。“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得教育部指令许可;校长乃嘱托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单不庵、杨栋林诸教员前往历史博物馆办理接受事宜。此项档案,自明迄清之题本、报销册、揭帖、贺表、謄黄、金榜、起居注、实录……等均在其中。共计装运六十二木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这些内阁大库档案运到北大之后,拉开了近代学术机构整理研究档案的序幕,也为近代档案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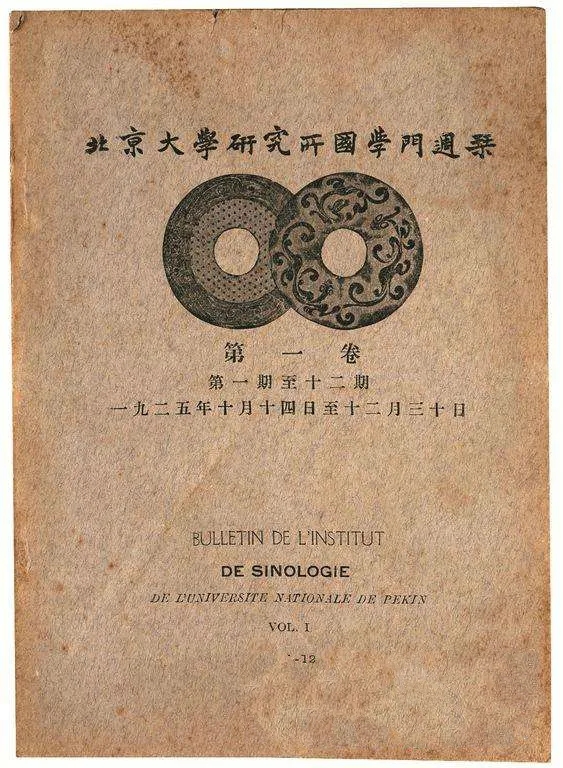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贰 首开学术研究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范式
中国传统史家虽然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来承担,因此当学术界面对“国史之整理,与本国地理之裁订”这类需要大规模协作才能完成的学术项目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成立专门学术机构的迫切性。罗振玉在整理内阁档案时,对以一己之力整理档案的无奈体会深刻,“检理之事,以近数月为比例,十夫之力约十年当可竟。顾检查须旷宅,就理者需部署庋置,均非建专馆不可。顾以前称贷既皆吾力,将何从突兀见此屋耶?即幸一二年间此屋告成,天假我年俾得竟清厘之事;典守、传布,又将于谁望之?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国学门的成立,开启了以学术机构为单位的研究范式,对于推动近代学术沿着科学化专业化道路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在整理内阁档案的工作中,国学门首开学术机构的集体工作范式,并且第一次尝试为内阁档案整理编目。
从成立初期,国学门就将“整理旧学”作为宗旨。为了整理内阁档案,国学门特别在1922年5月成立了内阁大库整理档案会(后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专门负责整理及研究内阁档案。国学门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教职员“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单不庵、杨栋林、沈士远、马裕藻、陈汉章、李泰棻、胡鸣盛、滕统音、刘绍陵、刘澄清,及毕业生王光玮,在校学生连荫元、魏建功、张步武、潘傅林、傅汝林、魏江枫、陈友揆……等富有整理档案之兴趣者,组织一整理档案会;于七月四日着手整理。”
大规模的档案整理,在中国古代并无成法可以借鉴。因此内阁档案整理的方法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关于档案整理方法的确定,再次显示出学术机构群策群力的优势。整理档案会汇集当时北京大学文、史、哲等文科系别的学者,经过讨论,制定出中国档案史上有记录可查的第一次科学的整理方案,整个整理工作依照三步展开:“第一步手续为分类及区别年代;第二步手续为编号摘由;第三步手续为报告整理成绩,研究考证各重要事件,及分别编制统计表。”在此基础上,作为国学门导师、档案整理会主席的陈垣,总结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的经验,提出了档案整理八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这八法是近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奠基性理论,是国学门及此后参与整理内阁档案各学术机构的指导方针。
国学门的档案整理工作从开始就显示出学术机构集众工作的优势,不论整理方法的确定、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还是整理结果的公布出版,都比罗振玉依个人力量整理档案有了很大的进步。罗振玉也一度与北大国学门建立联系,并参观了北大国学门的整理工作。“对于本校整理方法,颇为赞许。并由本会商准罗先生以后将私人购得之八千麻袋整理所得之目录,抄送本校一份。”
整理档案会仅仅通过三个月的工作就已经成果斐然,“自七月四日起以迄九月三十日,先后摘编謄黄、题本、报销册、金榜……等类已近万件。其中发现要件不少……除以上诸件外,可作史书重要考证者,尚不下百种。现拟于本校二十五年成立纪念日,将暑假期内整理之成绩,分类陈列,开第一次展览会,以供留心史学者之研究。”北大庆祝成立25周年内阁档案的首次展出,受到了参观者的称赞,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内阁档案的兴趣。到1924年,整理档案会已经厘清了这部分档案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全部档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要件,一部分是报销册。并对所有的档案进行过一次估计,把档案分成九种,每一种下面都有约数,共五十二万三千二百余件又六百余册。
国学门对内阁档案的整理贯彻了科学化、专业化的集众式整理方式,实为整理内阁档案的一大创举,这种研究工作的范式影响了此后包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等几乎所有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学术机构。正是有这些学术机构的共同努力,才使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得以基本保存。在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当中,国学门对内阁档案整理和研究的成绩,充分显示出了学术研究一旦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后,其传播与成长的速度确有革命性的变化。
叁 档案整理与公布并行
中国古代学者视稀有文献为“古董”的观念,造成了他们将藏书秘不示人的狭隘的学术作风。国学门的学者受到西方学界重视档案史料思想熏陶,对图书馆、档案馆都有充分了解,因此他们普遍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蔡元培主张著史与保档相结合,他认为“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愈益重视,而保存编目各方法,亦日渐精密。于是,故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认为整理档案的目的,一是要更好地保管档案,二是公布于世,用于学术研究。他介绍国外的经验“欧美国家,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而外交部档案慎重保存,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此不但有助于国民外交常识之普及,抑且供给历史学家以多量正确之史料。”
因此在整理档案工作开始之初,国学门就秉承档案资料应对外开放、供学者共同利用的观念,将一面整理一面公布作为整理准则。“国学门搜集整理之各种材料,完全系公开的贡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利用作各种之研究,毫无畛域之私见。惟以资力限制,未能使搜集整理所得之成绩,从速出版,为憾事耳。”
整理档案会从开始整理工作起,对于“有关于历史之重要文件”一经发现,立即刊出“以供为研究史学者之参考”。1922年7月4日开始整理档案,每个星期整理档案会都将整理成果公布,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第一次公布整理结果在1922年7月22日:“兹将本校整理内阁档案等件,自本月四日起,至二十日止,所有已经分类、择由(择由另有详细之登记)编定号数者,略举各类之中枢,宣布于左”。从7月22日到9月16日,整理档案会在《北大日刊》先后公布7次档案整理结果,前五次公布的档案多为档案整理的分类及卷数,具体内容较少,第六次公布由于“发见关于历史上之重要文件,为数甚众,兹将原文摘其大概,宣布于左……”。这些档案的公布,为史学界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22年9月16日,档案开始以要件形式随时登载,不再有时间限制,到1924年,档案整理告一段落,各种档案储存于陈列室内,上架储存。陈列室有十五间,题本占五间,报销册占两间,杂件占一间,要件陈列室及要件保存室共占五间。同人一面欢迎国内外学者到所参观、研究,一面将摘录的档案目录与重要资料,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发表,然后汇编成册出版。到1926年10月16日,全部《北京大学整理内阁档案报告》刊载结束,公布了2058件档案,内容包括摘由编号的明末题行稿、清朝题本、报销册等内容。此外,《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连续登载胡鸣盛整理《清太宗圣训底稿残本》、陈垣整理《宁远堂丛录》、王光玮整理《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红本处查办应毁书目》、及明清史料整理会编《清九朝京省报销册总目导言》。
整理档案会虽然在1924年以后不再继续大规模整理活动,但是在改为明清史料整理会后,出版了部分重要史料汇编。整理档案成就以最快的速度公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档案保管机构,“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档案史料,学术界则利用档案史料从事“各种有价值的研究”。校内外学者纷纷与整理档案会合作,希望能找到珍贵史料,“胡适之先生托查康熙雍正间,关于曹氏在(江)南织造局任内各案。陈援庵先生托查清代关于天主教之案件。杨恩元先生(贵州特派来京调查收集续修贵州省志材料者)托查贵州省自乾隆六年至道光二十一年乡试题名录,并清代关于贵州一切政务之题本。”整理档案会在工作中,对于这些学者的要求尽力满足,“上列诸件,务乞请摘由之时,特别注意,一经发现,即当通知嘱托诸君雇人来会抄写。”整理档案学会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做法,开一代学术风气,为此后整理内阁档案的学术机构所延续,并推动了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

沈兼士
肆 用整理档案训练学生
内阁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因此整理内阁档案“非有多数具有兴会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整理档案会从开始工作就聚集了北大众多教师及学生,他们既可以与这些珍贵史料近距离接触,同时整理档案也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机会。由于“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曾将所发见之重要文件陈列展览,颇蒙观者之赞许。”因此“史学系的学生多数加入整理,作为实习功课。”共有52名史学系学生参加整理工作,这52名学生按照《千字文》编号,“以后各该生所整理之件,即用排定之字编列件数。”这些同学编号以后,每人每周工作二至四小时,各自认定时间到整理档案会工作。“再由助教胡鸣盛,毕业生王光玮,郭振唐,学生潘傅霖,李开先,傅汝霖……等专责照料,并摘录要件事由。教授沈兼士,朱希祖,单不庵,陈汉章,马衡,杨栋林,马裕藻,沈士远,张凤举,李革痴及导师陈垣,亦皆认定时间到会指导。”
以整理档案接触史料来训练学生,虽是一时应急之举,但是却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学生在接触档案过程中培养了对史料的兴趣,掌握了整理史料的方法,为他们从事清史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如萧一山、郑天挺都参加过史料整理工作。郑天挺曾回忆:“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整理档案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通过整理档案会的工作,很多学者积累了档案史料的整理经验,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第一批拓荒者,并且拓宽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如陈垣、沈兼士、朱希祖等。陈垣曾任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会导师,又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导师,他先后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论文,对清初的皇室与宗教做详细考证。陈垣并不专治清史,他对清史的重视应该始于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1924年清朝末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1月成立。善后委员会由政府各部部长的代表、社会名流及北大教授组成,最初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干事二十八人,大部分是北大教授。这些人中,以国学门委员及明清史料整理会成员为主体,如蒋梦麟、胡适、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陈垣、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单不庵、徐旭生、李宗侗、胡鸣盛、顾颉刚、罗庸、黄文弼等。清室善后委员会下设的“事务会”,由四位北大国学门的助教任职,分别是董作宾、魏建功、潘传霖、庄尚严,其中魏建功和潘传霖都是北大整理档案会成员。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设立专责保管明清档案史料的文献馆,沈兼士先后任副馆长、馆长,陈垣和朱希祖任导师。北大国学门的助教及学生庄尚严、朱家济、单士元、傅振伦、董作宾、魏建功、潘传霖、刘儒林等都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文献馆整理清代史料的工作与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一脉相承,北大国学门对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支持与影响巨大而深远。
伍 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工作之不足

蔡元培
北大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许多遗憾与不足,这些遗憾与不足之处,作为史料整理会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经验的一部分,同样为后来的明清史料整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也值得重视。
沈兼士先后领导过北大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是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非常精辟的总结过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的教训。他认为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的时候,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初步的形式整理上。整理档案会虽然在三年内将众多档案初步进行了整理,但是并没有完成整理档案之初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区别种类,分列朝代;第二步编号摘由,第三步内容的研究。整理档案会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对档案进行形式分类及区别年代。“严格的说,就是这第一步也未完全做到,如以各机关所属之事务分类及依地区分类等,一直还没有做到。至于第二步,实只有把明季的题行稿等摘略一番,报销册按字面的名目分了类,第三步的编纂研究统计等,则更谈不到了。”造成北大整理档案会的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主要是经费困难,“我访问沈兼士胡文玉两先生,提到这一点。据沈兼士先生说彼时经费至为困难,一切原定的计划,终不得继续做去。胡文玉先生也说,当时经费支绌到了极点,政府对于教费是一扣再扣,一折再折,结果整理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其次,在整理方法上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一些缺陷:“(一)太重形式,只知区别名称,排比时代,而忽略档案的内容。(二)只知注意档案本身,而忽略衙署职司文书手续之研究,遂使各类档案,均失掉它们的联络性。(三)过于注意搜求珍奇之史料,以资宣传,而忽略多数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整理档案会虽然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但在开始工作时,并没有科学的整理方法,因此档案本身次序和分类都很混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多年以后,郑天挺对此有很深刻总结,“过去我们在北大整理的历史档案,也有分类,但是不十分科学,有些是主观的。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当时心目中有几个对清史大概了解的问题和自己所关心的历史事件,如文字狱等,因此就照着这样来分类,不是客观地根据历史档案内容去分,而是凭一点历史知识和主观的爱好去分。也编了号,分了类。分类有的太宽,有的太细,许多分类很难划清,分错的也有,可能一个问题分入两类了。这都不是从历史档案本身来分的,主要是没有按档案科学办事。”
再次,北大是最早进行整理档案的学术机关,众多档案让参与整理工作的学者与学生都很好奇,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的好奇直接导致档案整理工作中的失误。据在北大借阅过档案的学者李光涛回忆,“这些档案经北大整理后,据我于民国二十五年暑假在北大图书馆二楼研究室借阅顺治年题本、揭帖时,查出有好多本系一全件而乃至分为多数的残件者,而且每一残件也和整件一样的登记,均各装了一个摘由的目录袋。当时我凭经验所得,将我所见的这类的残件,可以归并一期的都为之一一归并了。这事我曾经向北大研究所导师孟心史先生谈过,孟氏说这些题本、揭帖分家的原因,都是当初的一群史学系的学生干的事,因为他们对于档案都特别好奇,一经奉到学校方面令他们都来帮忙整理博物馆移来的档案,他们都一窝蜂似的参加整理,打开木箱或麻袋,大家便七手八脚的你也抢,我也抢,抢得‘不亦乐乎’,于是档案就遭殃了,往往原是一件有头有尾的本章,被扯得张也拿一段在手,李也拿一段在手,结果残件自然也就变多了。像这样的整理,真是一个大笑话了。”
沈兼士领导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继承了北大国学门的方法,同时也对北大国学门在整理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原因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都由于没有把各种档案综合的研究,深刻的观察,所以结果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内容,仅知其区别而不知贯通,仅知有若干不相连属之珍异史料,而不知统计多量平凡之材料,令人得一种整的概念,以建化腐朽为神奇之功。这样做法是不容易将档案整理出一个系统来的,档案学更是没有成立的希望。”沈兼士能够对北大国学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失误上升到档案学建立的高度,足以体现北大国学门诸学者高远的学术眼界与视野。
虽然北大整理档案会的工作有诸多失误与不足,但是并不影响他们为保存、整理内阁大库档案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学门的学者敢于开风气之先,树立了科学史料观,为此后的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特别是对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的档案整理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他们用科学的整理方法对档案进行整理与研究,这种积极探索与尝试的精神值得肯定。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不足,都对此后的清代档案整理有积极的影响。在国学门整理档案十几年后,方甦生总结国学门“为近年来整理档案的分类方法的开山之作,有几点是直到现在所不能废除的。”再次,北大国学门贡献了多位优秀的史学、档案学专门人才,为近代学术史上浩大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培养了众多后备力量,正因为有了这些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清代档案整理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与整理,直接催生了清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清史研究领域,创建了新的学科,促进了近代历史学的发展。而北大国学门则为学术界整理内阁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并且开创了史学界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为近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推动了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这种学术机构与史学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直到今天仍然对史学界有借鉴意义。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冉博文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书目文献》202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