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被誉为二十世纪近代档案史料四大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秦汉简牍以及明清档案,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与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如近年来各地简牍的出土,带动了秦汉史、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推进;中央档案如近期满文题本、满文朱批奏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对外公开,地方档案如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顺天府档案以及冕宁档案的整理出版,势必也将触发明清历史、明清法制史研究更加深入到社会中的细节。与这种社会历史研究的背景相适应,2019年7月3日-7月10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2019年明清以来地方文献与档案”研究生暑期学校。来自海内外三十余名同学,利用不同史料文献,研究明清以来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日常生活史等相关主题。授课老师来自海峡两岸,有利用家谱与族谱、碑刻资料、地方档案研究明清史,也有利用大数据,如DocSky等人文数位系统进行历史大数据分析研究的学者。不同的资料代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代表不同的眼光,这些授课内容都在不断补充参会学员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写作的想象力。
一、丰富与多元:明清以来的碑刻与档案文献
囿于笔者本文研究方向在明清法律史、明清社会史以及法律社会史的关系,讨论的中心也多以此为内容。来自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伍跃教授,是利用地方档案(主要是巴县档案)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学者。在两次报告中,伍教授从日本学者现阶段研究明清档案(主要是法制史)的宏观现状,与巴县档案所见国家权力在乡村之存在形式的微观视野切入,从远近切换的视野向学员们展示了相关研究的心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日本学界清代档案史料研究读书会的定期举办,这对促进后学研究明清史提供了较好的交流平台。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李雪梅教授,以大量“田野拓碑”的活动图片,生动地向学员展示了研究传统中国碑刻文献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在报告的过程中,李雪梅教授从碑刻自秦汉始,至明清以后的发展变迁的大视角切入,讲述了碑刻在这一历史流变中形态的变化与功能发挥的差异。这些内容意在提醒年轻学人要注意碑刻资料在研究中的作用,碑刻资料不仅可以辅助证实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亦能单独存在并具备独立证明历史事实的强大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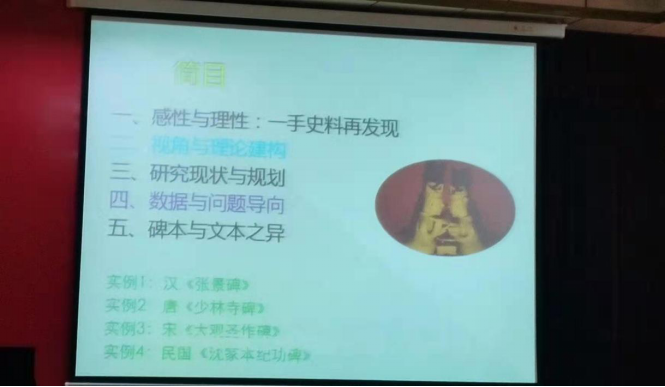
吴佩林教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向学员们报告了四十年来清代地方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通过各种统计数据与研究体会,直观地展示了明清地方档案研究在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报告的最后,吴佩林教授以《法律与社会科学》(第17辑第1卷)关于法律史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运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方法方面的总结。
此外,刘志伟教授家谱族谱的研究、项洁教授数位人文大数据的历史研究、成积春教授关于书信史料的研究、曹树基教授利用地方契约文书进行经济史的研究都是非常优秀的报告,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过多说明。
二、学科与视角:法学与史学视域下明清法律史研究的可能
本次明清以来地方文献与档案暑期学校除上述授课师资的多元丰富外,其中三个学员工作坊的报告也是加深彼此交流的另一途径。这三个工作坊依据学员报告论文的方向,主要分为法律与文书、法律与社会生活、经济史等相关议题。学员充分报告其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主题,同时对他人报告内容进行评议。这种互动的过程,通过内部自我省视与外部客观评论提高未来研究的学术品味。
笔者参与了全部论文工作坊的报告与评议交流,深感历史与法学两种学科在对待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史料资料的过程中侧重点的不同。这也引起了自我的反思。上半年在台湾交流学习时,曾与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陈惠馨教授有交流法学院同学的法制史研究与历史系同学法制史研究的差异性问题。愚以为,未来法制史研究的发展,是可能会实现法学与史学在同一学者身上实现贯通。但这一想法得到了陈惠馨教授的“批判”。她认为,法学与历史学有其各自研究的目标与旨趣,若要强求实现两者的融合,做出的研究成果只会是既非法学,亦非史学的“四不像”。在这次暑期学校工作坊参与的过程中,通过与历史系不同研究方向的同学交流后才逐渐发现,陈惠馨教授的这一认识有其道理。
因此,笔者以为法学视野与历史学视野下法制史研究,对当今年轻学子的帮助更应该是利用“两条腿”(法学、历史学)研究是基础,“各有所补、各有所长”是特色。这是基于各自学科研究的不同背景,因人而异进行的差异化发展。比如经过法学训练的法制史研究者,应在掌握历史学关于史料与史论基本理论、涉猎广泛资料的基础上,突出研究的“法学”属性;经过历史学训练的法制史研究者,则应是在熟悉了解明清以来(更甚者应是整个传统社会)法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突出研究的“史学”属性。唯有如此,基于某种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历史学研究者与法学研究者关于法制史问题的交流与讨论。
此次研究生暑期学校的主题:明清以来“地方”文献与档案。这就不得不想起另一个主题:明清以来的“中央”文献与档案。纵观现有法制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多(或是更多)则分别基于地方档案,或基于中央档案进行相关主题的研究。仅以笔者熟悉的明清法律史研究而言,有基于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顺天府档案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也要利用中央档案如内阁题本刑科档案、朱批谕旨等进行的中央层级的研究。(笔者也曾利用过中央题本刑科档案进行过研究)这种研究固然有其好处,但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如何实现真正的“动态法制史”研究的可能。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若仅观其一侧是很难看到这种动态发展变化的历程,以及不同层级官员子对待相同案件(或问题)时的司法心态。目前国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零星,研究材料的获得也较有难度,但却始终应该成为法制史动态化研究的目标,毕竟学术研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另一个法制史研究(包括社会史等历史学研究)为人诟病的问题,便是研究的碎片化。这一问题无非是有两种角度的解释:一是认为太多“零碎”问题的研究,无法实现学科内部的统一与整合。在一次会议中,某知名学者坦言“现在的学生写作论文都是喜欢小题大做,好像没有人再会考虑一些较为宏大的选题了。”即使是在外国法制史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对小题大做之“小题”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看法;二是认为学科内部实现整合的方法可以多元,很多对细节问题的研究,正如拼图一般,若将这些重要的细节问题分别研究清楚,再利用合理的理论框架或手段将其串联起来,依旧可以看清整个传统社会法制发展的“整体像”。
在阅读这些研究成果并参加暑期学校后,对这个问题又有了些新的体会。个人学术研究的路径是依赖于其长期学术研究的“习惯”。无论是做“小题”,还是“大题”,重点都是在于将作者索要研究的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而已。这是最重要的,无力也无需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尝试努力去实现对宏观议题的研究。也许是一种路径依赖,但学术研究的惯性问题确实影响着研究者学术研究取向的选择。只有适合与否,从无优劣之分。
三、代结语:一个年轻学子对明清法律史研究的期待
通过参加这次暑期学校,结合个人的研究学习经历,对于法制史在法学与历史学研究中应该如何“选择定位”进行了个人的粗浅解读。法制史也曾遭遇过两个尴尬的问题:法制史属于法学,还是史学?法制史研究究竟有何用途?其实答案有时就在“灯火阑珊处”,只是从未被发现过而已。在法制史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积淀出来优秀的学术成果,经历岁月的锤炼,留下来的便是法制史研究想要回答其功用最好的答案。
也许法学研究的同学,或是历史研究的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法制史好像有点边缘,或法制史无论在法学还是历史学研究中都是处于边缘的位置。但即便如此,也许对于法制史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去思考其是否边缘的问题,而是即使在“边缘”,那在开始便要学会思考如何生活在边缘,以及如何不去成为边缘的问题。
最后,借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教授在《史料文献与跨学科方法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的核心关键词作为结束,即中国法律史(尤其是明清法律史)研究要做到“思、全、深、新”——对史料性质认真思考、对互补性史料收集要全、对重要史料挖掘要深、对史料分析角度要新。这些期待与要求,不仅对明清地方文献与档案的研究值得思考,对利用中央层级的文献与档案更有裨益。
(杨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