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文书档案等当代显学,传统显学——金石学中的碑志,因其在坚实耐久、社会普及、跨越时空等方面较其他文献载体更具有普适性,也因而成为更经典的本土性史料。加之石刻文献兼具传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间、实体和程序并行等特色,且有千余年的厚重积累,使石刻文献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古代法律碑刻是中国本土特征鲜明的原生史料群。昭示公众、不易灭失是碑石的基本属性。法律碑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案可稽、布政施政、创制惯例、触目儆心、权力制衡等独特功能,带有标志性的额题、落款、印押等格式,以及彰显权威性和传播性的立碑地点等,均强化了其独立性。
法律碑刻史料群存在的基础,一是有可观体量,二是有丰富的族群,两者又有密切关联。法律碑刻包括六大主要类别,即公文碑、示禁碑、讼案碑、契证碑、规章碑、法律记事碑,相对形成六大史料群。每一史料群都有一定的分支,且具有相当量的规模。
法律碑刻所承载的内容,有几个特色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对秩序的追求、对规范性社会的构建,自秦汉至明清始终不绝,这个过程恰好与石刻和法律碑刻的发展同步。汉代涉及基层社会组织及其规范的《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已明确对集资购田的收益分配和继承原则,以及“他如约束”的规定。自宋代起,以碑石刻载官箴教条、御制学规、水利规章、义庄规矩、宗教规约等事例层出不穷。至明清时,由敕禁碑、官禁碑、民禁碑等构成的碑禁体系,既展示了法律规范的多层级构造及相互间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民间和官方遵从规范的共识。
二是“程序不可或缺”。无论是公文碑上的申奏批复等“过程性”内容,还是规范碑刻中的“行政授权”,都具有特殊的法律意义。公文具有申状和审批、发文和收文的双向性。对公文两端而言,发文和审批属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功能,申状和收文是确权过程,两者同等重要。而连接公文两端的过程,是公文形成、落实、反馈的完整记录,里面包含着授权、制约和监督等程序。故公文碑所铭刻的,不仅是两个端点,更是律令制度落实、委事责成的监管等过程,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法律碑刻中一再强调的“程序不可或缺”之关键所在。而一般文献载录公文多关注主体内容,首尾格式甚至程序往往被忽视。公文碑的史料完整性和实用功能,也因程序的重要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是财产权益的多样性。古代铭记财产的碑刻起步甚早,汉代建初元年(76)的《大吉买山地记》、汉安三年(144)的《宋伯望买田记》、熹平四年(175)的《郑子真宅舍残碑》、光和元年(178)的《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等,已显示出财产铭刻的重要性。唐宋以后,涉及财产权益的碑石数以千百计,形式多样,《唐许公墓志铭》详载家庭财产却被埋在地下,与同样埋在地下的石刻告身“异曲同工”,是社会观念普及的结果。明代五台山寺产碑刻中的《卷案碑》《免粮卷案碑记》《太原府代州五台县为禁约事》《各寺免粮碑》等铭刻的关键不是财产数额,而是寺庙田产能否超然于国家法律。法律碑刻中的重要类别——讼案碑,也多关涉财产权益。
法律碑刻不仅内容特色鲜明,其实体与程序、内容与格式、官方与民间兼具的形式特征,也值得称道。就单件的法律碑刻如一通公文碑而言,其特征是公文体式俱全,程序记述完整,内容具体明确,还有加载于碑额、碑阴等信息,较之被摹刻的文本原件和文集载录,史料价值更为完整、丰富。宋元明清圣旨公文也多载于史书、文集。宋徽宗“八行取士诏”见于《宋史·选举志》,但经过史臣剪裁,已殊非诏旨原文。反观大观二年(1108)《大观圣作之碑》上李时雍摹写徽宗御书《八行诏》,不仅诏旨原文俱全,且颁行、立碑程序也见载于碑。
碑石上所载诏令、敕牒不仅主体内容按原样摹刻,敬空、提行、时间等公文格式,以及署衔、印押等公文合法性要素,在碑石上多原样保留,甚有将公文封皮也依式刻石的情况,如金大安元年(1209)《谷山寺敕牒碑》首行“尚书礼部封”,为牒文封皮;从第2行“尚书礼部”至最末行“寺额付僧智崇”为牒文。加之与公文并刻的记文、时人总括碑石功能的“碑额”提示,碑刻史料的内容原生性和程序完整性,独树一帜。
更为难得的是,内容、格式、程序均完备的法律碑刻还具有群组化的特色。现所知宋金敕牒碑约200通,内容涉及寺观赐额、神祠封号赐额、加封封号、表彰赐额、改县设军等事项,其中以寺观赐额、神祠封号赐额数量最多。基于这批丰富的史料,既可看到公文的程式化特色、流变和官府行政效率,也可辨析公文文种的使用和相互关联,更可就一些行政程序特例进行分析探讨。
除敕牒碑外,还有大量刻载诏书、圣旨、敕谕、告身、榜文、执照、公据、帖文等文种的碑石。而每一种公文碑,都有其产生、流行、扩展、衰落的演进历程,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史料群组,其骨干和旁支,脉络相对清晰。
公文和私约并行,法律与行政互动,同样是法律碑刻的鲜明特征。以文书御天下的社会管理特征在秦汉碑石上已有所展现。在现存秦汉法律碑刻中,涉及社会管理的内容约占一半份额。政府行政管理方式主要通过诏书、公文。在唐宋金元时期,公文碑依然是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以文书御天下是一种行政手段,但需有制度的保障。唐、宋、明朝法律条款中都有涉及君命公文、官文书格式的内容,以及对制书传递、伪造、偷盗等方面的具体规定。
在碑石所载的司法活动中,行政程序和公文流转的内容也司空见惯。法律规章、规范的生成,御制条令的实施,也离不开行政程序的推进。无论是宋大观年间广泛刻立的御制学规碑,还是以个案形式存在的诸如熙宁三年(1070)《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政和七年(1117)《范文正公义田规矩碑》等,均可见明显的公文运作流程。
法律碑刻史料群的所呈现的形式和内容上特征,诸如公文与私约并行、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与行政互动等,以及自汉代自来日渐明晰的对规范性社会的追求,对财产权益的重视等等,仅是我们据“碑本”总括的本土传统法制的概观。而中华法制文明传统的精粹,尚需借助大量碑志做深入研究。我们编纂《叙录》的目的,便是为人们认识、利用这批珍贵的原生史料提供指引。引导我们对传统史料再发现,对传统法制再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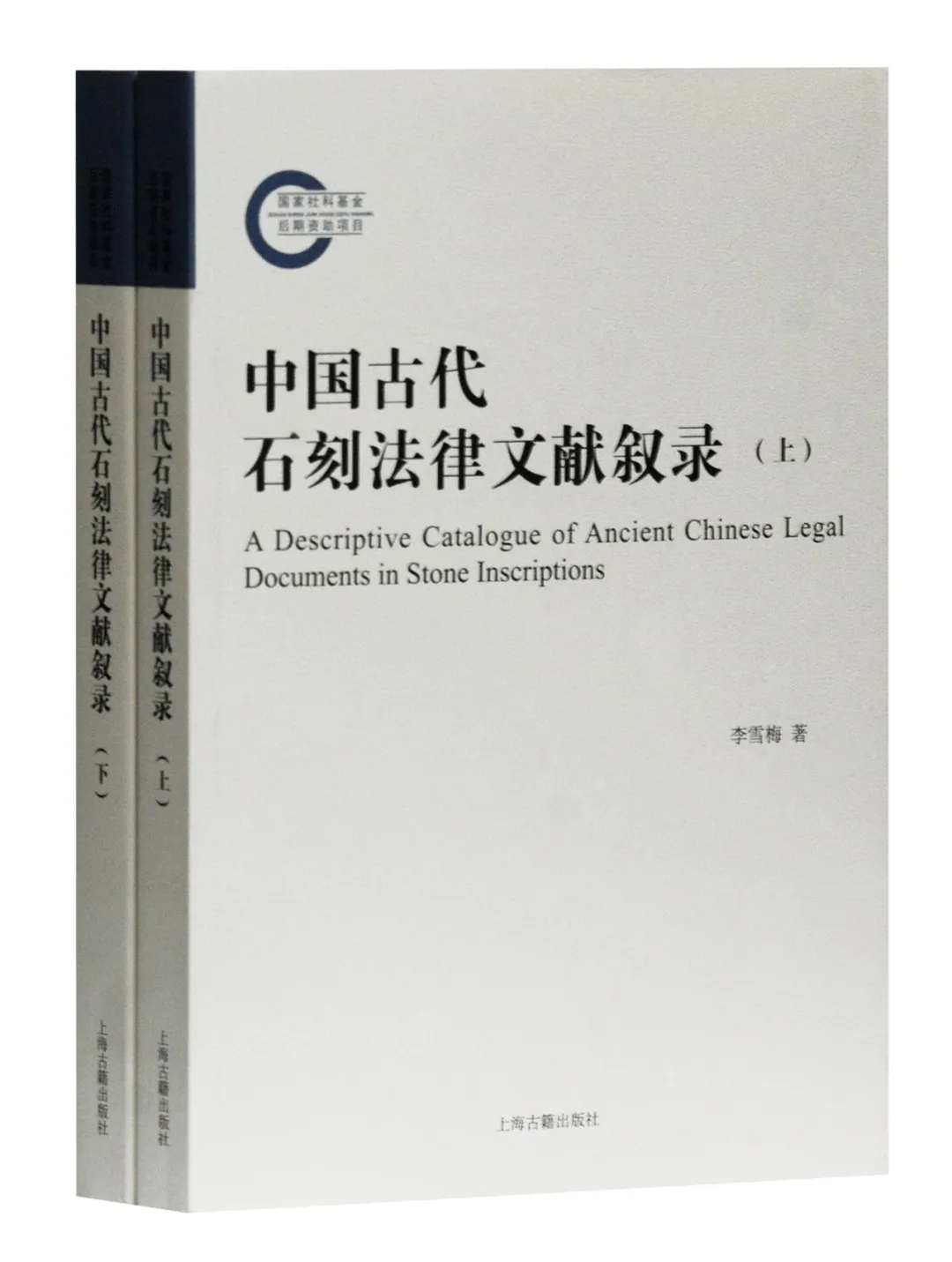
书名: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全二册)
作者:李雪梅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时间:2020年12月
定价:198元
书号:978-7-5325-98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