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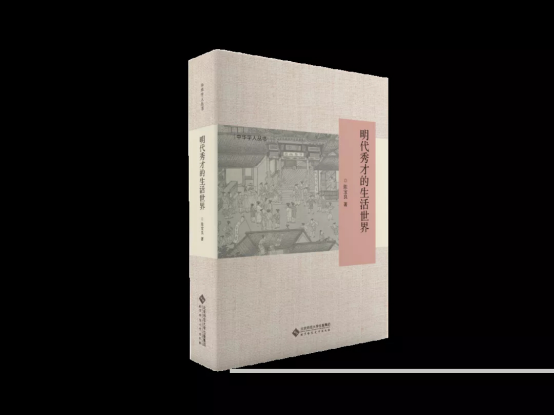
《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陈宝良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关于本书
秀才是一种俗称,其正式的称谓应为儒学生员。秀才既是一种科名,又是“四民之首”,构成士大夫阶层的下层,且在地方社会扮演颇为重要的角色。本书分上、下两编,对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秀才的产生、秀才在地方学校的肄业与考试,以及秀才如何步入仕途,旨在展示秀才在学校的生活世界。下编从社会的视角,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秀才的社会流动及其社会性动作,即他们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旨在揭示秀才流入社会之后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制度史与社会生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考察士大夫下层的生活与制度、社会之间的关系。
关于作者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等专著10余部,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明清史论文百余篇。所著多被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参考书。其中《中国流氓史》《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两书,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出版;《明代社会生活史》一书,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4年度十大社科图书”,并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
目录
导论1
一、生员及其相关概念辨析1
二、明代的教育体系11
三、明代生员研究:史料、现状与方法22
上编日常生活:肄业、科考及其仕进之途
第一章正本溯源:明以前的历代教育70
一、官学72
二、私学79
第二章学校:生员的生活空间86
一、南、北两京国子监87
二、府、州、县学93
三、都司儒学与卫学99
四、商籍与运司学校106
五、宗学113
六、孔颜孟三氏学117
七、书院121
八、社学、义学及乡学134
第三章生员分类:别称、名色及人数149
一、生员的别称151
二、生员的名色156
三、生员人数的初步考察176
第四章日常生活:生员的考取与课试195
一、学规与教法196
二、童试200
三、学官对生员的课业213
四、提调官的季考219
五、提学院道的考试223
六、院、台的“观风”236
第五章学优则仕:生员的仕进之途239
一、举人:生员羡慕的出路239
二、出贡:生员无奈的选择249
三、纳贡:为生员别开的蹊径256
四、荐举:生员的超拔之途260
下编社会生活:职业、生计及其社会交往
第六章社会流动:生员的职业生涯270
一、训蒙处馆271
二、游幕天下285
三、儒而医296
四、弃儒就贾300
五、包揽词讼303
六、弃巾311
第七章生员与地方社会:以政治参与为例324
一、生员与言责324
二、生员参政330
三、生员结社341
第八章士风堕落:生员的无赖化349
一、士风的演变349
二、无赖化倾向357
三、学变364
第九章穷秀才:生员的生计373
一、廪粮与优免374
二、生员之穷383
第十章走向社会:生员生活与明代学术391
一、生员的社会生活392
二、生员与明代学术406
余论428
一、士而仕430
二、衿与绅436
三、生员与地方社会442
四、生员与社会流动448
附表457
参考书目474
一、中文书目474
二、外人论著492
后记496
秀才的变迁(代再版后记)498
从士风衰微看士大夫精神的局限性
传统中国社会,无不把世风的“厚”与“让”当作一种美谈,而且将“士君子”作为世风的倡导者。《易》传有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又云:“上兴让则下不争。”汉有《崇厚论》,晋有《崇让论》,无不显示出厚薄争让,两相比较如同黑白。
在明代社会中,士风与士习也同样被认为相当重要。如徐阶云:“欲观士大夫名节,但不联姻富室,不接 山人,便是端庄之士。”这是就士大夫之名节而论,且其言外之意,晚明的士大夫,已经形成“联姻富室”“接山人”之风。可见,这是就士风之变而提出“端庄之士”对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又如张居正曾向皇帝进言,要求以“正士习为先务”。他认为,学术之所系,关系匪浅。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更是就士大夫与“百姓细民”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春天树木,何当尽有花叶,觉得有生意;冬天何尝无寒花,觉得枯索。”因此,他认为,树木只有得到小草的帮衬,才能有起色,而百姓细民就是士大夫的小草,同样可以起到帮衬士大夫的作用。与士大夫为百姓细民的表率之论不同,李光地更多的是着眼于百姓细民对士大夫的帮衬意义,这显然是一种视角转换。
山人,便是端庄之士。”这是就士大夫之名节而论,且其言外之意,晚明的士大夫,已经形成“联姻富室”“接山人”之风。可见,这是就士风之变而提出“端庄之士”对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又如张居正曾向皇帝进言,要求以“正士习为先务”。他认为,学术之所系,关系匪浅。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更是就士大夫与“百姓细民”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春天树木,何当尽有花叶,觉得有生意;冬天何尝无寒花,觉得枯索。”因此,他认为,树木只有得到小草的帮衬,才能有起色,而百姓细民就是士大夫的小草,同样可以起到帮衬士大夫的作用。与士大夫为百姓细民的表率之论不同,李光地更多的是着眼于百姓细民对士大夫的帮衬意义,这显然是一种视角转换。
明代士风,并不能一概而论。换言之,士大夫的行为,有其复杂性。在明代的士大夫中,既有恪守儒家行为准则的道德实践者,又有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假道学,甚至不乏不顾廉耻者。对明代士风的探索,既要把握其特点,又应注意其内在的变化。
若欲对明代士风、士气深入探讨,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士风、士气之历史演变,由此形成明代独特的士风、士气;二是明代士风、士气的内在转向,及其与社会变动之关系。
就前者来说,可引戚继光、刘玉、马从聘等人之说加以阐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就古今人物之变,有过下面一段感慨,基本可以说明晚明士风、士气的基本特点。他认为,明代所谓的“豪侠”,已与古代大相径庭,仅仅相当于古代所谓的“忿戾也”。与此相同,明代所谓的“仁人”,即古之所谓“姑息”;明代所谓的“才人”,即古之所谓“佞人”;明代所谓的“明哲”,即古之所谓“偷生”;明代所谓的“能宦”,即古之所谓“民贼”。总而言之,举凡明代能够“所称于世”之士,无不都属于古之“罔生幸免”。*这是相当明显的异动,说明在古今士风、士气的演变历程中,明代的士风、士气已经流于世俗化。
当然,士习的变迁,终究还是导源于“世变”。明人刘玉写了一篇名为《世变》的文章,对士习的变迁作了一些考察。在刘玉看来,作为士,其最高的境界则是不断对道德、义理完善加以追求,而上古时期的士,即能达到如此境界。这是“士习之最隆”时期。降及中古,自管仲之讲求事功,李膺之讲求名节,郑玄之讲求训诂,韩愈之讲求述作,导致道德流变为事功,义理流变为训诂、述作。这是“士习之既下”时期,即“道德而功名,固有依于道德者;义理而训诂、述作,固有达于义理者”。迄至明代这样的“末世”,士之所志者,科第而已;士之所营者,禄位而已;士之所习者,呫哔而已;士之所述者,蹈袭而已。于是,功名流变为科第禄位,训诂述作流变为呫哔蹈袭,这是“士习之愈下”时期。马从聘称明代为士风、士习“至陋”的时期,显然可作为刘玉之说的补充。这种士习的变化趋势,用一种形象的比喻,就好像山丘平夷而为陆地,陆地下沉而为深渊,深渊溃决而为流水,流水满溢而趋于大海。如何改变这种士习,使之回归到原先醇厚的状态,究之明代士大夫的普遍认知,就必须有一些豪杰之士出来加以力挽。
就后者来说,明代士风、士气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演变过程。按照明代人的看法,国家若欲扶危定倾,全借“士气”,而士气之盛衰,则或许与“运会”有很大的关系。从明代中期以后,士气开始了由盛到衰的转变过程。宋应星对这一变迁过程作了真实的对比:当士气盛时,士大夫即使面对“刀锯鼎镬”,亦不畏惧;当士气衰时,士大夫就会“闻廷杖而股栗”。当士气盛时,即使“万死投荒”,士大夫亦能做到“怡然就道”;当士气衰时,一旦“三径就闲”,士大夫就会“黯然色沮”。当士气盛时,即使“朝进阶为公卿,暮削籍为田舍”,士大夫亦能泰然处之,“幽忧不形于色”;当士气衰时,即使“台省京堂,外转方面”,士大夫都会“无端愠恨”。当士气盛时,士大夫大多“松菊在念”,即使“郎衔数载”,亦可做到“慨然挂冠”;当士气衰时,即使“崇阶已及,髦期已届,军兴烦苦,指摘交加”,士大夫“尚且麾之不去,而直待贬章之下”。当士气盛时,士大夫无不“班行考选,雍容让德”;当士气衰时,士大夫无不“相讲相嚷,贿赂成风,甚至下石倾陷同人而夺之”。当士气盛时,士大夫可以做到“庭参投刺,抗志而争”;当士气衰时,士大夫则“屈己尊呼,非统非属,而长跪请事,无所不至”。当士气盛时,士大夫即使“布衣适体,脱粟饭宾”,亦可以做到“清操自砺”;当士气衰时,士大夫则“服裳不洁,厨传不丰,即醴颜发赭而以为耻”。当士气盛时,若有“一令之疏,一师之败,一节之怠慢欺误”,士大夫无不“上章自首”;当士气衰时,士大夫则“掩败为功,侈幸存为大捷,而徼幸朦胧之不暇”。当士气盛时,士大夫“领郡之邑,艰危不避”;当士气衰时,士大夫则“择缺而几,祝神央分,遍挈重债,贿赂滋彰,既欲其靖,又欲其羶,然后快于心”。当士气盛时,即使“蕃兵虏骑攻城掠野”,士大夫亦能“激灑忠义,冒矢撄锋而成功”;当士气衰时,则“疲弱亡命,斩木揭竿”,一旦“谍报邻寇入疆”,士大夫无不“当食不知口处,妻子为虏而不能保”。*
这是相当大的士风、士气异动。那么,这种大的士风变动,就其大处而论,应该说以嘉靖前后为界,加以区分。按照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的考察,在嘉靖以前,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农家,只教人力田读书,深恶贪污,当时的士大夫无不知道“廉耻”二字。所以,嘉靖以前,士大夫“无携宦赀归家营产者”。这可以蔡清为例加以说明。史载蔡清登第之后,不求仕进,只在开元寺教书授徒。一日,为其母画像,母久不出,蔡清往请,其母道:“汝成进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见客也。”蔡清听后,大为伤感,即刻前去赴任。在任不久,又有归隐之心,即告归家居,不久其父去世。后又因贫穷,不能自给,只好去做南京部司之官,其目的就是南京离家乡较近。到任又归隐之心萌动,再次告归家居,其母亦不久即逝,人以为孝感。又史载蔡清任江西提学官时,曾寄出四两银子,周济他的寡居表嫂,再三叮咛告诫,“万勿浪费”。李光地由蔡清之事,发出如下感慨:“当时人虽穷,却穷得热闹。”然自嘉靖以后,士风、士气大有变化。当然,这仅仅就士风、士气的演变大势而加以区分,大体可以将其分为嘉靖前后两个时期。
其实,细究之,明代士气的变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明人郑以伟相当看重“士气”,认为士气是支撑、托举国家的主要力量。他将明代士气的演变概括为“三盈”“三竭”,其中云:
不佞居尝慨士气已三盈竭矣。有忍九族之灭,不肯成革除之一诏,甚至樵夫牧子固首阳之节,为一盈。少焉,脂韦成俗,遂酿土木之祸,为一竭。孝宗时,言论上殿,大臣重足立,为一盈。至大珰盗秉,而媚者半,为一竭。大礼议起,伏阙者声彻内廷,为一盈。嗣后不无少矣,为一竭。
概言之,明代近三百年士气,大体上受到了三次挫辱,一辱于靖难之役,再挫于大礼之议,三折于逆党擅权。
以靖难之役来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建文一朝忠义之士的诛锄,正可谓是不遗余力。就明成祖对待忠臣的态度与政策而言,即使与对待敌国巨憝相比,亦堪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保留下来的南京刑部及教坊司所记的一些资料来看,明成祖诛杀忠臣之事,确实是惨动天地,不妨摘引几例如下:
永乐元年(1403)正月,校尉刘通等解到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及杨文等男妇551名,明成祖下旨道:“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拏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只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所有这些人,都是练子宁的亲属,均被凌迟处死。同年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448口,也是相同的处理。永乐二年二月,教坊司题奏:“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妻刘氏,合无照依前例;谢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由韶舞安政等奏:奉钦依,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永乐十一年,教坊司在右顺门口上奏:“有奸恶齐泰等姐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怀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小儿女,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这显然是对明代士气的一大摧残。明亡之时,尽管崇祯皇帝自己身殉社稷,但能够“死事”的忠臣却寥寥无几,盖非无故。
以大礼之议来说,尽管不乏以死相争之士,但其结局却是从中产生了一些专以迎合皇帝心思之人,借此得以官运亨通。赵贞吉认为,议礼之争,直接导致了“士气卑弱”“委靡成风”,犹如越地所产之绵,“不团而软”。
以逆党擅权来说,尽管不乏东林一类的正直之士,起而与之颉颃,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随波逐流,甚至献媚或助纣为虐。
士气一旦受挫,士人随之出现了两分的现象:
一是仕宦率多寡廉鲜耻,贿赂请托,公行无忌,甚至以封疆为报仇修怨之具。
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即使如大臣王文,亦献媚王振,“见必长跪鼠伏,奔走甚欢,尤为士论所薄”。当时有一“贱工”,因为“谄事王振”,很多大臣就通过这位贱工向王振行贿,“故趋其门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节与之交”。成化末年,太监汪直擅权,士大夫更是不能守静安常、不为阿谄,而是“趋者澜倒,莫知纪极”,甚至不惜花费千两银子设宴,以取悦汪直,真可谓“丧百年士大夫廉耻之节,而不以惭羞”。当弘治之世,士风稍有变易,士大夫人人自爱而尚名节,重廉耻,形成一时忠厚之俗。其实,那些“中材之士”,身处盛朝,尚可保其名行,一旦遇到浊世,堤防既坏,不免放溢决荡。自刘瑾一出,这些无耻士大夫,“争先趋附,百计钻研,以营富贵。钻研得效,束装问途,甚至诲淫及于婢女。虽宰执台谏,多稽首董贤之车;父子兄弟,皆垂头万年之床。风俗波荡,无复士气矣。”即使是“大僚”,亦无不“蒙面濡首,争先屈膝而不恤”,尤其是高铨之子,甚至自劾其父,堪称“衣冠变为异类”的典型例子。于是,人心解体,忠义沮丧,而士大夫亦耳目习玩,以为当然,最终导致风俗纪纲“大坏极弊”。
所谓的逆党擅权,除了权阉之外,尚有权臣,同样对明代士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如严嵩、张居正擅权之后,士人的交际之礼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官场交际不再为人情所左右,而是受权势制约。很多史料记载已经明确显示,严嵩出任内阁首辅之时,权势熏灼,中外累胁。一些江西的士大夫首开谄谀之风,为了自己在官场上的一己私利,公然称严嵩为父。此风随后得以蔓延外省,很多外省官员也纷纷模仿,竞相认严嵩为父。即使严嵩的家人永年,也是狐假虎威,公然与士大夫“抗礼”,即平起平坐,一些厚颜无耻的士大夫甚至称永年为“寉年先生”。这种情况到了万历初年并没有好转。当时张居正出掌内阁首辅,也是权势显赫一时。张居正门下仆人游七、宋九,在那个时候也是着实风光了一阵。一些朝内“侍从台谏”一类的官员,纷纷与游七、宋九结纳,有些甚至关系相当密切,可以称兄道弟。
二是其中有些贤者,矜立名节,横执意见,只管实践了自己的道德风节乃至志向,却又不顾国家之事,对世变并不通达,甚至好同己植党。其结果就是使九庙陆沉,帝后杀身殉社稷,明朝最终趋于灭亡。换言之,一些士大夫中的贤者开始出现一种以辱为荣的现象。
自明代中期以后,凡是官员向皇帝上奏,一旦出言不慎,得罪了皇帝,往往会被赐杖大廷,这就是明代特有的廷杖。每当廷杖之时,官员通常会“裸体系累”,斯文体面丧失殆尽。这在传统士人看来,应该说是最大的侮辱,并不是盛世所宜之象。令人奇怪的是,明代很多官员并不以此为辱,反以此为荣。而天下的士人则因为这些受廷杖的官员抗疏成名,“羡之如登仙”。这不能不说是明代士人的一种特有风气。明代官员的“犯颜直谏”,就儒家人士的本心原则而言,应该说不是为了求名,而是希望自己的建言能得到皇帝的采纳。假若皇帝采纳臣子的建议,当然是一种主、臣共荣的理想状态。然而从明代的政治实践来看,一些皇帝多是刚愎自用,不愿采纳臣下的直言,甚至不乏以廷杖相加。尽管官员受辱,但还是不断有官员犯颜直谏。何以出现这种“过归于上而名成于下”的现象?正如明人于慎行所言,还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向皇帝进言之时,并非出于一种“纯臣之本心”,而是为了求得自己成名。
后 记
1998年3月,我离开了学习、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负笈南洋,求学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我先学习,后工作,在这个热带岛国学习、生活了近四年。客居异乡,终年如夏,由不得思乡之情不浓。即使是报纸上一帧故宫雪景之小影,亦不免为我平添丝丝愁绪,我的思乡之情并不因星岛的美丽风光而稍减。我无古人才情,可作“游子吟”以抒胸中之怀,但我能遨游于书海之中,以书籍为伴,并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享受读书之乐。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明代生员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于2001年12月答辩通过。论文选题的缘起,实可追溯至20年前,当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我就对明清之际学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读《亭林文集》,为其《生员论》三篇所吸引,觉得理应顺着亭林的思路,对生员作一考察。因随后我更多地关注明代读书人的结社,并进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明代乃至清代的各色社团上,故不得不暂将此题搁下。但我心中并未放下此题,当我读书之时,凡是相关资料,无不札记。时日一久,记录资料的本子已达十几个。于是在多年之后,我重拾旧题。
本书分上下两编对明代生员层进行了考察。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生员在地方学校的肄业与考核,以及生员如何步入仕途。下编以社会为视角,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的社会流动以及一些“社会性动作”,即他们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而这类生员又恰恰占生员总数的绝大部分。我斟酌再三,觉得不如将书名易为《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更为恰当一些,但并不是为了迎合所谓的学术“主流”。
正如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我的同乡先贤张宗子就批评浙江人模仿苏州人之风,直斥他们是“跟不着”!这确实是入木三分之论。生活如此,治学何尝不是如此。治学路出多途,我们何必刻意分出主路、岔道。关键不在于路之主、岔,而在于我们是否读书乃至于求真、求实。钱牧斋曾告诫他人,应多读书,厚养气,然后再深造而自得之。这可以说是治学的金玉良言。学术不是时装,需要紧随流行时尚。读书人更不是俏姑娘,总想前卫,紧跟时风。过分打扮的人,反而多了些脂粉气,还不如做一个素面人,让人觉得可爱。人为习气所染,就不免流为俗人;学为流风所濡,同样不免陷于俗学。我能幸免于此吗?这我不能自说自话,且等读者评骘。
目下有些学者,多了些山人气、游士气,少的却是学者气。或整日群聚,言不及义;或奔走于大老之门,觅一些蝇头小利。更有甚者,一年倒有一半时间在天上飞,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以机舱、包厢为书房。不是候鸟,却似游隼,闻膻麕集。若要他们静下心来,在书舍,在图书馆,一如坐牢,难免浮躁不安。想及此,不由为自己庆幸。当人们“熙熙”“攘攘”之时,我且稳坐螺壳室中,一杯清茶,一支淡巴菰,泛滥书海,其乐融融。室虽小,其地亦数迁,或在城东,或在城西,或在城北,或在城中,甚至一度移至南洋。然其名则一,其情不变。室名螺壳,不仅仅说其狭小,而是能如我家乡人所言,可以“螺蛳壳里做道场”。需要声明的是,我虽坐螺壳室中,却无道人本领,专会大吹“法螺”。
最后,我要感谢新加坡政府,为我提供了此课题研究的全额奖学金。我也要感谢李焯然教授在我求学期间对我的悉心指导,以及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我尤其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郭沂纹编审,以及出版社的诸位领导,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方使拙著能顺利出版。
古越村夫陈宝良识于京城螺壳室
2004年10月1日
秀才的变迁(代再版后记)
说到秀才,我们不妨先拿鲁迅的小说作为引子。在小说《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读书多年,穷穷,却一直未能进学,获取一个秀才的科名,只能穷困潦倒,终日梦想能在自己家中“掘藏”,找到祖宗埋藏于地下的钱财宝物,一夜暴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孔乙己》小说中的孔乙己,或许曾饱读诗书,甚至能在懵懂的孩子面前炫耀茴香豆的“茴”字有多种写法,但他因缺少秀才的头衔,也只能替有钱的读书人家抄书维持生计,甚至有时不免做一些窃书的勾当。
无论是陈士成,还是孔乙己,都是传统科举社会中读书不成且无法获取科举功名的落魄读书人的缩影。相比之下,已经有了秀才名头的读书人,其境遇应该要稍好一些。于是,在小说《阿Q正传》中,作者刻意提及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大抵可以说明如此奢华的雕花大床,只有秀才的妻子才受用得起,非乡野小民的女子所可觊觎。这无疑就是清末秀才身份与财力的佐证。相较于尚未进学成为秀才的普通读书人来说,秀才确乎已具较高的荣耀与地位。打个比方,与童生相比,秀才好像出椟之玉。若说童生是刚刚开蒙,默默无闻,那么,秀才不但名闻于人,而且因德行已成而被人寄予厚望。
自唐宋尤其是明清以后,科举社会已经形成,秀才随之成为科名最初的一级。秀才除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之外,还可享受诸多实际的经济利益。说得明白一些,秀才不但享受廪粮、膏火,而且还被免除徭役,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到府衙、县衙里去说人情,吃荤饭,谋取种种好处。在老百姓面前,秀才具有很高的体面,且颇有一些影响力。明代清官海瑞曾经做过浙江淳安县学校的学官,他写过一篇《规士文》,将百姓对秀才的敬畏之情明白地道出。根据海瑞的描述,乡间闾阎父老、小民,有时会同席聚饮,席间可以毫无拘束地笑谈。等到有秀才过来,就无不敛容息口,唯秀才马首是瞻,唯秀才言语是听。秀才行走于市上,两巷的百姓都注目视之,偶语纷纷,道:“这位是学校的斋长。”从人情上说,百姓如此看重秀才,倒并不是因为他们惧怕秀才的威力,而是在百姓的内心深处,他们认为秀才是读书知礼之人,自己却是村粗鄙俗,生怕引起秀才的讥笑。
在科名等级俨然的传统社会,秀才的身份又明显逊色于举人。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有“举人老爷”一称,大抵道出了中国科举文化的底蕴。从明清以后,小说与戏曲作品中人物的称谓已经显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唯有在科名上获得举人之后的人才得以被人称作“老爷”,而举人的妻子则被人称作“夫人”。这是因为举人可以出仕做官,而他的妻子则以夫贵,可以有幸得到封诰。至于秀才,通常只是被人称为“相公”“官人”,秀才的妻子则被人称为“娘子”。这种称谓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一些印记。秀才一旦中式成为举人,犹如置身青云,乡里富人争相与之结姻,美男、美女纷至沓来,上门求为仆人、争做小妾。换句话说,士子一脱青衫,就可以扬扬矜诩,衣马仆从,供具饮食,一切都变得阔绰起来,不再是过去那副寒酸的样子。至于他们的父母,也自忖有子成名,旦夕即可富贵,俨然以“封君”自居,厚自奉养,甚至豪横恣睢,鱼肉小民,为暴于乡里。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与举人相比,秀才身份确实稍逊一筹。明末著名的八股文选家艾南英虽然具有秀才身份二十余年,但终究因为没有中得举人,而享受不到应有的礼仪待遇。根据他的回忆,每次乡试之后,只要秀才中了举人,即使是空疏庸腐、稚拙鄙陋之辈,同样可以与府、县地方官分庭抗礼;至于名落孙山的秀才,即使是积学二十余年的资深秀才,在谒见地方官员时,也只能排队而入、分队而出。这就是科名社会的等级身份特征。举人出仕做官,归乡之后就成为乡绅,这些乡绅在地方上无不受到衙门官员的礼遇,同样与秀才霄壤不同。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提供了很好的证据,说明举人与秀才在地方上属于两个层级。小说在说及地方上遇到节孝祭祀一类的公共事务时,就明确说明乡绅与秀才必须站立两班:一班是乡绅,他们都是有了举人、进士、贡生、监生的身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则是秀才,他们穿着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
其实,秀才是一个民间俗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有“今俗谓生员为秀才”的说法,就是最好的例证。秀才的通称或者说正规的称谓应该是“生员”。根据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的记载,生员一称通常是用于公文、呈文、状纸时的头衔。除了“生员”是秀才的通称与正规称呼外,秀才还有很多别称,分别有“茂才”“庠生”“博士弟子员”“相公”“措大”“官人”“青衿”“斋长”“师傅”“酸子”“穷板子”“学匠”等。
今人一提秀才,就联想到三家村的老学究,他们的形象大多寒碜酸腐,秀才仅为粗通八股的冬烘先生。其实,这是一种偏见。秀才科自出现以后,一直在贡举诸科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尤以唐代为甚。中国古代的选士、俊士、造士,都是从命乡论秀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公山、正礼、崔儦、孙权,都曾举过秀才,无不都是瑰奇卓荦之士。尤其是杨素称周孔复生,犹不得为秀才,秀才的名头为世人所看重已是不言而喻。到了清代,民间称生员为秀才,又称“秀士”,在民谚中更是有“斯文一脉扭扭捏捏”的说法,说明秀才在百姓的心目中是斯文人。
事实确实如此。考“秀才”二字,原意是指“才之秀者”。其具体含义,正如明代人陈玉辉在他所写的一篇《规士文》中所云:“夫禾之高者曰秀,十中一人曰士。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薰其德而善良。”侯方域在《重学校》中也明白地指出:“才秀于人,谓之秀才”。可见,所谓秀才,即指秀出之士。
至于秀才一称的起源,过去流行下面三种说法:其一,明人杨慎认为“赵武灵论胡服云,俗辟民易,则是胡越无秀才也”;其二,明末清初人顾炎武认为秀才原出《史记·贾生传》:“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备,闻其秀才”;其三,则是清人王先谦认为“秀才所由命名,盖出《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是赖也’之文”。据近年来的研究,秀才之名起源于西汉说较为可信,而且明代人称生员为秀才,亦以汉代秀才说为张本。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汉代秀才并非作为举人的科目之一,直到西晋时才出现了秀才科。随着时代的变迁,秀才科越发为世人所看重。到了魏晋南北朝,因朝廷实行九品官人法,并使之与门阀政治相结合,秀才科的地位反不显重要。自隋代以后,秀才科在贡举诸科中的地位最为崇高,相对说来,及第也较为困难,终隋之世,举秀才及第者不过十余人。至唐代,朝廷更是提高秀才及第者的品阶,将其置于贡举科目之最。到了明代初年,朝廷也曾经举秀才,如洪武四年,朝廷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扬州府知府,俱赐冠带。洪武十年,朝廷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至洪武十五年,朝廷征至秀才数十人,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
然自宋代以后,秀才的声望已有下降之势。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宋代已视秀才为“相轻之称”。到了明代,秀才仅仅成为科举仕路上生员的俗称,而且生员也不以秀才为荣,一听别人称自己为秀才,就会觉得受到人家的轻蔑了。于是,在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开始涌现出大量“酸秀才”的形象,成为此类读书人的范型化人格。如民间俗语中称秀才为“醋大”,这是说秀才虽无多少学问,却喜欢掉书袋;明代流行的《江湖方语》这本书,更是直称秀才为“酸子”。如此看来,秀才确实很难摆脱与酸的干系。如清代人蒋砺堂中举人之后,他的族侄蒋德舆专门写了一副贺联,云:“秀才既去酸还在,进士将成大已来。”可见,唯有秀才中举,方可去掉酸气。至于秀才的酸气,我们不妨引用明人赵南星《笑赞》中一则《秀才买柴》笑话加以揭示。笑话记道,有一位秀才上街买柴,道:“荷薪者过来。”卖柴的人因“过来”二字听得明白,就把柴担挑到他的面前。秀才问道:“其价几何?”卖柴人因“价”字明白,就说了价钱。秀才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人不知秀才说甚,就挑着担子径自去了。可见,尽管秀才学问浅陋,却喜咬文嚼字,掉书袋,全然一副酸秀才形象,养成一股酸腐之气,干不了甚事。读书误人,于此可见。
从民间流传的很多谚语来看,秀才原本应该属于饱学之士。如在唐代,《昭明文选》一书颇是流行,当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说明即使读书人将《昭明文选》背得滚瓜烂熟,也只能成为半个秀才。到了宋代,开始流行苏东坡的文章,于是又有了“苏文熟,秀才全”的谚语,说明要成为秀才,必须写得一手精湛的苏式文章。宋代王安石改革五经之义,原本是想将学究变为秀才,但结果流于失败,王安石对秀才变为学究的结局大为感叹,说明秀才学问终究不同于学究。至明代,更是盛行如下谚语:“既成童,经义通。秀才半,《纲鉴》乱。”细绎其意,是说秀才无不具有积学功夫,他们有志于根柢之学,而并非只在高头讲章、新科闱墨中讨生活。到了清代,又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之说,说明秀才以天下为己任,杜门不出,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一旦出身任事,就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下能够措大事之人唯有宰相,而民间称秀才为“相公”,显然也有期望他们将来能措大事这一层意思。
事实并非如此。自科举制度盛行之后,秀才所务之学不过是八股文而已,学问开始变得浅陋起来。明末清初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一文中,记录了一则笑谈,不妨抄录在下面。过去有一位僧人与一位秀才同宿于夜航船。秀才高谈阔论,僧人畏慑,只得卷足而寝。不久,僧人听到秀才的言语有破绽,于是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秀才回答:“是两个人。”僧人又问:“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秀才答:“自然是一个人。”听罢此言,僧人就笑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笑谈已经明白地说明秀才腹中空空,反而会被僧人所鄙视。在清代的江南,流行一句谚语,叫“举监生员”。这句谚语的出典,就是举人、秀才、监生的学问各有差别。这则谚语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故事记载,有举人、秀才、监生三人,分别聚在一起宴赏中秋之月。三人饮酒至半,步出中庭,仰望明月,不禁文思泉涌。举人道:“好月色。”秀才道:“好月色也。”监生道:“好月色也者。”一字一加,声情如绘,学问却是越发浅薄。
秀才学问浅薄,其实也怪不得他们。科举时代的科名等级差异,导致秀才贫困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于是民间就有了“穷秀才”的说法,这是事实。根据明代忠臣杨继盛在《自著年谱》中的回忆,他在做秀才时,因为生计困难,只得借住在僧舍学习,甚至必须自操井灶之劳。譬如冬天他到外面汲水,手与水桶冻在一起,到了房内,呵化,才开始做饭。夜里因为缺油,他只得在月下读书。月下夜读,没有夜宵享用,腿肚常常被冻转,他只好起身,绕着室内快跑。秀才穷况,真可谓难言万一。秀才中的穷者,为生计所迫,只好出去教书,于是正如小说《闪电窗》中所说,在明代已经有了“秀才怕老婆”的说法。究其原因,秀才辛苦处馆,方得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岂有闲钱、余暇去傍花随柳?
时移势易。时代变化了,秀才的行为却堕落了。民间久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这原本是说秀才是斯文人,多有顾忌,难成造反大事。不过到了明代,秀才在百姓的心目中,却已有了“蓝袍大王”的绰号,百姓将秀才比拟为占山为王的大王与神庙中称呼不一的大王神像。至明代末年,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凡是市井闾阎有人互相争斗,动辄说:“我雇秀才打汝!”一至清代,秀才更是结成了“破靴党”,为害乡里。士风至此,已是可想而知。
秀才属于四民中的“士”,而且居于四民之首。孔子说:“士志于道。”曾子说:“任重而道远。”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所有这些,无不说明秀才博闻敦行,以成为圣贤为归趋。不过从宋代以后,很多读书人书室墙壁上所挂,大多不是圣贤格言,而是宋真宗所书的《劝学文》,他们所信奉的仅仅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之类的话头。于是,读书人动辄说“岂有生肉与我吃哉”,不再以“从祀孔庙”而得以享用冷猪肉为最高追求。士人崇高精神趋于沦丧,实有其因。
陈宝良识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
2018年6月18日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新史学1902》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