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晟 文/图
一,引言
从2010年立项,到现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已经有8个年头了。就写作的精致程度而言,这本书似乎比不上我以前写的几种,但是在学术思想上,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算是基本从追求解释,走向历史理解。这条路是否可行,是否会有成绩,尚不可得知,但是从内心来说,在学术上算是有一个安心之处了。起承转合,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做一些交代,既是立此存照,也是呈现不足,以供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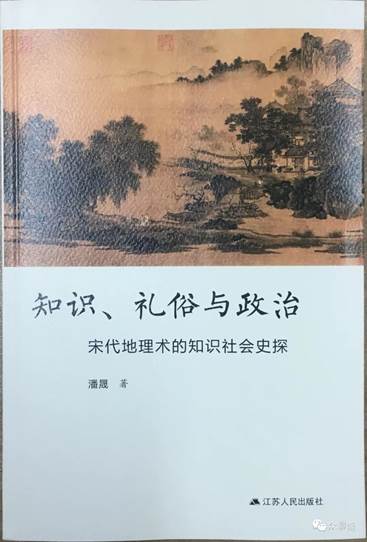
与《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讨论“学”不同,本书讨论“术”。直到本书二校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工作,无意中恰好形成了传统“学”“术”的闭合环,可以算是无巧不成书。
“术”的问题有时候比“学”来的更为复杂,也更难,因此本书中自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就我现在的精力、能力,包括兴趣,已经不可能在具体的细节上做到精致,再拖延下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恰好有一笔经费可以用,遂不揣浅陋,大胆出版。
二,写作缘起:生活与学术
作为农村长大的人,对风水并不陌生。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知道左青龙右白虎这样的词语,大概在我刚上小学那会。村里有两户隔着路的邻居,路左边的人家新建房子的时候屋脊高过了路右边人家的屋脊,矛盾因此而起,最后动起了手。当然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她还给我讲了白虎抬头、青龙抬头之类的话。大意是白虎抬头不好,而青龙抬头其实没有什么大碍。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虽然不懂,但是很自然地反问我妈,既然青龙抬头没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路右边的人家不乐意呢?我妈被我问倒了!
在我家里,据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是看过风水书的。他自己讲,上学的时候曾向本村一户藏有大量风水书的人家借过书看,但是没有学会。而且他后来当兵、入党,对这些东西基本属于半信不信。而我妈说,我大姑妈虽然不认字,但是却懂得风水。当年我家建新房子选地基(现在已经拆迁)大姑妈曾帮着看过。乡村中,这种情况实在是最为平常不过。
就我本人来说,真正在学术上接触一点术数的东西,是上了高中以后。我所读的高中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里面除了中学教材、参考书之类的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书。那个时候我对课堂学习既不排斥也不喜欢,所以空闲的时候就到图书馆看书借书,除了随便乱看小说,还认真读了一些《易经》有关的入门书,不过大多看过就忘记了。大学里面仍然如此。直到进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上了王克陵老师的课,才知道这里面原来学问很大。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日后自己会专门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2004年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选题是宋代的地理学。为了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宋代地理学的脉络,把影印出版的宋代文集基本翻了一遍。翻阅的过程中,发现文集中的“地理”,无论是人还是事,其所指都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地理知识有较大的出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与今天所讲的风水相近。遂就此现象向导师唐晓峰先生汇报。唐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了然于胸,并扼要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之写到博士论文中去。因此,在后来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就特别留意这部分的内容,并做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尤其在听了李零老师古代学术史的课程之后,对术数问题有了更多认识,遂在学位论文设计中预留了一个章节的空间。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随后的毕业论文写作方法与方向都做了彻底的调整,将这一部分全部放弃。
2008年博士毕业,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为了职称与收入,自然要积极申报各项课题。遂将未能写入学位论文的地理术数这一块做了重新梳理,并将它与聚落演变结合起来,做了认真的学术史准备,打算从历史地理学科的角度来阐述知识、信仰与聚落演变的相互关联。很幸运,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立项。
按正常的情况,获得立项之后我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之中,但是套用一句很俗的俗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不仅不能全身心投入,还一度荒废,经常在极度的无聊与莫名的紧张之中徘徊。这既有面对无力购房难以维持家计的无奈,也有对隐隐触碰到红尘之后的那种寂寥的理解。
总体上资料搜集的工作较为顺利,但是后期的整理与写作却并不如意,经常写得一团浆糊。直到2014年初才完成初稿,同年7月份递交了结项书。这个时候项目已经延期一年了!
三,思想旨趣的转变:从复原性解释到历史性理解
最初提交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的时候,选择宋代地理术数作为讨论对象,最主要是希望还原地理术数在宋代的基本面貌,揭示它作为一种知识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从而祛除围绕在它周围的层层迷雾,起到正本清源,直面本质的作用。这既是延续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旨趣,尽力复原古代知识世界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当下社会对它的各种形式的神秘化。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因素。一是,每隔一段时间,社会各阶层都会兴起关于它是科学还是迷信的纠缠不清的论争。而这种论争,无论来自哪个领域都是自说自话,对地理术数作为一种知识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缺乏必要的证实与证伪。一是,我哥哥迷上了包括风水在内的术数,并到处拜师学艺。说实话,当时我极力反对,认为不好好琢磨种地,却到处拜师学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实在是不像话。但是我又无力说服他。因此于公于私,更好地呈现古代地理术数的原貌,对我来说都是一件有意义也有必要去做的事情。
随着阅读的深入,接触的面也越来越多,对于它作为一种信仰性知识在日常社会中的位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初在项目设计中还较为虚化的地理术数与聚落形态的关联性,地理术数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问题,也逐渐有了展开讨论的头绪。考虑到这里面涉及的层面过于庞杂,不可能一一疏通,遂选择其中最为显著且易于把握的两个方面——即地理术数发展与科举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或塑造聚落形态或社会空间——以个案讨论的方式,较为轮廓性地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到这一步,算是摸索到了如何讨论地理术数这一类信仰性知识与社会互动,并塑造出人文景观的方法。但比较遗憾的是,在本书中没有能够在这方面深入地展开。
书稿及单篇论文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古代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吸收国内外理论进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学术史——知识史——知识社会史,这样一个相互衔接又相互交叉的讨论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虽然以复原知识在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为核心,但是最初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释知识何以成为知识本身,以及它背后的社会与它如何在相互之间互为可能。白话一点说,就是希望通过对某一类知识的演变来探求其所处社会的历史演变途径,并解释该途径。虽然我在讨论的过程中,强调对象的还原性呈现,认为这种呈现作为一种现象学还原,它本身就是真理存在。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解释型的研究,或者称之为释义型的研究。
这种方法与研究思路,为了解释已然发生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按照解释者自己的需要来展开释义,而且大多数时候都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自圆其说的效果。如此这般,那么历史研究虽然发挥出了社会价值,但是这种社会价值实际上是以研究主体为中心的。换句话说,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单向的,从而造成各种中心主义——无论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中心主义——的客观存在。各种形式的中心主义,都是以某一文明或文化为中心展开的释义,它所对应的是其各自文明或文化自身的存在价值,是一种单向度的内向化的认同方式。它在本质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凡事从其本身出发,无法解释而得不到认同的都是异类,并进而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否定合法性。这一点在1500年以来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全球扩张时期,表达的最为淋漓尽致。要破除各种中心主义或中心论,或许有必要从方法与思路上提出新的看法。
在学术思考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对于哥哥拜师学习风水等各类术数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在此之前,我哥哥不仅不相信这些东西,而且是反对的。但是人到中年以后,面对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这种看起来似乎无法突破的生命状态),他可能已经认命,不想再在原来的道路上挣扎或者抗争。内心的苦闷以及不甘,需要找到新的途径,来解决未来的道路问题。这是我在与他的对话中,能够时刻体会到的情绪。而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仅没有办法给予他帮助,还有赖他在家照顾父母。同样也面对着他所面对的出路问题,只不过与哥哥略为不同的是,我还在原来的道路上努力地挣扎与抗争。
夜深之时,时常回想生活之种种,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释然。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哥哥这些年来学习术数的动力与希翼。也正是如此,我不再反对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而能够聆听他对于术数的理解,并适当地与他展开讨论。而我哥哥这样走上术数学习或者修炼道路的情况,在我阅读的宋代文献中有着相当广泛的记载。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感悟还是文献阅读,都逐渐让我从解释型研究开始转向“理解型”研究。
虽然暂时我还没有能力对这种研究旨趣的改变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但是我认为从解释型(或释义型)研究转向理解型研究,实际上是从单向的内化认同,走向双向的内外互动认同,是跳出各种中心主义的一条人本主义道路。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它的学术前景多少还是有点不自信的。不过2015年8月-2016年8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期间,发现合作导师戴梅可教授(MichaelNylan)最近几年来从事的东西方经典的翻译研究,其核心旨趣就是文化理解。虽然限于语言能力,无法全面理解戴老师的工作,但是她的学术旨趣与我的想法有相似之处。她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理解,特别是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古代经典的阅读与翻译,来发现这些古代经典对于推动当代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理解的价值。而我所想的,更偏重于认识论。我希望“理解”是一种互动认知过程,不追求理解之后的解释或释义,并不赋予被理解对象以意义。因为一旦赋予被理解对象以意义,这种意义本质上就难以逃脱以理解者为中心的解释或释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的内化认同,回到各种中心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我所倡导的只是理解。
就本书来说,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脱离解释或释义,并试图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只是有了一点理解型的味道。但是无论如何,后面可以预计的若干年内的工作核心,我将会试图围绕如何展开理解型的研究进行尝试,并以人与人之间的历史性理解为基础,由此推动人的共时性理解为目标。
(按:写作侧记以《知识、礼俗与政治》一书的“后记”为基础,做了删改)。
原创: 潘晟
众聊斋
众聊斋 2018.11
微信号 zhongliao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