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以线上的方式进行了一场题为“我与地方文献”的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黄阿明副教授主持。

▲科大卫
科教授回顾他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和国外,只能接触到非常有限的地方材料。他上大学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清史学界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清实录》等官方编纂的记录,所以很多学者都是研究清政府的制度而不是地方社会。跳出政府制度,他们最有兴趣研究的地方是对清政府财政最重要的地区——江南。
台湾地区成文出版社从1960年代开始,相继翻印了一系列的中国地方志。在这之前,地方志也不容易找到。当时,大家以为可以利用地方志探讨地方史,但是,很快,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地方志其实也是非常官方的材料,而不是民间保存下来的地方文献。当然,地方志继续对历史学者很有帮助,不过要先明白地方志与乡村(“地方”)已经距离很远了。
当年,通过阅读傅衣凌先生的《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知道地方文献的存在。傅先生提到他在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发现一批土地契约,令学者一窥使用从地方人士手中拿过的文献做研究的兴奋。当时,出版的徽州文书数量很少,直到叶显恩先生《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出版,科教授才知道徽州文书里面的内容如此丰富。

▲傅衣凌
那个时候,不仅能看到的地方文献十分有限,就是到中国大陆的机会也不多。1973年科教授第一次来大陆,但是根本没办法到乡村行走。当时,历史学者中,很少有人想到要研究地方上的历史,反而都是一些人类学者在香港的新界和台湾做田野考察,所以当时他们研究中国依赖的其实是中国边缘地带的材料。历史学者用江南研究明清中国,人类学者用新界、台湾研究中国,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一些难以接受,但是鉴于那个时代的种种局限性,这已经是学者们最接近中国农村的方法了。
科大卫1976年毕业,1977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当年还有农村气氛的新界。在新界学习乡村的历史,才碰到地方文献。
科教授强调在农村学习历史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注意到每一段文献材料的出土背景。他以新界一个偏僻小岛吉澳发现的《奉两广总督阁部堂大人批行给示勒石永远遵照额例碑》为例,说明为什么出土背景资料对历史学者重要。碑文的内容是两广总督在嘉庆七年的批示,回应“疍民”即水上人的申请,禁止岸上人向他们增加租用土地的租金。按照碑文所述,这些在偏远小岛的水上人,向要走两天才可以到达的新安县,呈交了呈文,县政府认为事情的重要性值得传到两广总督批示,然后,批示刻在碑上,放到当地的小庙。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些水上人或许普遍都没有读书识字。这个过程,需要怎样了解?大概当时还是有书吏替他们写状子的吧。但是写状子的人,真的需要替他们跑到新安县衙门吗?谁知道总督有没有这个批文,谁知道新安县有没有判过这个案子?谁知道碑是否嘉庆七年立的?我们并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唯一能知道的是有这么一个碑出现在这里,作为历史学者,我们需要抱住这些疑问去解读。
地方文献包括族谱。但是科教授从一些老照片和田野所见的祠堂、祠堂里分猪肉、牌坊、碑刻、古钟铭文显示族谱需要放到宗族的生活里面解读。地方文献也包括土地文书。在香港新界,土地文书甚至可以连贯到非常详实的殖民地时代的田土登记记录。科教授在他发表的有关新界历史的书(《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子》)有一章就是利用这些资料重构一个村子发展的历史:祖宗到来住在哪里,哪些房子是哪一房的后人建筑,为什么宗族的规模就印刻在村落房屋的分布之中,其发展与村前的防潮堤坝的修建有什么关系。当然,地方文献还包括账本。他以一本租簿为例,说明为什么解读账本还是需要对地方有所了解。账本中有一个把两兄弟名字合并的名字。村子里面的人一看都知道这个名字代表两兄弟,但是外面的人就会以为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人。解读地方文献也需要懂得地方的礼仪活动。他认为他在新界的研究,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可以从宗教活动中了解乡村联盟。宗教礼仪需要道士先生的参与,道士先生应用的科仪本,很慷慨地让我们学者复印。但是,学者需要可以把科仪本放回宗教仪式的现场才可以明白宗教活动在乡村生活的核心性。历史学者在田野的目的,不是在收集文献,而是学习村民文献、口述传统、仪式演绎,把历史存留下来。科老师强调,文献其实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专门为历史学者而留下,因此历史学者们要读懂一个文献,需要把文献放回生活去。
在新界发现的地方文献,只是学习的副产品。但是,在新界也实在发现不少文献。他在新界研究找到的文献,都是复印后把原本交还村民,同时也存一份在图书馆。现在香港的大学图书馆都藏有《新界文献》的复印本或胶卷(20多卷)。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界大埔海下村找到的一家人三代的藏书。需要明白,到现在,学者没有在多处发现一整批的乡村读书人的藏书。其中有印本,有抄本。有看风水、看相的书,也有乡村的日用手册,常用的礼仪文书(例如三书六礼)。有地契、有账本、有医书、有课本,有普及的到处可见的四书五经,也有清末民初广东这一带的新课本(例如民国元年的《妇孺三四五字书》,用广东话写的),也有单张的文件(例如《那奴及澳顺岛舢板水手合同章程》)。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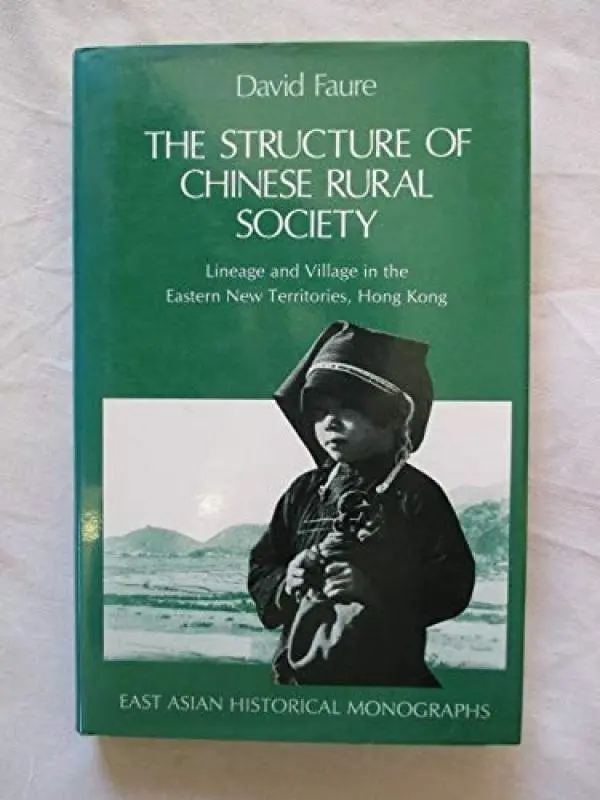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子》
研究了新界的历史以后,科教授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继续研究宗族的历史。他虽然有机会跑田野,但是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广东省图书馆。对于他而言,地方志、谱牒、碑记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除了碑记,在地方上找到的文献不多。在番禺沙湾,地方办公室收藏的《留耕各沙总志》和《辛亥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非常宝贵。后者标题的“辛亥年”就是辛亥革命这一年。可能因为珠江三角洲在近代开发比较早,很多地方文献流失到别处。但是,地方学者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小榄何仰镐先生让他们读他写的《榄溪杂辑》手稿,杨宝霖教授与他们分享他收集到的东莞族谱,佛山博物馆也非常慷慨地让他看到他们当年还在整理的文物志的材料。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是得到很多地方上的学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甚至中山大学、广东省社科院的同事种种帮忙的。
村子的文献流失,去了哪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部分叶灵凤先生后人捐献的材料,其中包括一本光绪丙申修的《灵应祠田铺图形》,一幅一幅地纪录佛山祖庙(就是灵应祠)的房产。很明显,有部分流失的材料去了收藏者的手里,然后再从他们手里转到图书馆。所以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文献,需要在图书馆里去找。在广东省图书馆从1930年代,已故罗乡林教授已经有收集族谱。图书馆还有一些鱼鳞图册、家用账簿等等资料。他特别有印象的是新会县景堂图书馆,收藏了好几份行会的资料,也从改革开放开始收集当地的族谱。当时比较意外的,是在国外的图书馆找到重要的珠江三角洲地方文献。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找到道光十年编的《佛山街略》。这本小册子把佛山每一条街的商业活动记下来。另外有一本《广东名人故事》木刻版的小册子,以趣味形式记录例如霍韬、方献夫上大礼议其中两人的微妙关系。其实也不应该奇怪这些十九世纪出版的小册子收进了国外图书馆。以前,这些印刷很粗略的小册子在地摊上可以买到,藏书家看不起,但是外国人感兴趣。另外一个有丰富广东地方文献收藏的地方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尤其是收藏一批广东巡抚衙门的文书抄本。这类材料,他只见过三种。另一种收藏在广东省图书馆,第三种香港许舒先生在旧书店找到。
有关旧书店和许舒先生,科教授说许先生是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政府官员,长时间在新界服务,对乡村历史很有研究,也多年来跑香港的旧书店,收集了不少有关广东的资料。许先生很慷慨,找到资料提供给学者参考,他是受益者之一。科老师在“告别华南研究”已经提到黄永豪先生把许先生买到的地契配合到广东省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写出一本有关沙田开发的历史。许先生还买到过一批从民国初年到四十年代的潭岡乡乡会董事局议案薄。这个单姓村在新会,但是在民国初年因为械斗毁掉,通过在外地生活的族人(在广州、香港、东南亚)的协助重建,建立了乡会。所以村子虽然在新会,乡会却在香港开会,新会的事务交予当地一名“司理”,长时间不断地向乡会报告地方情况。在这个架构之下,乡会的会议记录就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地方档案。刚巧,这批文件差不多完全有正副本。许先生收藏了正本,后来捐到史丹佛大学胡佛图书馆,科老师得到副本(没有的,以复印本补充),副本后来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他用这批材料写个一篇文章。顺带一提,他在香港的旧书店也很幸运找到好资料。《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给他很大的启发,《叶光大堂世守书》显示家族祖尝过渡到有限公司的变化,《承办广州市粪溺大生公司息摺》他认为应该放在博物馆,最后捐了去广州博物馆。
2000年以后,科老师带着八十年代的问题,跑到华南以外的各处。比较注意的材料仍然是地方志、碑记、族谱。再没有机会做像在新界那样的深入研究,去过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走马看花,但这个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令他知道中国各地社会的异同。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山西,所记录的碑文对他的研究很有启发。在当地读碑与在出版品里读碑的经验就是不一样。在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所见到的元、明碑记,不只看到族谱刻在碑上,还见到有一行被凿掉。为什么要凿掉,最后连贯到一个离奇的故事,这里不多说。地方还是有文献:江西村子的人很帮忙地拿出族谱,西南一带的道士们也提供科仪书,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高度的发展,村子变了,文献也变了。这个是一个地方文献工作者一定需要面对的问题。
近些年来学者在地方上发现大批文献,陆陆续续把文献在很大部头的文献集出版。比如贵州清水江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徽州文书、上海交通大学石仓契约、浙江大学编的龙泉档案。还有很多还没出版的文献收藏,例如中山大学的徽州文书、厦门大学与地方政府开发的永泰县文献、浙江师范大学的民间文书等等。对科教授影响比较大的尤其是家谱网,主要是上海图书馆与犹太家谱学会的网页。这些在以前看来不可思议的发展,对历史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科教授发现,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自己更多的是坐在电脑前做研究。有多少以前不到北京、东京、纽约就看不到的族谱,现在可以随手通过电脑钻研,更可以把族谱连贯到地方志、甚至这些最近发现的资料。这些发展把地方文献的利用带入另一个平台。科教授现在正在写一本总结这十多年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书,这些材料对他非常重要。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据库
但是,这些资料的出现,也有它的隐忧。历史学者从田野学习到利用现成(例如图书馆)的收藏,再到依赖出版的资料集,历史学者与他们/她们所研究的地方之间距离拉到越来越远。尽管可以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其实历史学者对文献的背景了解越来越少。地方文献脱离了地方社会,变成一种空泛的“制度”,我们很容易走回头到建构一些谁都不知道在哪里发生过的“制度”史。
科教授说需要知道读文献为什么要跑田野。1,跑田野可以启发研究者对地方的感情。2,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地方的环境的敏感。3,因为会碰到在一些长时间有人连贯定居的地方,人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知识和认同。4,因为在田野还可以看到文字资料,只有田野中才能看得懂文字资料里面有些话的意思。
接近讲座尾声,科教授对于文史机构如何帮助学者了解历史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他十分感谢技术发展下,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材料。但是请一定要保持文献的完整性,收集资料,需要用考古学的态度,考古学者往往在研究报告中写清楚文物如何出土,在哪里出土。文献需要从“制度”回到“地方”,越细致越好,具体到哪个村子,村子的哪个部分。面对今天这样一种变化,科教授对年轻学者也有一些提议。他认为带着田野的经验读文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有了现在更充实的材料,年轻学者应该开发新的研究问题。科教授说,假如他现在还年轻,绝不会陪上一代的学者去讨论那些什么国家与地方,唐宋变化之类的问题。上一代学者为没有史料发愁,这一代的学者应该为怎样面对读不完的数量的史料发愁。没有新的问题,新的资料是没有用的。我们要通过新的问题发现新的田野,因为只要一直有人在活动的地方,历史就没有停止过。
黄阿明教授认为,这是科教授对他的经验分享最为完整的一次,并认为提出新的问题其实是科教授对新一代学人提出的要求。文史研究班的成员,分别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就如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存音乐等特殊体裁的文化等问题与科教授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