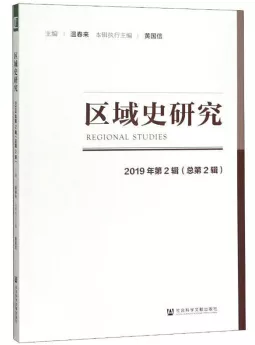
本文摘自《区域史的魅力——刘志伟、赵世瑜、温春来北京沙龙对谈》,《区域史研究》,2019年第2辑。题目为编者所加。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专门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赵世瑜:谢谢大家!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他们两位敲敲边鼓、站脚助威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本书,一本书是《区域史研究》,是温春来教授主编的,他自己也交代了;另一本是刘老师的,他自己已经做了广告,所以跟我没什么直接关系。
和他们两位有一点不同的是,刘志伟教授比较早期的研究其实就是区域性研究,虽然他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他是从广东具体入手的;温春来教授刚才也说了,他是刘志伟老师的学生,从他一开始做他的论文,就是区域史研究,但是我不是,所以我走了很长一段别的路——不能叫弯路,不做区域史研究的人是很多的,做得也很精彩。这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有更多重的体会。不管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做别的工作,一个人可能会跳好几次槽,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是对自己的挑战,当你换了一个行当以后,你再反过头看以前,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有可能会觉得昨日之非,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在比较之后发现不同阶段,你自己从事的工作或者采取的方式、接触的社会,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的不同,让你自己变得丰富了起来。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好像不太得志或者不满意,就跑了,干别的了,但是那是一时的;从长远来讲、从一生来讲,短暂的不得志或者短暂的不满意,最后都会变成你一生当中对你自己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财富。
我一开始做研究时,当我去关注某些过去不太关注的主题,就是说当你去关注官书、正史那些材料之外的现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材料非常丰富,就逼着你不断缩小你的研究范围,否则的话你一辈子可能都写不完。比如我们过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生卒年代肯定要搞清楚吧?传统的研究不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要做到这么具体。但这通常比我们关注的问题要小多了,但很多人还会觉得我们讲得太琐碎。你每看一个材料、每到一个地方,同样一个主题,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很大差别,就是俗话常说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只是把这些差别淡化掉,或者把它抹去,就是讲一个笼统的、断代的历史或者通史。比如描述某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特点的时候,可能引一段材料,也很准确,但是不会再去讲这样一个特点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是东部发达地区,然后是中部、西部欠发达地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国家还在采取很多政策,比如说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种现象叫“孔雀东南飞”,很多人才都从中西部跑到东南沿海去了,现在我们要采取措施,要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切实采取措施,留住人才,要不然差别越来越大。大家都参加过高考,有所谓“高考移民”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的存在恰恰就说明,我们中国这么大,不同的地方经济、文化水平差别大。这都是很简单,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但是在过去的中国历史叙述当中,很少能够看到对这些差异的描述。在区域史研究开展起来以前,我们大家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整体而笼统的、只沿着时间脉络讲的历史变化。在每个时间段,区域之间或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别,特别是这些差别怎么会影响到这个时间段上的整体变化,我们是很少讲的,因此也就不会知道,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时段的历史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
刚才温春来教授讲到这个刊物是他们岭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这个院建在过去的南海县,现在叫南海区的西樵山,风景很漂亮,人文底蕴很厚,在那里我深刻地领略到区域史的魅力。我去了西樵山好多次,五六次都不止。如果大家去旅游,同一个地方去一次、两次就差不多,为什么可以去那里很多次?这是后话。不过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大家有科研经费,不管做哪一段的,都愿意到各处走走看看。只是很多人去了某处一次,看见了他在书上也能看见的某个遗存,就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了,更不会几十年都往那里跑,就明白这些学者其实和游客也差不多。
到了西樵山就会知道,从温春来刚才讲到的新石器时代之后,一直到他后来讲了许多名人的明代中叶,也就是从距今五六千年前到距今五六百年前之间,还有四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知道西樵山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后来就知道了呢?因为从那以后,有了温春来讲的那些人,再加上刚才也提到的晚清的康有为,如果再远一点,还有新会的梁启超、香山的孙文。突然一下那边就出来了很多名人,好多是大家没怎么听说过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恰恰就说明,以西樵山或者南海或者珠江三角洲,甚至广东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区域,它从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晚清甚至到民国肇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以往的四五千年前相比是非常不同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它对于帝制晚期到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或者建构来说,起的作用要比以往的时代大了很多很多。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全中国任何地方都存在这类情况,比如说陕西,汉唐的时候有很多的名人,不能说到了近现代就没有了,但好像没有汉唐那么辉煌、那么引人注目了。实际上是关中地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了,即使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大家也很少提及。所以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区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俗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里肯定是有很多蹊跷的。今天在座的人,不管是专业研究历史的,还是业余喜欢历史的,既然愿意来听这么一个很无聊的谈话,我相信一定还是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一定愿意探究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动因。这个魅力就很大。
当然这个还不是当时引发我转向去做区域性研究的直接原因。刚才刘老师已经批评了某种认识,就是我们做区域性的研究,只是因为资料太多,所以选择小一点的尺度。其实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从很实际的角度出发的,没有后来这种比较理性的认识。我也曾开玩笑似的忽悠学生来跟我做区域研究,说现在做论文都要查重,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做的地方没人知道,材料都是没人用过的,别人没去过,就拿不到,所以一定不会重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对,我错了。刘老师他们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为什么?我跑到一个地方去,在当地搜集了很多地方上独有的文献,包括访谈,都是独一份的,但是等到写论文的结论、要讲道理的时候,完了,因为你讲的大道理一出来,全都是老师以前讲过的。虽然论文里的材料是独特的、新颖的,里边讲的很多人名、地名,答辩委员五个也好,七个也好,全都没人听说过,但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完了,可能也挺精彩的,最后要想说的那个道理却可能是老生常谈。所以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新史料与旧史料的问题,结论是材料固然重要,但思想更重要。
我现在也经常在问,有很多区域性的研究,比如江南地区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来讲,还是在欧美、日本来说,都是最早开始的,所以成果也是最丰富、最深厚的。到今天该如何超越呢?很多研究做来做去,核心概念变了,比如不再用当年的“资本主义萌芽”,改用别的了,研究的问题也广泛多了,比如研究江南地区的市镇,但最后讲到结论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在一个所谓现代转型的问题框架中。某个问题前人没讨论到那么细,可能是用别的词,现在材料容易找,可以讲得更细,或者用另外一套词,但是有什么新鲜的道理吗?不能是老师一提这个问题,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下空了一大半,似乎前面的研究都白费了。直到现在我的学生还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甚至感叹说:区域社会史研究好难!其实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一样难,区别在于学者们各自的要求不同而已。刘老师刚才说,你的区域怎么划定、怎么选择,是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和你的空间尺度配套的。他所说的问题就是在你划定的区域内所做研究要得出的道理。
从理念上说,刘老师刚才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不只可以使我们讲得很具体、很鲜活,至少我们的追求比这个要更大。前面的道理大家容易理解,但后面这个道理,虽然也讲过很多次,还是经常被人们忽略,总是会有人追问你们到底想讲什么。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特别是对一个也许不做研究的人来讲,很多生活的细节往往最容易被我们理解,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同情的理解。这有点像一句名言所讲的,小的就是美丽的。前几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感慨:
吃完晚饭继续看小说,皇帝说,“没有过在地方做官的见识和经验,你就不懂百姓们真正需要什么;没有见过战场的厮杀,你就不懂将士们真正需要什么。在内阁做事,不是每天忙忙碌碌地分拨整理那些奏折就够了”(《长宁帝军》)。我觉着,好些研究者还不如网络小说作家明白应该怎么去认识“国家”。
这位网络小说作家告诉我们,光去读那些国家的档案,不是说不对,但多半还是不知道在基层的社会里,官员跟普通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国家的政策措施要怎么落地、怎么见效。现在国家搞精准扶贫,要求干部帮扶到户,要求与具体的农户经常保持联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干部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的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不接地气的情况,否则就不用做这样的要求了。所以小说作家都明白,如果你只是在办公室里处理官方的文书,就能治理好国家,就能真正认识这个国家,认识这个社会,认识这些人群,那是不可能的。但恰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当中,存在许多网络小说作家借皇帝之口批评的官员那类人。
所以,先不说魅力,就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想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每一个个人或每一个人群,知道他或他们究竟是怎样经历历史的过程,恐怕不回到比较具体的情景,是很难真正有同感或者很难真正发现真实的。只有认识了这个,你才能够返回来理解国家尺度上那些林林总总的各方面的事情。我们不用担心研究区域的历史,哪怕我们选择非常小的空间,比如一个村子来研究,你就会变得碎片化,没有可能。借用我们书店外面摆的一排鲁迅先生的书里的诗句,叫“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们只要研究的是文明时代,我们做任何的很小的、很区域性的尺度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和更大的尺度,包括国家,甚至超国家那样一些制度、那样一些历史运行的法则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区域史研究》2019年第2辑目录
学人访谈
科大卫任建敏《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科大卫教授访谈》
石志杭《区域史的魅力——刘志伟、赵世瑜、温春来北京沙龙对谈》
专题研究
张侃《近代亚洲海洋网络与在华韩人独立运动的展开》
黄志繁张洪亮《科举、商业与文化:宋明以来地方家族的转型》
温春来《矿业、移民与商业:清前期云南东川府社会变迁》
张超《军阀派系政治中的中央与地方:1922年湖北省长更迭案探析》
书评
王洪评张小军《让历史有“实践”:历史人类学思想之旅》
陈鹏飞评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
李培娟探秘川西秘密会社——评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宇丹评吴四伍《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
胡宇博评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
文章来源:区域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