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入《贡赋体制与市场》,刘志伟著,中华书局2019
论学天涯远 孤怀贵相知
——追忆与何炳棣先生的一次会见
刘志伟
最近两三年,梁其姿教授好几次同我谈起何炳棣先生有意到香港访问一段时间的安排。开始,我们计划在何先生访问香港期间,请先生到中山大学做一次讲座。2010年那次,我们把细节都商量好了,后来何先生到了北京后就直接去台北出席中研院院士会,没能到香港。去年,梁其姿教授告诉我,她正在筹划何先生今年再到香港小住一段,其间拟在香港大学安排讲座,这时,我们知道何先生身体已经不如前,不便旅途周折,便设想在何先生到香港时,带中山大学所有明清史的学生专程前往香港聆教。一切已在安排中,学生们亦都翘首以待,到今年初,得知何先生因体力原因,香港之行的计划也取消了,我正为失去了再度聆教席侧的机会而遗憾,没想到不久竟传来了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愕然哀痛之中,六年前晋谒先生之情景一再在脑海中浮现。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晋谒何炳棣先生。当时,我正在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讲授明清经济史等课程。梁其姿教授素知我对何炳棣先生怀有景仰之情,请一位学生托话,告诉我何先生正在中研院,她很乐意引见。6月中的一天,我从埔里到台北的中研院史语所,梁其姿和范毅军把我领到了先生的研究室。敲开何先生研究室门之前,我心存一点激动期待又有些畏却。心存激动,是因为从我步入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门槛开始,何炳棣先生就是我心中的一座高山,有机会晋谒聆教,是一种久藏心中的期盼;有些畏却,一则是因为学界历来传闻何先生对人严厉,二则是因为我当时带着一本我在2004年选编的《梁方仲文集》,想当面呈给何先生。何先生是史学界中最熟悉梁方仲先生的研究的权威,马上就要见到何先生,自然会怀着“待晓堂前拜舅姑”的心态,特别是里面有一段提及何先生的话,我更拿不准是否有冒犯之嫌。
我写的那段话,是关于梁方仲先生对明代土地、户口数字的理解的。我说,梁方仲先生早在1935年发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时,已经初步指出过明代的田地之数,不是实际的田地面积,户口有时是指纳税户口。梁方仲先生早就指出的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数字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学术界长期被忽视,后来经何炳棣先生加以更深入的论证,才逐渐被人们认识;而在中国,即使何炳棣先生著作发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被大多数学者所了解。”我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曾忖度再三,对这样说是否恰当并无十分把握,一直很想知道何先生的看法。
随着何炳棣先生研究室的门打开,只见一位精神矍烁的老人正坐在书桌前看书。听说我是从中山大学来的,何先生马上亲切地说,中山大学是梁方仲先生在的学校,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他温厚的目光,一下子就把我的畏却和顾虑驱散得无影无踪。寒暄了几句,我就有点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梁方仲文集》呈上,他一边很快地翻了一翻,一边听我简单介绍编集《文集》的缘起。我翻开了有上述那段话的书页,请何先生批评。何先生的目光在上面扫了一过,马上对我说,“你说得对!梁先生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继续告诉我,人们对梁先生不够了解,其实,梁先生一定看过Maitland(梅特兰)的著作,熟悉Maitland的研究,必能认识到土地户口数字作为纳税单位的性质。他还表示,梁方仲先生是他最敬佩的学者,自己的研究深受梁方仲先生的影响。听到他这一席话,我所有的顾虑都放下了,轻松地谈了开来。后来他又关切地询问了中山大学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情况,我告诉他,梁方仲先生的学术传统在中山大学一直没有中断,从梁先生的几位学生到我这一代,下面还有两代的学生,一直在继承着梁先生开创的研究。他听了非常高兴,一再说“很好,很好!”
谈话中,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是梁方仲先生有没有看到他1959年出版的著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我告诉他,我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记得我1980年开始跟随汤明檖老师研习明清经济史的时候,这本著作就是汤老师指定我读的第一批书之一,汤老师还告诉我,我们系的资料室之所以有这本书,是何炳棣先生寄给梁先生,梁先生收到以后,因为是海外寄来的,就交给历史系资料室收藏了。由此我一直相信梁方仲先生一定是读过的。不过,何先生已经记不清自己曾经亲自给梁先生寄过书了,他说也有可能是通过出版社寄的。我想,事隔将近半个世纪,且当时正在冷战时期,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通信联络处于近乎中断状态下,何炳棣先生这本著作通过什么途径到达中山大学,也许已经难以稽考。但很确定的事实是,这本书在梁方仲先生在生的时候已经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当时担任梁先生助手的汤明檖老师也曾经借阅过。并且,直到葛剑雄教授翻译此书,介绍到中国大陆学界之前,大陆地区的图书馆中似乎只有中山大学藏有此书,那个时代进口图书一般都是统一购入,先入藏北京图书馆,再考虑其他图书馆的,这本书如果真的如我所知只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有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与梁方仲先生有关。我说了我的这个想法,何先生表示,他对明代以来人口田地的研究,最希望能够听到的是梁先生的意见。他一直以为梁先生可能没有读到这本著作,为此抱憾多年,现在知道梁先生生前很有可能已经读过,觉得很安慰。
何炳棣先生告诉我,梁方仲先生是比他早几届的学长,但他在清华期间并没有机会与梁先生谋面。不过,他进清华的时候,就读的是历史系,当时清华历史系是以追求中西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为特色的,学经济学治经济史的梁方仲先生当时在清华园颇有名气,他对梁方仲先生十分敬佩,所以,在清华读书时就读过梁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最能够体现历史学者对社会科学的追求,鼓励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谈话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散漫开来,记得我们谈到了一些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又与清华、西南联大和岭南大学有关的学者的情况。他提到罗应荣先生的时候,我曾想告诉他,其实罗应荣先生在“反右”和“文革”中的经历比他在回忆录中记述的情况还要悲惨,并且就在他1971年到访中山大学前后故去,并未能活到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1980年代初期。我犹豫再三,几度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我当时想,虽然对于一位历史学者来说,最希望了解的是真相,但对于一位已经历尽沧桑,年近九十的老人来说,也许不应该再在他心中增添更多的伤痛。
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我现在已经不能一一想起来了,惟有很清晰地记得,交谈越深入,自己越是沉入感动中。平日读书时,我对于那些通过他们的著作引领我们前行,照亮着我们智慧的前辈学者,总怀有一种时空相隔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在我们心中营造出景仰之情和敬畏之心。但现在,这样一位在我治学路上自始自终影响着我的学者就坐在我面前,相距咫尺,谈论着似乎可以把彼此间的生命关联起来的人与事。我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历史,身临其境地陶醉在前辈学人的精气神韵中,一种难以言喻不能遏止的情感,慢慢在全身盈溢。这种感觉,过了许多天之后,仍一直萦绕着我。
这次见面,对我来说,除了感情上满足了多年的愿望外,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白了何炳棣先生为何一直那样推崇梁方仲先生的学问成就——他们那一辈学者一直都怀有追求中国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共同志向,并走在同一条治学之路上。在梁方仲先生早已了解明代户口土地数字是一种纳税单位这个问题上,何炳棣先生肯定了我的说法,令我特别受到鼓舞,也从中领悟到学术价值与信念的力量。我相信,这种肯定乃是建立在对梁方仲先生的学术取向的理解与信心之上的。
回忆到这里,我想我应该向已经身在天国的何先生补说一声道歉。因为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何先生早就在1995年台湾出版的《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一书的《序言》中,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一直以为这本书就是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文《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和1988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书的繁体字版,我自以为早已对这一著作非常熟悉,就一直没有去阅读台湾出的这个版本。这种出于自负懒惰的疏失,令我深感惭愧!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谈一点感想,向身在天国的何先生交一份功课,以弥补自己懒学之失。
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的《序言》中,何炳棣先生谈到有关他对土地户口数字的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时,有以下几段话甚为重要,他写道:
因为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之间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隔阂……除文字外,专攻近代史的学人往往对种种古代观念和制度,尤其是赋役制度中一系列专词及其实际内涵,很难正确了解,而赋役制度通常是研究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架构。助我减少或消除这种隔阂的名家著作之中,使我最受益的是陶尼(R. H. Tawney)《十六世纪的农村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和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末日判决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后者对我这部土地专著更有直接的影响。
他在讲述了自己在陶尼和梅特兰的影响下通过长期严密的考证,论证了“亩”和“丁”的性质之后,写下以下一段在学术史上发人深省的话:
我对明清“丁”和“亩”的研究的结论既与梅氏古代海得的研究如此相近相同,照理在中史学界也应发生类似的影响。虽然自1950年代末起,我以清初之“丁”为纳税单位之说似已在西方及日本逐步获得普遍的接受,但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有不少学术论文的作者对顺治、康熙期间全国丁数的性质缺乏正确的了解,依然用以估计重建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我对“亩”的定性,经过1980年代两次扩充在中国大陆问世,至今对整个中国学界还未发生过有效的警告作用。以致近年中国大陆仍然有一系列的博士硕士论文,忝不为怪地以历代户口、顷亩数字作为区域性计量经济、社会史的重要依据。不消说,此类研究造成学术上时间精力的相当大量无谓的浪费。这种学术上对外隔阂之深而且久为讯息传播极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所罕见。
上海复旦大学史地所的葛剑雄教授,拙作明初以降人口史论的中文译者,对上述大陆上国史学界的不寻常现象注意有年,并揣想这些不寻常现象可能多少由于已故梁方仲教授集毕生精力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所收进的数据乍看之下十分丰富美备,215个统计表格一切一目了然,对研究者提供了无比的方便。葛先生进而婉转地在问:何以梁先生在此皇皇巨著的序言中对广大的读者们并未给一个最低必要的限定和警告。
虽然我和梁先生只在纽约哥大见过一面(1946年或1947年),自1930年代起,我对梁先生是一向景仰的。梁先生祖上是著名广东十三行中天宝行的主人,这可能是他一生专攻经济史的原因。梁先生是比我高八班的清华学长,新制第二级(1930)经济系毕业,拥有理想的专业研究工具。毕业后不久即成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撰柱石。三四十年代多篇论文发表于该所《集刊》、《地政月刊》等期刊,史料方面征引之广、考证之精,分析综合水准之高,当时经济史界无出其右者。梁先生不愧是当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他虽在其巨著长序之中并未明白警告读者历代户口、田地数字的实际性质,他本人对此问题具有深切了解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地政月刊》某期里曾表示对梅特兰史学成就的景仰。照理,梁先生应该是第一位有资格向专治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中外学人作一必要的警告的。他生前既不愿作这最低必要的警告工作,不得已只好迟迟由我来作了。
我之所以长篇引述何炳棣先生这段话,首先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何炳棣先生所揭示的明清田亩和丁口数字的性质,对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其学术上的贡献和启示,远远不限于土地人口统计数字的的估计和评价。何先生的研究,无论在结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几乎所有有关明清经济的重要结论,都需要重新研究。我自己对明清户籍赋役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粮”、“户”等等概念演变的解释,就是直接在何先生的研究启发下得出的。何先生提示我们要在正确了解“赋役制度中一系列专词及其实际内涵”的基础上去做赋役制度的研究,这也是梁方仲先生一生坚持的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并没有被中国大陆的学界所重视,由此引出了很多很多历史的误读误解。上面引述的这些话,在我见何先生的时候,他很强烈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当时曾令我动容。虽然我是在听其言之后才读到这段用文字写下的话,但读着这些文字,何先生当时说话的神情和声音仿佛再现在我面前,在我心中泛起波澜。
中国大陆学界长期漠视何炳棣先生关于地亩人丁数字性质的不刊之论,是一个难以令人理解的现象。三十多年来,我多次在学界同仁和学生面前表达过这种不解和愤懑。葛剑雄教授的译本出版以后,我也曾向葛教授和史地所的一些朋友请教,他们对此也似乎不能理解。这个现象,也许是目前中国大陆史学研究存在一种远离科学规范倾向的典型例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何炳棣先生在充分了解到大陆史学的这一难以理喻的现实的同时,却坚信梁方仲先生本人“对此问题具有深切了解是绝对不容怀疑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出于何先生手头有白纸黑字的明证,而是出于他对学者的素养与学术的本质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其中还包括了他对1930年代清华学术环境和风气的直觉体验。虽然我手头也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何先生深信不疑的这一事实,但在梁方仲先生的学术经历和一些零星材料中,还是有一些痕迹可寻的。
何炳棣先生告诉我,他深信梁方仲先生对土地人口数字是纳税单位的问题具有深切了解的理由,主要是他相信梁先生一定读过梅特兰关于英国的“末日判决簿”的研究。我想,这一点,首先是由于他对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重视社会科学、中西历史结合的教学风格有切身的了解,他深信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的梁方仲先生一定读过梅特兰和陶尼的著作。其次,我想他从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中,也能够感觉到曾经深深影响他自己的陶尼和梅特兰,也一定影响了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这个判断,也许是出于何先生在学术上的敏锐感觉,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事实说明何先生的感觉并非没有根据的。
除了从我在《梁方仲文集·序言》中已经引用了梁先生在1935年写下的那段话可以看出梁方仲先生早就清楚纳税单位与实际的田土人口数字之间的区分外,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总序》中,梁方仲先生也曾有写下过一段介绍英国“末日判决簿”(“Domesday Book”)的话,其中提到“末日判决簿”的调查,“对各领主及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进行登记和承认以后,便要求他们承担各种封建义务和交纳地税。这个调查对于各种各类的土地和人口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但可以肯定,它既不是全国登记,也不是全民登记”。另外,在梁方仲先生留下的读书笔记残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摘录自三种英文百科全书关于“Domesday Book”的英文笔记,这些笔记中,包括了有关田土数字是税收单位和户口统计不是全部人口等方面的内容。至于何先生提到的他自己深受影响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尼(R. H. Tawney),更是可以肯定也对梁方仲先生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梁方仲先生留下的札记残片中,夹着一张抄列着几本英文书籍的纸片,其中包括了“Tawney R. H.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1937 3.00 ” ,相信是一份梁先生在哈佛时期准备购买的书单。1946年梁方仲先生从哈佛转去伦敦大学,更是曾当面向陶尼请教,他对陶尼的许多学术观点比较认同,曾说过受陶尼的“启发不少”。这种种事实,都足以作为何炳棣先生基于学术的敏锐所作判断的旁证。
想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尽管何炳棣先生与梁方仲先生没有多少个人交往,但在学术上一直有相通的理念和追求,这种相通,基于彼此之间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关怀和理解。学人之间,这种相知相识,贯穿其中的是学问的逻辑,促长其成的是理性的魅力。吾辈后学,得入此境,则无憾矣!在晋谒何先生的时候,我请何先生到中山大学访问,他当时的回答是,他也很希望有机会到梁方仲先生任教的中山大学看看。如今何先生已经西去,未能在中山大学聆听先生教诲,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但先生则可能在另一个世界与梁先生相逢了。真希望他们相逢的时候,能够有机会一起重温民国时代清华园的学境气象,交流切磋读书研究心得,成为相知相识的朋友。这样,何先生一直以为梁先生未能读到他关于明代以来中国人口研究的著作而怀抱多年的遗憾,也就可以彻底释然了。
2012年10月21日写于康乐园
【中大史学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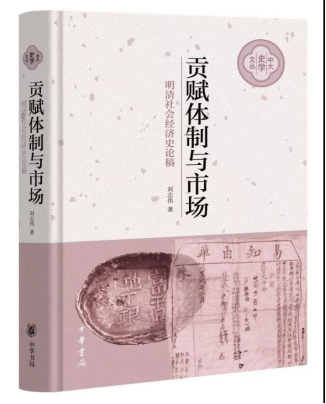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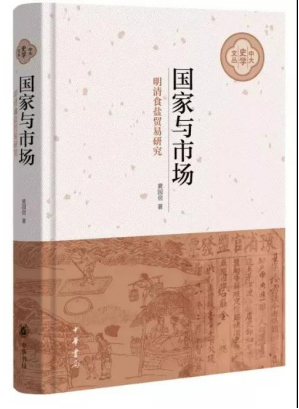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随读随写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Kcc2psgDjk77GkLbix4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