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场合,都有人询问我的研究与华南研究之间有何异同。山西大学研究近代华北社会史的专家行龙教授也曾在私下里问过我,为什么我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那些社会经济史学者相距如此遥远,却有着极其紧密的学术联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华南学派”是学术界的朋友们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的一种称呼。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成员自称“华南学派”,也很少听到对他们的研究非常熟悉的国外学者在学术场合这样讲。他们自己曾用“华南研究”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研究,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也经常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等概念来指称同样的研究,因为“华南”只是其学术主张的早期试验场。

我之所以在此仍使用这个概念(尽管打了引号),一是因为年轻朋友以此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并有相关文章公开发表,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在这些学术史研究中有着不同的表述;二是因为在本文中,我回顾的主要是与这一群体中人的关系,而把与其学术主张的关系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不好用“我与华南研究”这个题目。
说到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不得不涉及“华南学派”的定义与形成时间。在我看来,无论是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等人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周刊》那个年代(20世纪20-30年代),还是后来傅衣凌在福建、梁方仲在广东进行研究那个年代(20世纪30-80年代),都是“华南学派”的史前史,因为在那个时期,无论他们各自的研究兴趣和特点是什么,前者主要打的是民俗学的旗号,后者则主要贴的是社会经济史的标签;其背后也没有对社会科学史学方法进行反思的背景,当然,更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认为“华南学派”的形成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1991年,华南研究会成立,其基础是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
同年,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简称“华南计划”)启动,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尝试透过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一些属于本土性的观点。”
此时,“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开始成形,日后的中坚人物开始密切合作。到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可以视为“华南学派”的正式形成,这个群体的学者开始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文化自觉”。

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首先是从个人往来开始的,与学术主张无关。1987年,我首先认识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那年教育部开始设立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每个项目经费七八千元。部里非常重视,专门把申请人召到北大勺园住下,当面答辩。记得一起参加答辩的还有周积明、张其凡、汤开建等(但愿我没记错),而答辩专家有田余庆、李洵、朱雷、瞿林东等前辈学者。
支平当时报的题目就是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那个题目,后来成书后由上海三联出版。支平是很容易交朋友的,后来就慢慢有了较多的联系。1995年在北京召开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就是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现在叫和敬公主府)支平的房间里,我和陈春声互对身份证,发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那时我们只是作为年轻的特邀代表,作主报告的是刘大年、齐世荣先生,葛剑雄可能都算当时年轻的理事。
1987年对我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我拿到硕士学位,并首次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年会,算是迈进了明史的圈子。承办会议的刘秀生恰好也是傅衣凌的弟子,与李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都是师兄弟。由此我才能参加1989年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年会,但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会在山西研究方面与当时承办会议的张正明有那么多的来往。
1989年8月,紧张的气氛尚未消散,但对会议和学术交流并没有造成十分明显的影响。正是在这次会上,我首次认识了科大卫。对于我们之间当时是否有过学术性的对话,已经完全记不得了,相信应该有吧?但应该没有谈到在山西做田野或者看碑这类话题。不过,会后我们一起到五台山考察,也一起合了影,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友谊。当然我们两人也都不会想到,多年之后,我的硕士生韩朝建做了科大卫的博士生,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五台山。
1991年,中国史学会、教育部社科中心、陕西社科联在西安召开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会议的秘书组是由人大的王汝丰老师、近代史所的庄建平老师带着人大的华立、徐兆仁、北大的高毅、三联的潘振平和我组成的。由于与会代表的名额是中国史学会分配到省、各省史学会根据名额选拔出来的,一般每省的名额不超过3人,北京、上海这样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较多的地方名额多一点。会议代表平均年龄33岁,最小的25岁。我们几位虽然是秘书组的,但都是正式代表,都交了论文。
陈春声是广东省的代表,与我们同龄的与会代表还有彭卫、辛德勇等。到五年后在安徽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和陈春声都只能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

由于会议的性质,大家讨论的基本上都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比如陈春声的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数据的可信度问题,而我提交的论文是《论历史学家的直觉》,与日后所做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我们才能相识,而且巧合的是,我们当年都申请了美国的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CSCPRC,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是魏斐德)的项目资助。当时我翻开委员会出版的通讯,发现我们两个的名字赫然在目,只是在1992-93年,他去了阳光明媚的UCLA,而我去了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
我们这些人的相知基本上与我们后来共享的研究路径无关,但却应该有对相互之间学术立场的基本判断。我和刘志伟见面很晚,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大概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了吧。据他回忆,他知道我的名字并留下印象,是因为1988年夏天,电视片《河殇》热播,一时万人空巷。我因不赞同其史观,便在播出后写了《论<河殇>的历史观念》一文,与之商榷,并在《光明日报》刊出。但一年之后,形势突变,一些报刊组织对《河殇》进行批判,我不愿做违心之论,撰文指出该片的创作动机是好的,只是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比较片面。我当时不会想到——如想到自然也会觉得正常——本着学者良知的做法,为我日后获得朋友的接纳奠定了基础。
显示出共同的学术立场,或者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应该是在1994年8月于西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上。科大卫、郑振满、陈春声、梁洪生、邵鸿和我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刘志伟提交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姑嫂坟”的论文,但因当时他在牛津大学访问,未能与会。虽然此前陈春声等也参加过在沈阳举办的社会史年会,但在这次会上,社会史同行们才开始发现存在一个“田野派”,并围绕社会史的田野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如果说有个“华南学派”的话,“田野派”就是这个说法的雏形。
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郑振满。他那篇关于莆田江口平原神庙祭典与社区历史的文章给了我很大震撼,后来我去莆田去看东岳观、木兰陂,听他讲乌旗白旗的械斗等等时,脑子里都是这篇文章。说实在的,比他关于福建宗族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要深得多。不过,在那次会上,我还只是这个“田野派”的拥趸而已,因为我的文章还基本上没用过民间文献,对在田野中如何理解民间文献也基本上是门外汉。但这次会议,使我与“华南学派”的朋友们变得更熟悉,并从此变成了“一伙人”。
这次会后,我麻烦葛承雍帮忙租了个车,与科大卫、陈春声一起跑去了三原的城隍庙和耀县的药王山。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此次会议开始的8月2日,是我和陈春声共同的35岁生日。随后的9月,我开始跟随钟敬文先生攻读民俗学的博士学位。
1995年,便是前面提到的在牛津大学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同年8月,陈春声、郑振满和我又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海峡两岸社会史会,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谈了很久。由此可知,90年代上半叶对于“华南学派”以及我与这个“学派”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此后数年,我与“华南学派”的联系渐多,也是开始学习和理解“华南研究”的起步阶段。1997年4月,时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科大卫邀请我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中国城乡:认同与感知”学术会议,在那里认识了科大卫的学生,时在利兹大学任教的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和刚去西雷瑟福大学任教的柯丽莎(ElisabethKöll),也第一次见到了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萧凤霞(HelenSiu)。记得那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卜永坚还没有博士毕业。日后回想起来,那时的研究的确鄙陋,上不得台面,因此也无法真正与相关学者交流,所以,尽管彼时与这些或长或幼的学者谋得一面,但他们当时对我肯定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
同年7月,我在职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的旅程结束,博士论文后来以《眼光向下的革命》为题,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于学科的关系,我不仅认识了民俗学科的刘铁梁、叶涛,认识了由民俗学转入人类学、社会学的郭于华、高丙中,也由此结识了马戎、周星、王铭铭、麻国庆等等一批人类学者,开始接触到人类学的许多重要作品。
在另一方面,我有机会和他们、和民俗学科的学长学弟们一起去河北赵县范庄、井陉于家村、山西定襄等地进行——尽管是浮光掠影式的,但于我也是新奇的体验——田野调查。这种思想的升华和实践经验使我日后对“华南研究”的理解和学习、甚至对话有了可能,所以,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必须感激钟敬文师和民俗学科给我这样的机会。

虽然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6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但研究路数显然与“华南学派”不同。不过,我非常愿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给全国、特别是北京的学术界。1996年,我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田野工作与文献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验》一文,介绍了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的研究。他们到北京来出差公干的时候,都会来到北师大附近聚一聚。从那时开始,我便被封为他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1999年,我应陈学霖教授之邀,首次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这个时候,科大卫应该还在牛津。不过,也正是在那一次,我受蔡志祥的邀请,顺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并做了报告,题目似乎是蔡志祥建议的,大概的意思是从中国史看华南研究之类的,回想起来,讲得肯定是云里雾里。
对于我来说,“明白事理”还是很缓慢的。1998年,我因博士毕业,可以开始指导硕士生。跟随我读书的两个杜正贞和张宏艳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惜我那时自己还懵懵懂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没有帮他们打好传统史学的基础,也没有让她们去做田野、发掘民间文献,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内疚不已。
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与张宏艳合作撰写的《黑山会》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与杜正贞合作发表了《太阳生日》一文(初刊于《北师大学报》,后收于司徒琳主编之论文集),并把她送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更为扎实的学问。
这些事情无非是说明,在90年代的后半叶,我只是与“华南学派”的某些人成为了朋友而已,与他们的学术主张可能还只能说是“貌合神离”。直到大约十余年前,我曾在某次田野过程中,对郑振满说:“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了!”
进入21世纪,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进入了第三个、也是崭新的阶段。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成立;同年,萧凤霞也在香港大学建立了社会人文研究所,这些学术机构的建立必然导致一些研究计划的开展,也加速了我与“华南学派”的密切合作。本年12月,科大卫、杨国桢、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范金民、曹树基和我,以及若干研究生,从广东湛江一路行至广西北海及中越边境的京族三岛,其间所见所闻所议,已见诸张小也所撰《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一文,不赘述。
好像就是利用这次机会,张小也抓住科大卫、郑振满和我,做了一次关于碑刻资料的访谈。那个时候,科大卫已经有了在香港搜集碑刻资料的经验,而郑振满和丁荷生已经在将他们搜集的碑刻编辑成《福建宗教碑铭汇编》,而我也开始搜集、抄录北京的东岳庙及其它碧霞元君信仰的碑刻。访谈于2002年1月刊登于《光明日报》,大约因此成为朋友们戏称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的由头之一。
2002年,我们一起参与和筹划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那年3月,在做清水江研究的张应强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到了黔东南的锦屏县。那时交通不便,我们从桂林乘车出发,在山路上颠簸了1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从县城乘船沿江而下,登岸后接着翻山,到了苗寨住下,便已天黑了。那是我第一次住在干栏式的木屋里,也第一次在各家各户见到日后大放异彩的“清水江文书”,结识了像锦屏方志办王宗勋这样的朋友,感受到了苗族同胞的热情款待,也引发了我对清代西南边疆开发程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在我的《社会史研究导论》课上,每次都会提到这个例子,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区域历史勾连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范例。
这年8月,我到上海参加了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记得在会上,梁洪生介绍了他参与华南研究田野调查的经验体会,森正夫先生、王家范先生也就此话题做了报告,我则针对一些误解,解释了“华南学派”的区域研究之目的,实则是为了重写中国史。记得滨下武志先生接着我发言,进一步发挥说不仅是为重写中国史,还是为重写东亚史,重写世界史。
12月初,《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一次关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会议,记得与会者有葛剑雄、商传、于沛、陈争平、虞和平、谢维扬、梁其姿、彭卫、汪朝光、黄宽重、梁元生、苏基朗、王子今、陈永发、马敏、陈红民、张国刚、金观涛、刘青峰、郭少堂、杨奎松、吴景平、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王和、宋超、徐思彦等人。
此会主题虽与“华南学派”无关,但前期的筹划却是由陈春声、刘志伟、徐思彦、王和与我共同参与的。在此次会议筹划过程中,《历史研究》主编张亦工兄极为支持,但却在会前查出身患癌症,于半年后便英年早逝了。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历史研究》杂志在将“华南研究”的影响推向全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香港会后,我们这伙人跑去了海南岛。八年后,贺喜在她的著作《后记》中回顾这次海南之行,感叹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但对我来说,那时发生的一些事彷佛就在昨天。就其深远影响来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去了许多冼夫人庙、五公祠、丘浚祠堂和海瑞庙,也不是在五指山区跋涉时大家纷纷扎紧裤脚,以防山蚂蝗的叮咬,而是晚上在房间里的讨论。
那个时候,虽然可能讨论声如雷贯耳,但滨下老师却可以在一听啤酒下肚之后,坐在椅子上安然入睡。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因缘巧合,我主动承应了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这个连续举办了13届才告一段落的研修班,不仅是许多人将我视为“华南学派”代表性成员的重要因素,也是日后“田野工作坊”这种形式在中国大陆逐渐流行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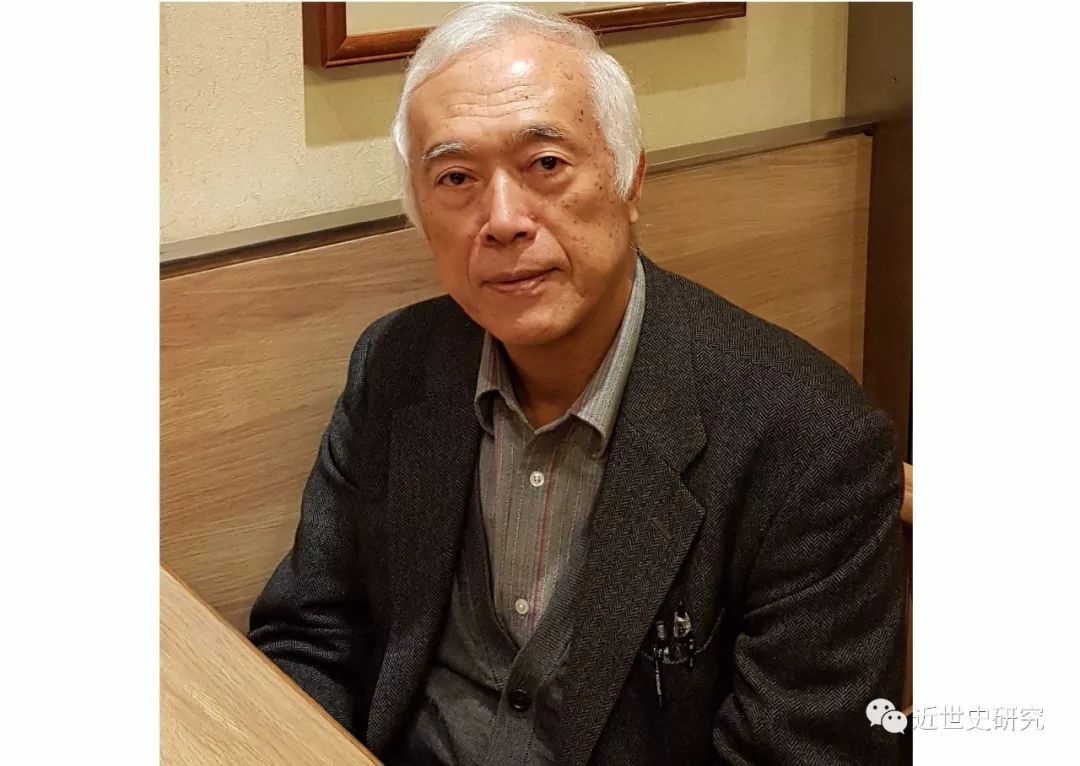
2003年暑假中,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在北师大举办。这个班的经费是由萧凤霞的港大社会人文所提供的,包括教师和学员的食宿、旅行费用。还有部分费用给学员回去后完善自己的研究报告。研修班举行10天,前5天在北师大授课,学员主要是各地的年轻学者,讲者包括人类学者萧凤霞、庄孔韶,社会学者孙立平,历史学者科大卫、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我等。后5天到河北蔚县考察,形式是白天全天做田野,晚上19:30-22:30各组汇报和自由讨论。整个日程很满,也很辛苦。南方来的人水土不服,比如温春来严重腹泻,不得不半夜去医院急诊。
当时的蔚县还没有成为华北的旅游热点,著名的剪纸也还不是“非遗”,条件好点的宾馆似乎只有一家。不过令我们惊讶的,除了壮观的北城楼上的玉皇阁外,还有乡间那一座座格局基本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的堡城,堡城内的庙宇及其中的壁画、皮影戏台和清代的题壁。记得学员们冒着酷暑,一起把以前埋入地下的几块巨大石碑拖出地面;记得卜永坚背来厚厚的几册《蔚州志》,边走边读,回香港后就迅速写出了文章刊出;也记得因为我们考察风景秀丽的飞狐道以及“空中草原”时,要求严格的科大卫认为有“旅游”之嫌,愤而将笔记本电脑摔在地上,吓得陈春声边说“不干我事”边躲得远远……,总之都成为多年后茶余饭后的谈资。
第二、三、四届高研班都是由我承办的,授课都是在北师大,田野点分别安排在临汾、济源和晋城。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般都会先去踩点,比如2004年春天,我和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先随田宓(时为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去了内蒙古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然后又去了洪洞等地。可能是由于过于疲劳,2006在晋城期间,我在府城村关帝庙里突发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所以随后的第五、六、七届高研班,便都由中山大学接手承办,我也是间隔了两届,到第七届时才跟随去了江西万载,第八届在陕西韩城举办时,又由我来承接。故此,谢湜戏称我为第一、二、三、四、八期“校长”。
我之所以认为2002年底的海南之行十分重要,就在于当时决定了开办这个高级研修班。连续13届的这个班,参与学习的学员总计达数百人,有不少已经是教授、博导,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各自的领域中的青年翘楚。无论他们是否继续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但历史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必然对他们产生影响,并藉他们得以传承和发扬。因此,我坚信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会有这个班的一席之地。在整个过程中,萧凤霞在办班经费上的支持、科大卫全心全意的参与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诸友的核心作用,当然,还有我的历届学生们的辛苦,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我个人来说,早在90年代初,“华南学派”诸兄就在珠江三角洲、潮州和莆田等地开展过类似的活动,虽然并非对年轻人的培训,但田野经验要丰富得多,无论是在现场解读民间文献的能力,还是发现问题的能力,都远超于我。郑振满在读碑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着许多年轻人,听他讲自己的见解,所以被誉为“碑神”。
科大卫自发表了《告别华南研究》的宣言之后,他的眼光当然不会限于珠江三角洲,对整个中国的不同地区,都怀有极深的兴趣,以我熟悉的山西来说,他就写过关于长治、夏县司马光家族和代县鹿蹄涧杨氏家族的故事,在每次高研班的10天里,我们边走边看边讨论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当然,类似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我们自己办的高级研修班。由于我们的做法效果比较好,时在台南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吴密察联合成功大学也举办了两期类似的田野研习营,邀请了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和我去授课,并以台南府城为田野点。后来中研院的李孝悌和王鸿泰在金门也举办了数次田野研习营,也是请我们授课加随同田野,与我们的模式相同。对于我来说,虽然不能像郑振满、陈春声他们那样将在地的经验与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但也促使我思考了许多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我必须庆幸前几年一时兴起写过几篇博客,记录了我参加这些活动时的点滴收获:
……这次去台南是在那里参加吴密察教授组织的工作坊。他和他的同事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我于是有再一次到台南游历的冲动。此外,这次不是我一人乱跑,而是有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很有田野经验的朋友一道,不是客气,我又学了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我正在写清初郑氏政权据台那部分历史。
我们和学员们观察的空间范围,就是清代台湾府城的范围。这是荷兰人在此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郑氏及其日后大陆人来台的第一个据点。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性时刻”,这里就代表着台湾;而在17世纪中叶的前后,台湾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地点”。这就是施琅、以及最终清帝国没有放弃台湾的意义所在。
从台南起步,重新理解台湾史,再重新考量我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和“历史性地点”,似乎是实践我们这些人的所谓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理念的又一个绝佳选择(取自2007年8月30日的博客)。
另一篇是:
在台南的第一天上午还去了开基武庙和大天后宫。……

开基武庙的院子里有块新修的碑,讲一个灵验的故事。大意是说,全台湾到处都有武庙,但只有这家最灵验。因为清嘉庆年间关帝在这个关帝港宫后街的地方留下文字,让大家敬神,这个字迹被彰化的一个生员得到,又把它写回到福建泉州的关帝庙去。那么关帝这段话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云游到此,特有数言传布人间,速进纸笔来!吾乃大汉关云长也,奉玉皇命,巡察人间善恶,云游到此,适见汝辈戏演吾像,以供笑乐,不忍不教而诛。夫演戏祀神,将以敬神也。敬神而转以慢神,于心何安?吾居天阙,掌天曹,位列奎缠之舍,职分挂籍之司,眼见世人图予像,塑予形,朝朝崇祀,亦可谓制有礼者矣。然至酬愿、供神、演唱之间,每以予形为戏,侮不敬之罪,稍知礼义者,忍为之乎!剧本多矣,何必戏演吾旧事?吾本日特来附乩,汝辈可以传布世人,互相劝戒,切勿以敬予者时而戏侮及余也。信予言者,积善获福无疆;慢予言者,侮辱必遭天谴!速将吾谕言贴文衡殿通晓。”
据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本地鼎行演唱三国戏的临江会一折,香炉中冒出火光,还未引起大家警觉,最后扮演关帝的演员忽然乱跳起来,拿手中的木剑乱砍扮演鲁肃的演员,最后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云云。
这个故事本是士绅编出来,对民间祭祀礼仪的不合规矩表示不满。这些士绅不知怎么和庙里的人、甚至唱戏的演员串通一气,制造出这样的“神迹”。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唱戏酬神的方式,而似乎是反对演本神的戏来敬神。但最可疑的是他们还要把这件事闹到海峡对岸的泉州去!不到别处,到泉州?
我不懂台湾史,但有点怀疑那位叫林光夏的彰化生员的居心绝不仅在于匡正风俗。我查了下道光《彰化县志》,里面没有发现这个人的痕迹,倒是知道彰化有大量闽南、包括泉州的移民。再查康熙末《台湾县志》,这关帝庙早在明郑时就有了,但在地方志中并未被列入《典礼志•祭祀》的部分,而被列入《杂记志•寺庙》,只是简单记载“小关帝庙,伪时建。五十八年,里人同修。在小关帝庙巷内”。可见其正统性是有点问题的。后来比较火的是东北面一点的祀典武庙,也有一些碑文留下来,但这里的碑文却只是嘉庆二十三年的,也就是上面说鼎行演戏出了神迹的两年后!
我怀疑当年关帝港之得名本是由于这个小关帝庙即今天之开基武庙。“又坊里庙祀甚多: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关帝庙,伪时建”(续修《台湾县志》卷2)。那个比较大的关帝庙由于当年有明宁靖王留下的匾,一批批心里有想法或者有愧的汉人官员纷纷来此贡献力量,名气自然就大了起来。
乾隆末林爽文起义及其被清廷平定,导致台湾社会结构的重组。我不肯定是否有一批家伙势力重新崛起,希望重整河山。他们告诉大家,你们过去某些事做得有点离谱,而我们这样做才符合规矩。当然我估计他们这样做倒也没有多大的胃口,无非只是为自己多争取一点生存空间罢了(取自2007年9月15日博客)。
除了因办班而跑田野之外,我们也跟着学生们的论文选题跑田野。比如2004年,我们到了湘西的凤凰、永顺;2005年,我们到了晋东南的晋城、阳城、高平和晋南的闻喜、夏县,以及雁门关和代县,云南大理、还有浙江温州;2006年,我们跑了灵渠沿线、大藤峡和金田;2007年,去了河南博爱……。无论是谁的学生,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几个人都是一起跑的。因此不仅学生获得锻炼,得到老师们的指教,就是我也获得了不同地方的“地方性知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仍可以当年的一篇博客为例:
今晨6时许从桂平出发,乘船去广西中部的大藤峡。

这个地方是是读明史的人,甚至读思想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因为它与王阳明的事功有关。史书里说那里的瑶民用山中的巨藤把江面封锁起来,官军难以攻取,后来明军打了胜仗,砍断了大藤,这里就改称断藤峡。当然王阳明志不在此,他的志向不在破山中“贼”,而在破心中“贼”。
本以为这里的峡谷两山壁立,古木参天,中间一条深谷,古代的瑶民在此间纵横,官府莫可奈何。但入峡之后,虽然时遇激流险滩,但江面开阔,两岸山峰大多较为平缓,复因高大树木被砍伐殆尽,多是近年来新栽种的林木,全无古藤绕树的景象。阳光毫不吝啬地扑洒下来,眼前的一切清晰无比,不禁多少有些失望。……
看了点文献,知道明永乐初开始瑶乱不断,这个瑶乱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因?我不得而知,但却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整治。或者,是朝廷开始整治这些边陲之地,然后制造出了这种种借口?最后的结果,是外来人日益进入,在明代有从贵州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清代有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逐渐成为化内之区。
事情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三言两语那么简单,但究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还是一个“内”与“外”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狼、瑶、壮、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格局?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果,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300年后,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起事的人就是从外面来的客家人,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那些土著与当年瑶乱平定之后的人群有何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重要的是,从明后期始,国家就在那里,不慌不忙,延续着明代以来的国策,没想到这个太平天国竟然如此影响帝国的筋骨,一个多少地方性的问题终于演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这当然就不是单一的区域史因素所能解释的了(取自2006年10月6日博客,文字略有改动)。
我甚至在2012年抓了刘志伟的“壮丁”,请他带我去跑他当年做田野的珠江三角洲村落,比如著名的沙湾,不止从文章中了解,也亲身体验他所描述的沙田区和民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市场中心、聚落形态、祠堂和庙宇。我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仅仅靠读文章,是不能准确理解他的结论,乃至研究理念和方法的。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20多年与“华南学派”的密切往来,固然不能说我只能闭门造车,或者只是在山西兜圈子,但肯定不会对香港、台湾、珠三角、潮汕、莆田、黔东南、西江流域、温州,甚至江南地区有那么多了解,更不用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了。这些经历使我坚信我们的尝试是有益的:不止是在故纸堆中理解历史,而且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历史;不是在一个画地为牢的时间(如王朝)和空间(如民族国家)中理解历史,而是在能够说明其意义的时空范围内理解历史,并寻找其与其它时空范围的联系;不是专注于颠覆(比如在国家-社会、中心-边缘等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专注于常态。
当我回答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这类问题时,我的表述是,我与“华南学派”共享某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平台。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妨碍我们之间具有各自侧重的研究风格和叙事方式。在这20多年里,我也亲眼目睹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变化,直率的批评和用心的善意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原来可能不太认可的东西。

但是,界定目前的历史学界究竟谁属于这个“学派”比较困难,我们这些人也从没有考虑过发表一个类似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词》那样的“共同宣言”,我更珍惜的是我和几位老朋友之间几十年的友谊,这比是否属于同一个“学派”更重要: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一个很难被骗到的人,但别人不小心会被他“骗”到。他会因听到弱智的言论却不便反驳而憋得满面通红,嘴唇哆嗦,但也会经常露出狡黠的笑容。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很难受别人意见左右的人,做事绝不拖泥带水,讲话总是有个性的。一般以为他较欠生活情趣,但听过他在悠闲漫步中哼唱小调的人,会略略窥见他隐藏的内心。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可以用《纪念白求恩》里的话来表扬的人,热爱生活,有一点小资情调,这可以从他喜欢美食和点菜看出。虽然他的父母都不是广东人,但他却像是个浸染了300年广州文化的广州人。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人,他手里总是拿着茶杯,说明了他的某种严谨。他是个很好的教师,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学生总是能诲人不倦,而且是因为大家公认他讲话的录音整理比他的文章漂亮。
对其他或年长、或年轻的圈子里的朋友,恕我不在此一一点评。而我本人则泛善可陈,想到的只是我一贯的简单、粗暴、妄言对朋友和学生们的得罪,许多年来,一直心存愧疚。
本文原刊于《文化学刊》15年10期


文章来源:赵世瑜 近世史研究 本文原刊于《文化学刊》15年10期

微信号 jinshishiyanjiu微信号 jinshishiyanjiu
微信号 jinshishiyanj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