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范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所著《明清江南史丛稿》于今年上半年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上海)有限公司出版,“新史学1902”今日继续连载该书代序《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如何在学术与社会之间平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王先生的思考无疑颇具深意。感谢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上海)有限公司授权发表。
挣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汇入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大潮,这对具有世界罕能相比的中古传统的中国,无疑是一掀天揭地的大事件。它不仅在经济领域撞击出一连串的裂变反应,而且使积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经历着剧烈的震荡。整个社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变迁,使人眼花缭乱,又处处牵动人的神经。社会的行动,现实的变迁,总比我们设想的更少理性。在激动、混乱的嘈杂之中,往往充满着野性。身处这一历史变局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会显得特别的不平静。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也许是出于“职业特点”,他们更追求和谐、理性与完美。因此,当他们面对现实的社会变迁时,往往变得躁动不安。一些人文学者,因追求和谐、理性与完美而呼唤改造社会和国民,渴求振兴中华的变革,但当变革切切实实在身边展开,变得可以捉摸、可以体验时,面对五色缤纷、光怪陆离的新旧嬗变,他们又觉得有太多的始料不及,不尽如人意。于是就有了迷惘、沮丧、困惑和失落。说起来,真是让人难堪,叫人莫解,不可思议。
最近,有好几位学者,以深沉且带有些许悲怆的口气,发表他们对现实变化的种种意见,其间,还不时流露出几分孤傲和轻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面对社会的震荡与变迁,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是否应具有坚定的理性,多几分平静和冷峻,少一些浮躁和盲动?既然人文科学是关于社会组织和人的行为怎样符合理性的学问,是关于如何养成一种良好的社会人文心态的学问,那么,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且有两个基本方面是丝毫不能忽视的。
知识分子要历史地、理性地理解变革
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在设计并贡献各种回应变革的对策时,最好能温习一遍古今中外已有的历次变革,以期对社会变革能有一种知识界特有的冷峻,以坚定的理性对待变革。有感于人生的诸多烦恼,有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场经历。其实,由个人群聚而结成的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为解不清的“社会情结”而苦恼、而调整、而变革?诸多的社会两难命题,如群体与个人的矛盾对立、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对立、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对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对立,以及人自身的本能与意识的矛盾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对立,一直在考验着人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架永远找寻不到平衡、处于摆复中的“天平”。种种的阴阳两极相运,过分倾斜到哪一头而舍弃另一端,社会都难得安宁,人们也不会感到满足。
就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的、中世纪的种种“不合理”的倾斜和压抑,做一种尝试性的调整呢?已有的历史经验足可以证明,社会的变迁,如文明取代野蛮、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都是得失相兼、利弊俱生、善恶共荣共存的。市场经济变革除了带来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物质的富足),也必将混杂着污泥浊水,叫人们一口吞下,不消受也得消受。早在20世纪初叶,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法、德、美之后,凝聚其精要的体验思索,发表了一席至今读来仍震烁人心的宏观高见。他一方面预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另一方面又深致忧虑,谓“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且曰:“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这是谁都得经历的、无可逃遁的变革的历史代价。明乎此,眼前的诸多不尽如人意都显得淡淡的,一切均在必然中。
梁启超说过,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叶扁舟,初离海岸线,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现今之中国,情境虽不同于近代之中国,但仍是一个“过渡时期”,迷惘与困惑自也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患得患失、顾影自怜,何不以一种平静明智的态度,去观察那些为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旧事物是如何随潮流而去,而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是如何产生和生长的呢?变革,将是无穷无尽的,如危崖转石不达平地而不止。新旧交替,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事物,终究会被无情地割舍。变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只处于航程的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初级阶段”。因此,不必苛求变革,也不必苛求自己,一代人做不到的事,后一代人一定会去做。

《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王家范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知识分子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
变革是全社会的事业。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首先就应该抛弃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或霸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于此前所有的社会变革。它首先是世俗化,大众广泛参与的程度前所未有;其次是由单一的机械整合转向高度分化的有机整合,即社会趋向多极化、多元化。反观已有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经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程度不同、形式不一地朝着愈益世俗化和高度分化的方向转轨,旧秩序和传统无不先后崩坏,而新秩序的确立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现代社会变革犹如一台大戏,生、旦、净、丑各角均不可缺,编导、美工、乐师、内勤俱有建树。摧毁传统秩序,营建现代社会,政界、商界、文化学术界的彦硕名流固然占尽风流,但贩夫走卒、芸芸众生,自亦有他们的一份血汗、一份贡献。
譬如近十几年崛起的民间坐商行贾,人们固然有理由瞧不起他们,刻薄他们的贪婪、卑劣和庸俗。然而,在经济的变革中,由他们演奏出的不谐调的“流行曲”历史不会不记载,不会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对他们,与其刻薄之,倒不如多一点理解,仔细地去体察一下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时内心的苦涩、烦恼和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莫名与无奈。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人不论是伟人名流,还是凡夫俗子,归根到底都是断不了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肉体与灵魂合一的“人”。在现代社会,我们理应更尊重每个人对生存的选择和争取生存权利的努力,少一点贵族式的文化偏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传统久远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人因为占尽了物质和权力分配的优势,很少分化和另谋他业。时至今日,这种分配上的中世纪优势已是明日黄花,“良辰美景”再难追回。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知识分子面临着高度分化的命运,需要做出各种选择。近十几年来,知识分子先是经历了从政风——许多人满怀信心,以为知识分子从政一定能别开生面,而后来不知为什么对从政又颇多非议与指摘。其后是迎着商品经济大潮的从商下海风——这至今仍拨动人心,只是蔑视、调侃以致公开斥责的议论逐渐多起来了。
其实,议论和斥责,皆大可不必。人各有志,人尽其才。知识分子从政经商,为这些领域增添新鲜血液,提高文化素质,贡献智商、谋略,不都是营建多样化的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吗?物竞天择,大浪淘沙。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成不了大事,做不成善举,会被淘汰或淹死,却也不足以成为杞人忧天的理由。成功者毕竟会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逐渐变得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从长远看,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正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
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假如你是甘心选择这一清苦的事业的,那就应该既来之则安之,潜心于学,无事喧哗,不计毁誉,安贫而乐道。“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陈寅恪语)前辈大师既已讲得如此明白,新进后学似亦不可再作他图了。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不求闻达,自甘清苦,亦是一功。总而言之,自己走自己的路,也不必菲薄他人。
泛指的人文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但严格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应该加以区分的。研究人文的学者,往往超脱具体的功利和时空,将“天理人性”看作“有一无二,有同无异”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追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和体验都具有个体性和时代性,但他们内心所服膺的,则是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境界。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的难题和操作路线,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可行不可行,有利与无利,往往是他们最煞费苦心思索的。他们比人文学者较少浪漫色彩,奉行现实主义。然而,现在有些人文学者,视社会科学注重应用与操作为雕虫小技、急功近利,这就是大谬不然了。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往往交互为用,各具千秋。但与传统社会所不同的是,目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潮流。讲求效率和效益,能使现代化社会比传统社会产生高得多的生产力和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利益机制就是比道德机制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约束力。这一点,我们正在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无可奈何地被迫承认,这是现代化社会运行难以抗拒的一条法则。现代中国,更缺的,或者说更迫切需求的,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全面发展的操作设计和实践对策。基于义理又合乎国情的、有真见卓识的社会设计与对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愿意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际,敢于碰我们不熟悉的社会问题,敢于贡献思虑甚深的实践方案的学者也太少,很不够用。这样说,丝毫没有菲薄甘心从事纯学理、纯人文研究的学者的意思。例如提倡新儒学、新国学的学者,不囿功利,不求闻达,不苟合于时潮,就像陈寅恪、吴宓那样,“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救人心,挽世道”,是很值得全社会敬重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要敢于直面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有机整合的现实要求,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如泰山不让土壤而能成其大,如河海不择细流而能就其深,特立独行,不废古今,由此而涵养的文化精神必将惠及当代与后世。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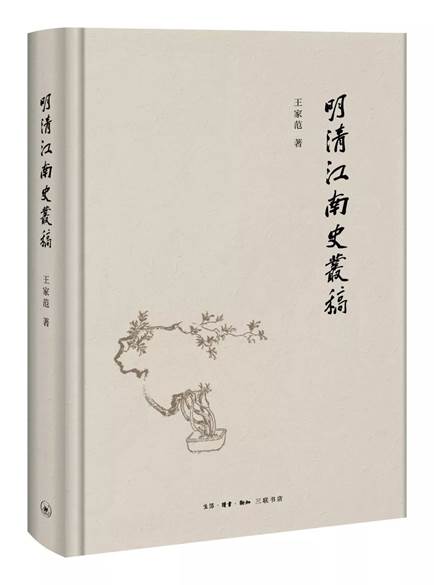
原创:新史学编辑部 新史学1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