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建立在对传统民族史反思的基础之上,其族群研究以边缘看中心为视角,以社会记忆为研究路径,并强调反思性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族群研究的概念体系,即以“文类-模式化叙事-历史心性-现实情境”来分析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提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民族史新见,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但其研究中也存在疏于考证、史实未清等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辨别与警惕。全面评析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王明珂先生的民族史研究贡献,还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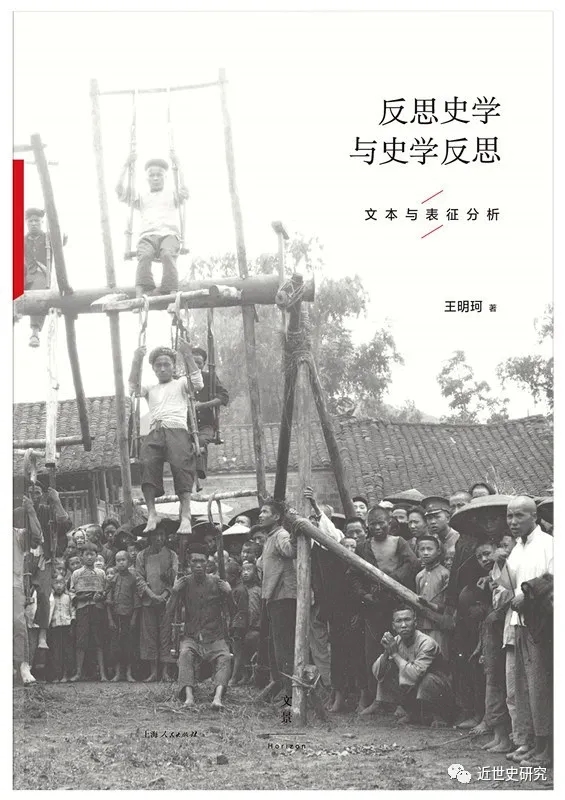
王明珂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边疆民族史名家,他的“华夏边缘”系列研究一经推出,迅速在两岸三地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其著作至今畅销不歇,以至于洛阳纸贵,不得不一版再版。内地学者为此有过不少相关学术述评,然而目力所及的这些述评大多是王明珂单本论著的评价,很少将他的边疆民族史研究进行整体考量评析。王明珂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屡次申明:他的多部学术论著之间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若孤立地评价其单本论著,这既不利于观察他的民族史研究全貌,也有悖于王先生的初衷。职是之故,笔者不揣冒昧,将王明珂先生的系列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置于中国民族史的学术脉络中去考察评价。疏漏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之所以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就在于他的研究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并运用了新视角与新方法来探析边疆族群的生态历史。相较于其他民族史研究而言,王明珂主要运用了“从边缘看中心”的新视角与“在文献中作田野”的新方法。
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范式是先验地将“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体质、语言、考古遗存等客观特征的实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的定性分析。但通过王明珂的梳理与论证会发现,“民族”形成的所谓客观标准并不能让其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族群”。他进而认为主观认同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人们会因为资源的分享、合作与竞争而不断扩大或缩小“族群”认同的范围,这就造成“族群”内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认同变迁。在此逻辑下,族群的边缘人群与现象成为解析相关民族的关键。即王明珂所强调的研究转向:民族史的重点应该从“民族”的内涵溯源转向“民族”的边缘研究。
民族的边缘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王氏看来是“边缘”定义了族群的范围与边界。正如王明珂用“圆形”来比喻“民族”一样:“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只有深入研究了华夏边缘族群的认同及其变迁,才能更好地了解华夏族群的历史内涵。
“从边缘看中心”相较于“从中心看边缘”的另一优势还在于研究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观察到边缘人群具体的认同变迁与情境变化。就像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杆,木杆半燃半熄,而我们可以细致地观察燃烧节点的变化。燃烧的推进过程就像族群的演化与变迁过程,研究者就能尽可能地返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族群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探寻“民族”或“族群”的形成过程。
正是在以上族群边缘理论的引导下,王明珂探寻出了羌在汉藏之间的社会情境,揭示了羌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一截骂一截”的社会现象。同样凭借族群边缘研究,王明珂将具有共性游牧特征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等族群置于汉帝国边缘的社会情境之中,透过各个族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治、经济抉择,分析出汉代华夏北部三种不同的边缘族群类型,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
在文献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是王明珂利用文本、文类、模式化叙事、历史心性、社会表征、社会现实等概念来揭露隐藏在文献背后历史情境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将历史文本当作古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下创作的社会记忆,历史本身情境与历史时期人们留下的社会记忆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有别,但是社会情境与社会记忆有其对应的关系。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社会情境的能动反映。
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通常强调实物与文献的互证,这既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也是民族人类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从事民族语言、体质与文化调查的民族史学者,在边疆地区进行大量的实物采集与分析,这是传统民族史学者研究工作的重点与常态。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边疆民族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与汉文化不同的的族群文化。在此情况下,民族实物与民族文化表征为人们识别、划分不同民族提供了有力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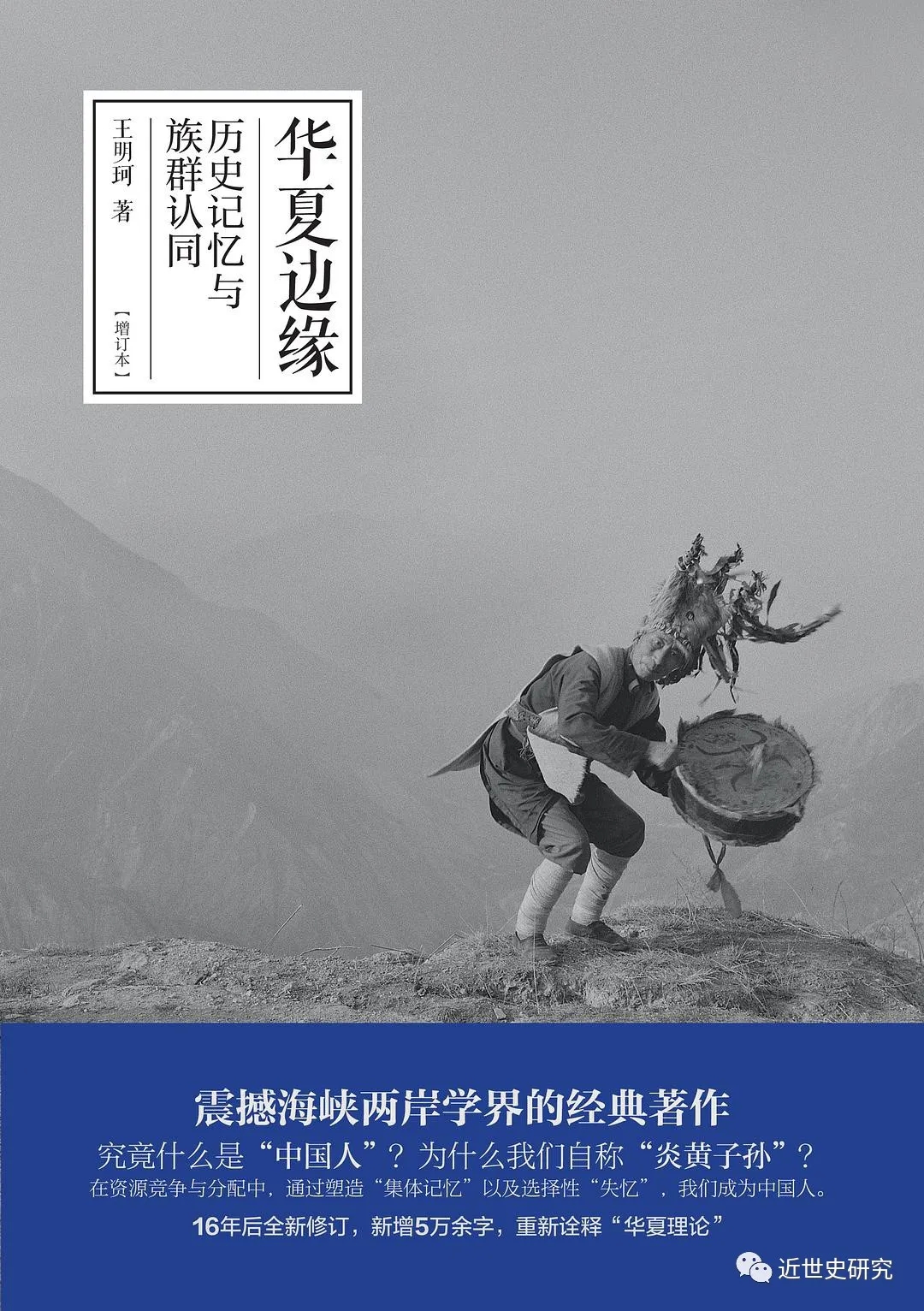
而王明珂的“在文献中作田野”研究方法则将历史文献、考古器物以及实物表征皆视为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遗留下来的社会记忆,强调承载于文献与器物之上的社会记忆如何让被利用、强调、遗忘、选择与重组,而并非将文献与器物视为十足客观、无偏颇的史料来运用。这种“史料反思”的精神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得到彰显:“《华夏边缘》所提出的一种史学研究取向,便是根本改变对历史文献或更一般性‘史料’的看法——我将它们视为人们在其社会情境下,循着既定模式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失忆与想象。”王氏在这里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不是止步于史料的外缘考证与选择组合上,而是深入到史料产生的社会情境中去探赜古人的真正处境,努力做到了“了解之同情”。
为了保证“在文献中作田野”的客观性,以及为了实现对边疆族群的“了解之同情”。王明珂还深入到田野中进行实地调研,在进行口述访谈时,他尽可能地摆脱带有偏见或先验观点的束缚,正如他所强调的:“我读过一些人类学的著作,熟悉相关理论,但是到了田野我不是跟随那些理论,不是为理论找证据,而是跟随着我的问题,理论只提供一些探索方向。”口述访谈活动结束后,其所得的口述资料也是从录音逐字逐句转译而来,确保最大限度地保持原始访谈材料的原貌。此外,为了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王明珂还有意采用多点观察的方式了解研究对象:“我做调查的情况也比较特殊,那就是,我从不在一地久留,而是采多点、移动的方式进行。”将这种多点观察法进一步引申就会发现,王明珂的研究缘何能新见迭出,就是因为他在进行边疆民族探究时采用了的长时段、跨族群的共性比较研究。
除了运用“在文献中作田野”的研究方法外,王明珂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后现代理论等学科理论的优势。并将这些理论方法内化为自己的研究素养,尽可能做到不被理论牵着鼻子走。当被问及诸如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在自己研究所充当的角色时,他回答道:“人类学对我来讲,只是认识‘历史’现象的工具而已。我也吸收社会学、心理学、后现代研究、文化研究与诠释学等研究中的精髓。”理论方法与概念工具皆是为了深化自己研究的而采用的,它们仅仅是研究的手段,绝非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传统的民族史研究侧重于民族溯源及其相关定性研究,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范式长期得不到革新与省思,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而王明珂的系列边疆民族史研究成果宛若一束久违的阳光,给中国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概而论之,王先生的边疆民族史新见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一)“国族主义实体论”与“民族近代建构论”的反思推进
通过分析传统“国族主义”下产生的典范民族知识与“民族近代建构论”的学术主张及其影响,王明珂发现二者皆存在明显的不足。譬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北方边疆民族史,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史研究范式下的产物,其强调长城内外的民族区别差异与华夏驱逐鞑虏的历史记忆。如此这般的典范民族史知识,其穿凿附会之处不仅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之风下略显无力,而且亦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今日满、蒙等边疆族群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民族近代建构论”者则认为民族与民族国家皆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华夏族群、中华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也都是近代时人所建构的。王明珂明确反对这种“解构”式的研究,他认为后者并未深入到族群历史与田野中去考察人类族群认同的本质,也没有考虑到“现在”在长时段历史中的人类生态意义。而对于这些,王氏已然有了更新、更高的认识。因为他通过长时段的族群互动历史的考察,理解了所谓“民族国家”并非近代的想象,而是贯穿于中国几千年族群历史之中。此外,他也从近代羌族人群因为族群的攀附与歧视而导致的倾轧互斗现象中深有感触,更加认定其反思性族群认同研究的重要性。
针对以上两种学术理路存在的问题,王明珂进行了建设性反思。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王明珂力图呈现一部因边疆族群与内地人群互动与抉择下长城逐渐消失的历史。自汉代至近世,靠近长城的北方游牧族群始终无法脱离长城内外的资源。凭借此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我们不仅深化了边疆族群的互动历史,更是从中理解了华夏边缘在形成与变迁过程中的延续与断裂。此外,王明珂认为“民族近代建构论”者忽略了族群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因此在其研究中,他着意强调了族群历史书写背后的社会认同情境与真实情感意图,此举就是为了突破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藩篱,进而实现人文现实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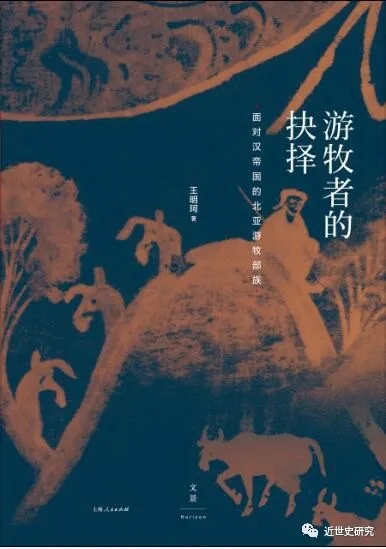
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观点认为,民族或族群的成员内部具有较为一致的客观特征,如在语言、体质、血统、文化等方面具有共性。但王明珂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所谓的特征并不能作为定义族群的客观条件:“无论‘族群’或‘民族’皆非客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基于此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常受到质疑。”这些客观特征是人们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因为人们对“同胞”与“异族”的体质、肤色、语言的异同看法是相当主观的。
王明珂在受到挪威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的启发后,认为客观文化特征至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普遍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问题,更无法深入探讨族群认同的变迁。所以,要研究族群的认同变迁与边界问题,势必要研究族群内部人群的主观认同。主观认同看似运用的是一种主观标准,但因为其符合人们真实的内心诉求,实际上达到了真正的客观。
王明珂的羌族研究就是“族群形成的主观认同”论的一个典型个案。在其《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作者以羌族为例,通过长时段的观察与分析,明确了族群之间资源合作、分享与竞争的关系,进而发现了族群的动态区分与主观认同。羌族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在时空领域内固定的“非汉民族”,而是一个介乎汉与藏之间的少数族群概念,“羌族”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羌族”民众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动态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论”的深远意义还在于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界就热衷于“民族溯源”。其中一些重要学者的观点仍然具有较大影响,譬如傅斯年先生所主张的“夷夏东西说”;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等等。而王明珂却独辟蹊径,研究华夏边缘的族群历史及其社会记忆,他认为从族群边缘的新视角来看此问题,“‘中国民族的起源’不完全始于一个古老的‘过去’、一个‘核心’,而更重要的‘起源’发生在‘华夏边缘’人群间的一些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化。”这样一来,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就会从无尽的民族溯源探究中解放出来,而转向更加生动、具体的族群边缘互动研究。这不仅是民族史研究方式的革新,还会毫无疑问地深化华夏民族的历史研究:“历史是延续的,但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
王明珂还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文类-模式化叙事-历史心性-现实情境”的分析概念,为透视边疆族群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王明珂没有按照传统历史研究的方式,即根据文本史料与考古材料去进行考证工作,并在钩稽排比史料的前提下,努力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深入分析古人遗留下的文本书写,以及文本背后人们的真实意图与现实情境。在此逻辑之下,不是研究历史事件本事是否存在,而是研究产生这种社会记忆背后的情景变迁。不是研究历史上黄帝与炎帝是否为兄弟,或研究箕子奔朝鲜事件是否存在,“而是透过文本分析来探索,何时、何人有此之说,为何有此之说,也便是探究产生此社会历史记忆的‘情境’。这情境,也便是一种社会本相。”于是,上古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访谈等一系列被传统历史学家所遗弃的史料又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王明珂看来,从边疆人群口中得出的“弟兄祖先”故事再也不是简单的野史传说,而是隐藏着重要的族群历史信息。王氏并没有就一则“弟兄故事”讨论“弟兄故事”,而是将众多族群的族源记忆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在众多“弟兄故事”祖源记忆的背后有着相同的现实情境,即这类族群生活在需要合作、区分、对抗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的人类生态。而反观我们熟悉的华夏主体族群的族源记忆,其炎黄祖先记忆之下隐藏着对外扩张、征服,对内进行社会阶序化管理,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的人类生态。两种不同人类生态产生了两种不同祖源记忆模式,即王明珂所定义的“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与“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秦汉时期,华夏族群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庞大帝国。前所未有的现实情境呼唤着与之有对应关系的文类,司马迁的《史记》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文类因符合了汉代国家的现实情境与统治需要,所以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与褒奖。自汉代至清末,《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范本,因为这一时段内国家政权的主要形态没有发生改变,所以相应的书写文类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另外,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代表的边疆方志文类对应着中央集权与地方郡县的联系实态,此后各地官修方志大多会模仿《华阳国志》的撰修体例与格式,同样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境与合理化彼时的统治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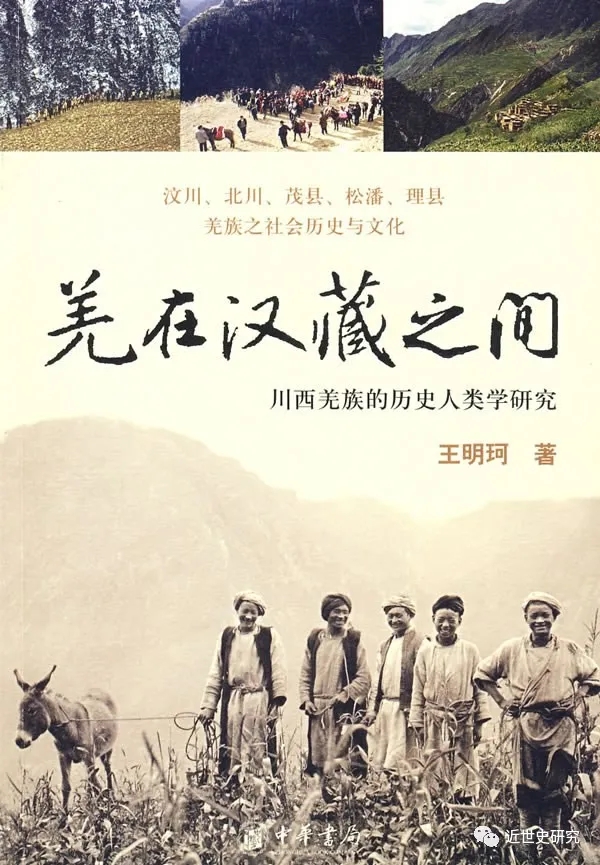
在对边疆族群历史进行考察时,王明珂还发现了一种模式化的叙事,譬如太伯奔吴、箕子王朝鲜、庄蹻王滇、徐福出海等等。这些“英雄徙边记”的模式化叙事中都有一位来自华夏族群内部的失意英雄,或王子或弃将,他们来到落后的边疆地区开始从事教化工作,当地人将他奉为祖先。通过研究分析,王明珂认为这些模式化叙事是华夏族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对四方蛮夷的想象,同样也是为了顺应符合当时华夏居于中央地位且文明更加发达的现实情境。
除了运用新视角、新方法,并提出边疆民族史的新见解外,王明珂还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上升为基于反思性知识之上的现实关怀。
在王明珂看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充满“表相”的社会当中,而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察觉何为“表相”?何为“本相”?实际上,表象产生于本相,本相也因表象而得到强化,表象遮掩本相,让人们置身其中却难以窥见社会本相的真貌。本相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特征,而相比之下,表相则具有短暂性与易变性的特征。表相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事物表相的深入分析,以此来认识事物的本相,并根据本相来指导认识表相。
表相与本相的内在关系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时段理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相一般不易显露,表相产生于本相之中,表相常具有迷惑性质,但表相终究是随着本相的改变而改变。而在“三时段理论”中,表相就如历史的短时段,本相就如历史的长时段。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与趋势一般隐藏在世相之下,不易察觉,短时段历史事件是长时段历史趋势的表现,短时段的历史事件纷繁复杂,但不管其如何变化都无法脱离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与趋势。人们需要了解事物的本相与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了解历史的发展大势与现实世界的本质。
王明珂在其羌族研究中就将运用了“本相”与“表相”的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上半叶,处于华夏边缘的北川地区族群有着强烈的汉族认同倾向,汉人认同的边缘地带中,各村落人群皆自称“汉人”,而讥讽上游地区村落人群为“蛮子”。但令人苦笑不得的是,自称“汉人”的人群也常被下游村落的人讥讽嘲骂为“蛮子”。荞麦作为羌人的传统食品,一直被视为羌人的重要标志。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时,“吃荞麦的人”成为了“蛮子”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情况下,荞麦被人为地赋予了歧视与污化的意义。但到了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扶持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而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会为他们带来直接的现实利益。于是,愈来愈多过去自称“汉人”但被他人称为“蛮子”的人群在此时开始主动要求被识别为羌族,而此时的荞麦又成为这些自称为羌族人强调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有力证据。在这项族群认同的研究中,荞麦为生动复杂的表相,而人们的现实情境与利益诉求成为了本相。
由此推之,我们可以发现本相是人类族群赖以维系的人类资源的分配、共享与竞争的社会现实情境,而表相则是为了实现、服务本相而存在的。如维系现实的一系列社会记忆、历史故事、宗族信仰、饮食习惯、服饰特色等等,都建立在特有的具体社会之中,都蕴藏着具有社会本相性质的内在结构、群体认同、地域边界等问题。人们通过预设的刻板印象与社会记忆,以及各种“物”的展演,从而强化他们心目中的社会本质的认识。而一旦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改变,这些表相在没有了本相的支撑之下,随即会被人们迅速抹除或遗忘。
长期以来,我们所接受的都是典范历史知识,并且生活在典范历史知识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之中,社会现实诱使我们对“历史”进行后见之明式的想象与建构。因此,当社会现实成为权力所支持的一种正统时,与之想应和的“历史”也会随之成为典范历史知识。即王明珂所定义的“典范历史知识”的概念:“典范历史知识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它成为典范乃因其最符合当前之社会现实,或最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期盼。”这里的典范历史知识与社会现实,其实就是本相与表相关系的实质。
我们需要对典范历史知识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打破典范历史知识对人们思想的桎梏束缚。当然,王明珂也强调其典范知识反思研究并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纯粹解构工作,而是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反思性研究:“我认为自己做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是一种‘解构’,即建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来认识我们当今的存在。”王氏研究的终级关怀在于:希望自己的系列边疆民族史研究可以让人们具有一种建立在反思性历史知识之上的族群认同:“创造具有反思性认同的中国人,也便是造‘国民’(或公民)。一个个具反思性之现代国民,应是理想中多元一体中国的主要构成单元;这是近代中国国族(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未竟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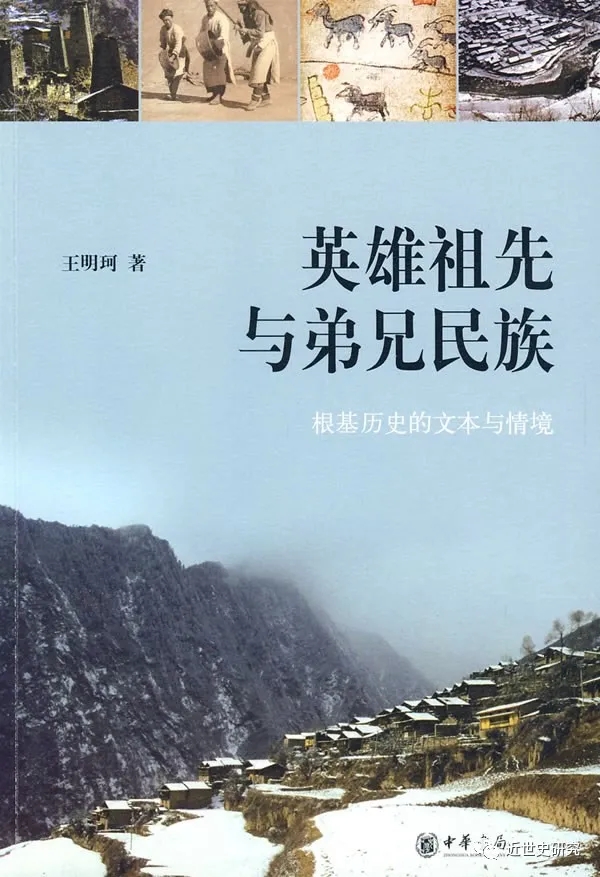
而要实现以上目标,王明珂的具体做法是从事典范知识之外的边缘研究,“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揭橥边缘缘何成为边缘?族群边缘的认同变迁是如何的?这些都需要研究者真正深入到边缘的空间、时间、人物与书写之中,探究边缘族群表相背后的真实意图与现实情境。
同时,我们也要摆脱研究者“与身俱来”的偏见,譬如王明珂在谈到《游牧者的抉择》一书的研究旨趣时谈到,人们关于游牧人群的刻板印象是面目狰狞的匈奴人,人们对游牧人群有很多误解。因为世界上主要居民是定居在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文明当中。因此游牧社会人群的研究意义在于挑战我们的偏见,促进反思性的知识。而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或许是人们所处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之中,“这是一种内化于我们心中的文化结构,让我们永远带着‘偏见’,选择性地观看、建构与回忆过去。”比如,处于“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中的研究者,可能会对“弟兄祖先历史故事”产生疑惑甚至误读。所以,我们要正视这种偏见,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尽量避免它,这样方有可能无限逼近族群历史的真相。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体性是建立在近代国族主义想象建构的基础上的,很多少数族群是被裹挟进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这是汉族中心主义霸权下核心主体对边缘族群的宰制。因此在西藏与台湾等地区的政治历史与社会现实上,中国的国家一体与民族团结受到西方外部势力的挑战。
王明珂明确反对这种对现实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民族解构式的研究范式,而为了强有力地回应西方主流学术界,其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努力尝试建立在反思辩证的基础上,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谈到其学术研究的路径及其旨趣时,他的一贯立场是:“学术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了解(针对实际问题,透过田野与文献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各种典范(如一学科之理论、方法与词汇概念)的反思上,如此学术才可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反思性研究可以超越典范历史知识的后见之明,协助人们借由对族群历史与社会记忆的反思,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并对当下社会有着深刻的省思:“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借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事物真实本相。”
唯有如此,我们对族群的认知才会上升一个台阶,也会对族群的黏合与分离有比较辨证的反思:“我们所宣称的‘统一’(或多元一体)中是否存在各种文化偏见、本位主义,导致‘一体’之内的人群阶序化,并造成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同样,王明珂也对另一种极端主义进行了反思:“我们所主张的‘分离’,是否为一种垄断资源的自利抉择,并可能导致内外族群体系之长期分裂与对抗?”只有基于以上两种深刻的反思与叩问,我们才有可能共商共建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与人类生态。

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可谓是体大思精、新见迭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其著作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疏漏,现就个人目力所及的一些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就教于王明珂先生及相关专家学者。
历史学是一门强调实证研究的学科,民族史研究亦然。而王明珂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却有着疏于考证的嫌疑,譬如他在举《三国志》中汉代良吏郑浑的例子时,认为渔猎经济模式相对于农业定居模式而言具有较强流动性,而婴儿不利于此流动生计,因此渔猎经济常有杀婴、弃婴的习俗。这是作者为了印证其文本分析背后的人类生态与现实情境而援引的例子,但深究此一论述似乎有悖常理,而且因为其没有充足的史料支撑,而令人心生疑窦。另外,王明珂还将具有模式化叙事的太伯奔吴、箕子王朝鲜、庄蹻王滇、无弋爰剑等“英雄徙边故事”视为华夏正统对四方蛮夷的想象,认为以上故事皆为人们构建出来的族群历史。在没有充足史料证伪的情况下,认定以上人物及事件为不复存在的历史,这一论断似乎有失公允。
虽然作者曾强调“这些历史叙事情节中有多少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事本身的结构与符号。”我们承认王明珂开创的这种探究文本表征背后的人类生态、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很具创新性且十分必要,但无论理论与方法如何创新,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史实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不能臆想、构建史实,他们必须通过扎实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来推论出相关史实,实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立论基础。王明珂的民族史研究方法原本是对传统史料归类分析方法的反思,其研究强调“文本、表征”背后人们的真实意图与现实情境,而非简单地进行史料的考证与钩稽。但如果在实际研究中无视史实考证,这就会有矫枉过正之嫌,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纵观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会发现,作者将华夏民族概念几乎完全等同于汉族概念。这或许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起见,而采用的一种模糊化的族群定义。但我们知道汉族或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这是民族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学术议题。如果没有将汉族或华夏民族大体的历史脉络与内涵实质梳理清楚,就开始分析族群边缘及其认同,这未免有些不太严谨。
另外,中国历史上有多次民族大融合,其中北方民族也不止一次从边缘族群成为政治正统,而原来处于中心的华夏族群相应地从中心流落到边缘。这些生动且复杂的族群互动及其认同变迁的历史,毫无疑问是华夏民族交融、认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王氏研究所涉及的时间大多从先秦、秦汉直接跨跃到了近代、当代。这对于人们完整地从边缘族群认同的视角了解华夏民族史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种缺憾。当然,学术研究从来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给人们留待缺憾的同时,不也是为后来者提供了后出转精、突破创新的可能嘛。
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以族群历史作为研究旨趣,以边缘看中心为研究视角,以社会记忆为研究路径,为人们呈现出一幅不同于传统民族史研究范式的边疆民族社会史画卷。其研究在充满了洞见的同时,强调反思性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然而,王明珂的研究也并非毫无缺憾之处,其论著中的相关史实论述存在疏于考证的嫌疑,较长时段内的边疆族群认同的历史也并未厘清。虽然王氏的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疏漏缺憾,但毕竟瑕不掩瑜。总之,王明珂为边疆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为中国民族史的长远且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