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成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20年第6期
原文刊载于《史林》2020年第1期
胡成(图源:网络)
摘要:自19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逐渐居于各国史学主流。该范式关注“话语”、“文本”、“符号”和“象征”,重点研究身体、性别、族裔和边缘人群,极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思想认识的多元化。不过,它带来了“碎片化”、“短时段”的问题,也引发了当下史学界的诸多反思。作为一个补偿选项,是史学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再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长时段”意味着对于“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予以更多义无反顾的关心和投入。
关键词:后现代;新文化史;历史时间;长时段;马克思主义
美国已故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家 (Thomas Samuel Kuhn,190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科学发展除了渐进式的日积月累之外,还有风起水涌的研究范式之转移(paradigm shift)。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替牛顿经典力学,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类似的旧范式失效,新范式由那些没有太多束缚的年轻科学家提出,在“科学革命”的意义上为探索未知世界打开了一扇新大门。同样发生在历史学领域里,是自19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强调文本、话语、意象和记忆,关注身体、性别、族裔和边缘,摒弃了此前国族史观、进步史观,以及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一度跃居于各国史学的主流。
正如《红楼梦》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每个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生命鼎盛周期。2008年,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也是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史学书写理论研究者的加布里埃·M·斯皮格尔(Gabrielle M. Spiegel, 1943-),在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引用了另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随着“后现代”的退潮,当下需要探寻留在海滩之上有哪些值得打捞和拯救的宝贝之说法;她进而强调,为确定哪些是值得拯救的,“我们还需要解释这场史学研究的大变革,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它受到了哪些激励,有什么样的配置和接受、扩展及衰落的节奏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学术实践。”
早在1920年代初,当史学方才成为中国大学一门专业性的独立系科时,有学者指出:“学术无国家界限,有同情者得共求真理,谓之学术共作。”如果我们大致梳理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发展,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到王国维、陈寅恪和傅斯年等人矢志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再至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1980年代末推动的社会史研究,以及1990年之后“新文化史”的风行,都表明了我们史学的发展早就“无国家界限”。相对于同时期其他的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以及后来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是中国最早进入全球性知识生产网络的学科,与欧美史学(1950年代后的苏俄史学)的变革,有着多年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带性、关联性和共通性。所以,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果“新文化史”在大洋彼岸退潮,新的研究范式正蓄势待发,那么在大洋此岸的我们将如何反思和应对?
作为一篇回顾性的学术反思,本文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原则,首先从研读以往的研究文献着手,然后“见诸于行事”地提出若干应急浅见。就此,本文的论述将在这两条研读轴线上展开:一是作为全球“新文化史”研究重镇的美国学界,另一则是国内这些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将美国学界作为反思的参照和借镜,并不关乎于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而是考虑到相对于其他学术社群,美国学界颇具学术反省和批判能力。这可以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是作为美国历史学界顶级旗舰性刊物的《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三十年来不仅刊发了十多篇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文字,且还组织了多次相关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专题讨论(AHR: Forum)。当年,傅斯年告诫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应该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这就像在北京的一位心脏专科医生,尽管面对不同族裔的病人,所在医疗机构的制度和文化也有所不同,然如果在纽约的医院同行,有了新发现或找到了新的有效治疗手段,肯定不会予以拒绝或故意视而不见的。这也就是说从学术理性出发,我们的各项研究应当融入,而不是孤立于这个世界,方能得到最充分的良性发展。
早在1980年代末,美国学界对“后现代”影响下的“新文化史”风行就已经忐忑不安,最早撰写反思性学术专著的,是时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1934-2012)。他的研究领域是法国现代史及美国历史编纂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职业》(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职业》(图源:网络)
具体说来,诺维克笔下“那高尚的梦想”,来自于1934年美国历史协会庆祝成立五十周年时,时任该会主席的西奥多·克拉克·史密斯(Theodore Clarke Smith, 1870-1960)教授,以“美国的历史书写:从1884-934”(Writing of 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 from 1884 to 1934)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在回顾美国历史学职业发展时,称自1884年以来美国历史学家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客观真理的理想”,已经作为职业认同中不能动摇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最核心和最持久的部分。概括说来,“那高尚的梦想”,更是史家们从“普适主义”(universalism)出发,将基于档案资料而得出的历史真理视为唯一和绝对的最高追求。
本书的副标题,是“‘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职业”。“客观性”何以与“美国历史职业”并列?这是由于在诺维克那一代历史学家看来,如果摈弃了追求客观真理的“那高尚的梦想”,历史学专业就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最初,被称为西方近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原因在于其时的欧美历史学隶属于哲学、政治学,没有独立招生和开课的资格。1833年,兰克在柏林大学开设史学研讨班,率先将历史学在德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系科。美国则是在1880年代,一批留学德国的历史学家回国之后,将史学与政治学科剥离。最著名的是赫伯特‧巴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 1850-1901),于1874年留学海德堡大学,1876年回到霍普金斯大学。他通过发扬光大兰克提倡的科学史学,培养了众多杰出研究人才,推动美国大学追随德国大学而创办历史学系。
当诺维克撰写此书之时,那些被视为“新文化史”的开山和经典之作,在欧美已是洛阳纸贵、喧腾人口。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3)、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1939-)的《屠猫记: 法国文化史钩沉》(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1985),以及更具理论冲击力的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1928—2018)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都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相似性,认为历史著作与小说同样是一种“虚构”(fiction)。这就让诺维克等人担心,称如果这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研究,那么必然导致追求客观真理的“高尚的梦想”,犹如“以色列没有国王”那样灰飞烟灭。
此前的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1950-)出版了《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 “新史学”》一书。虽说多斯不满年鉴学派的第三代,热衷于文化史和心态史,更多却是批评背弃了前辈们矢志于总体史的初心。与之不同,让诺维克等人忧心忡忡的,是历史学科在美国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因为不同于法国的研究型大学多为国立,美国顶级大学则多为私立,系科设置和教授聘任主要由董事会决策定夺。其时,诺维克眼看一些美国大学的微生物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物物理学系和理论生物学系,正被新成立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分子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系逐渐取代。[9]谁又能保证与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没有多少区隔的“新文化史”,不会被这些学科兼并而成为其从属附设的研究领域呢?这俩人的区别在于:多斯焦虑的是一个学派;诺维克焦虑的是历史学这个学科。
《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 “新史学”》(图源:网络)
《那高尚的梦想》出版后受到热议,并获得1989年度的最佳书籍奖,即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Albert J. Beveridge奖项。不过,其时“新文化史”方兴未艾,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发轫之初的欣欣向荣,并没有太多感受到随之而来的负面冲击和影响。《美国历史评论》于1991年6月号刊发了一组讨论此书的笔谈,也有认为诺维克所说的那些由第一代历史学家形塑的“客观性”,迎合了男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权力控制,并将之包裹上了一层“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史学之神圣外衣。再就这本书受到的广泛关注来看,《美国历史评论》在刊发这组讨论的引言中,特别讲述了1990年12月28日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关于讨论此书而组织的那场论坛(panel),不仅会议大厅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且会场过道和旁边走廊也都站满了人群。
接下来则还需要提及《美国历史评论》,于2008年4月号刊发了对时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杰奥夫·艾利(Geoff Eley,1949—)的学术自传、以及2012年6月号刊发反思史学“转向”的两个论坛。前者针对这部题为《一条曲线:从文化史到社会史》(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5)之书,集中在如何从“新文化史”转到“社会史”的讨论;后者则是针对其时美国历史学各种各样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讨论,总结这些“转向”对历史学发展的成败得失。为节约篇幅起见,我们在这里不详细展开。因为这两组讨论都只是对以往的回顾,而没有太多对未来的前瞻。套用其中一篇讨论文字的话说:关于如何超越“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史学家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理论和进行更多讨论,此时只能“巧妙地勾勒出未来必定产生争辩的地方”(masterfully sketched out the terrain on which the debates must take place)。
果然,关于史学未来发展范式应是什么的争辩,不久如期而至。2014年,由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担任当时该系主任的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撰写和出版了《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该书先刊布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官方网站,设置为读者自由获取的免费电子版,同时还开设了容纳广泛参与的公开论坛。这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出版纸质版学术著述之前,将电子版文本发布在互联网上。这俩位作者在参考刊行于网上的数百条读者评论之后,将修订过的纸质版交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当年推出。是书的全球影响,是随即有了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日文、韩文和俄文版,中文版则于2017年3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不同于以往对“新文化史”的反思,多是回顾性地描述而鲜有前瞻性地展望,《历史学宣言》旗帜鲜明提出了回归“长时段”的补偿方案。
该书仿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劈头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一个短时段的幽灵(the spectre of the short term),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句话则是:“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是书信心满满地声称,新的研究范式将立足于大数据,采用“长时段”的研究维度,探讨大框架、大过程、大问题和大趋势的大历史。对于“短时段”,是书则疾言厉色地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全世界各地史家沉溺于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inward turn)而成为一门孤芳自赏、与世隔绝的学问。
再颇为吸引全球历史学家目光的还有,是《美国历史评论》于2015年4月号以“交流”(Exchange)栏目为平台,刊发了由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 ,Ph.D., Berkeley, 1996)和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且还曾担任过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12-2016)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 1958)共同撰写的批评文章,以及古尔迪、阿米蒂奇俩人联名撰写的回应。鉴于《美国历史评论》通常只刊发经过匿名评审的文章,书评也只是由编辑部选定,从未刊登过在公共大众平台上的论战文字;编辑部“引言”称,这是一次“规则总有例外”(Exceptions prove rules),即该刊创刊一百二十年以来的首次破例。
至于为何“破例”,编辑部的“引言”坦承是考虑到该书通过网络和媒体,清晰、及时和豪情满怀地进行了传播,引发众多专业人士及非专业人士的关注。虽然赞扬、肯定和支持者不少,但批评意见也很多。撰写这篇批评文章的柯恩和曼德勒,建议《美国历史评论》以学术对话的方式予以刊发,毋庸走通常匿名审稿的程序,得到编辑部的首肯。的确,这篇批评文章语辞之尖锐,就像作者在回应中所写的,文中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溃”(“debacle”),“歪曲”(“travesty”)和“惊慌失措”(“panic”)。
这作为对本书最具负面意义的批评,加上还是英美史学界这俩位能见度颇高,且具领导地位的资深教授领衔的争辩,再由美国史学最高档次学术期刊“破例”刊出,由此凸显出该书的强劲冲击力,以及对相关讨论的巨大拉动及升温效应。我们将之称为本世纪以来史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事件,并不为过。同时,我们还可大胆预言,“长时段”的研究将会是未来全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
二、“社会史”、“新文化史”及 “长时段”的 缺失
有了上述美国史学相关讨论的借镜和参照,我们反身回顾国内这三十来年的发展,似更容易简明扼要地梳理出一条类似的演化线索。关于“短时段”的盛行和“长时段”的缺失,可能还要追溯到1980年代末的社会史之兴起。说到这项发展,源头还必须追溯到1987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刊发了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史学家们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以“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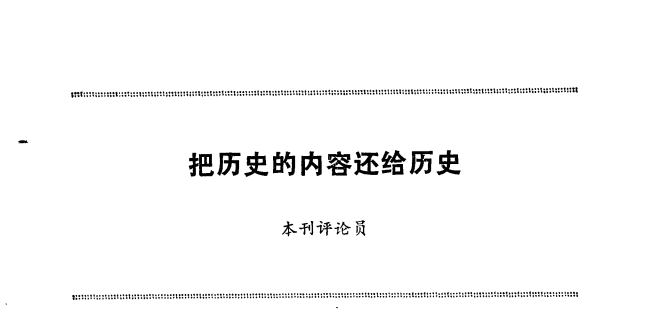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倡导,可谓是一种来自顶层的强力推动。从1986年至1992年期间,全国性的社会史的大型讨论会至少举办了四次。与会者讨论了包括宗族、商人、妇女、会党、匪盗、人口、习俗、婚姻、社区、货币、居住、城市管理等诸多以往主流史学忽略的议题。统计数字显示,在1987-1998年社会史研究的鼎盛年代里,《历史研究》刊发有关史学理论的“总论”栏目,总共36篇文章中,讨论社会史理论的9篇,占所刊发文章的百分之二十五。
不过,其时的社会史研究虽投入之学者众多,成就显著,但让学界最多担心的,是浮现出与“长时段”缺失相关的“碎片化”问题。
早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刊发的一篇题为《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的文章,认为其时社会史研究趋向琐碎屑细,表现在“一缺历史哲学层面上的宏观观照,二缺具体的概括性模式。”再至2012年第4期的《近代史研究》,刊发了一组讨论“碎片化”问题的文章,至少有两篇文章将此源头追溯到随社会史兴起而出现的微观研究。其中一篇的批评是:“把自己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只会导致历史学的繁琐化,甚至将历史书写退化成为传播逸闻轶事和发思古之幽情的手段。”
到了199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取而代之的是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
最早谈及这一研究转向的,大概是《读书》杂志1993年刊发的一篇题为《走向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文章。该文介绍了台湾的最新研究,声称无独有偶,北京一位学者在讨论这部方术史著述时,“亦引用福柯的话,提出要‘写另一种历史’”。翌年,《历史研究》刊发题为《福柯史学刍议》的专题论文,全面介绍了这位“后现代”最重要思想家的学术成就。是文指出福柯的毕生工作,是通过历史研究来探讨哲学间题,故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作者称赞道:“他的全部主要著作不仅都可以被视为史学著作, 而且部部都是振聋发馈的史学大手笔, 都能在史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并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一项重要的发展,是《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刊发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一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此前人们虽了拜读过谈及“后现代”或“新文化史”的,但那是就欧美学者谈其对欧美历史的研究,是文则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提供了能够为国人直接效仿的研究典范,产生的思想冲击自不可低估。本书中文版的书名是《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由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s L Hevia)所著,英文版于1995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在美国史学界却引发了一些批评和不满之声。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图源:网络)
1997年,对此书的中文批评就已经问世,同时还有为之辩护的文章。总共这五篇文章分别刊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当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的12月号,以及翌年的2月号、4月号和10月号。最严厉的批评者,是在大洋两岸都很有影响力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1942—)教授。一年后的《历史研究》刊发上述那篇专题书评,则是对该书的正面肯定和称许。这就不太符合所有高水平学术期刊,刊发已有激烈争论的学术文章,总是既刊登正面肯定,又刊登负面批评的惯例。再加上此时像《二十一世纪》这样的海外期刊,规定只能存放在对研究生和教师开放的“港台阅览室”,并不是很容易就被读者读到和知晓。由此或可推定《历史研究》刊发的这篇文章,多多少少推动了“后现代”在国内学术界的登堂入室,形成气候。
再就这些年的发展来看,不同于此前兴起的“社会史”,“长时段”的缺失是由于研究领域有点漫无边际的扩展,受“后现代”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则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元史学”(Metahistory)意义上,颠覆了以往主流历史研究的线性和进步史观。
这具体表现在,不仅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事模式,受到挑战和被摒弃;且以往被霸权文化压制的弱势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肯定。2007年,中文世界中一篇对“后现代”颇多微词的文章,承认这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恢复本土和传统的文化自信,因为“文化多元与‘地方性’成为新文化史的大势所趋。”重要的是,“新文化史”还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现实诉求。此前另一篇以《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为题的文章,认为按照这种“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y)的理念,“将来中国经过现代化的努力,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事实上也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所走过的道路。”
关键更在于,受“后现代”影响的“新文化史”之发展,带来了比“社会史”研究更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这些年来较重要的讨论,如上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于2012年第4期、第5期刊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的总共13篇文章;虽说作者们的看法和认知有所不同,但都认为“碎片”是当下我们史学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再至2019年的年初,《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刊发以《史学观澜2018》为题的总结文章,称本年度的中国史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畸轻畸重局面依然存在。这也就是说“碎片化”情况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注意波动、周期和数字的经济史,较少“短时段”而多“中时段”、“长时段”的研究,那么统计数字不太乐观。《中国史研究》2018年刊发了65篇文章,其中“经济史领域仅有6篇,不仅远低于政治史领域,也低于社会史和文化史”。
这里需要稍作讨论的,是我们能否有点耐心,等待当下这种受“后现代”影响的“新文化史”,通过日积月累,在无数“碎片”的研究之上,忽然哪天催生出若干“长时段”意义上的鸿篇巨制?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
如上引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指出,不同范式代表不同的世界观,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兼容性。就像在哥白尼之前,人们将月球看作一颗行星;而在哥白尼之后,人们则将之视为卫星了。这也好比只有认识到牛顿理论的欠缺,才能够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新文化史”与“长时段”,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这二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我们或可从以下“虚拟性”、“建构性”和“空间化”的三个方面做点阐释:
首先,是“新文化史”偏重于“虚拟性”的研究。
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社会史的议题,研究文化现象本来就较多倚重于研究主体的推测、猜度和诠释。“新文化史” 反对简单地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对应文化解释,希望通过分析语言、符号、意象和仪式等,进而探讨历史演化进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些虚拟的历史面相,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没有办法触摸和数据统计的,需要研究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去体验和感悟。所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之境界”,意味着是一种此时、此地和此人的“在场”或“现场”的“短时段”对话。当进入到与历史现象同在的特定“语境”, 研究就不太可能是那种高屋建瓴式的“长时段”之历史乌瞰。
其次,是“新文化史”认为文化象征乃“建构性”的历史产物。
不同于此前政治史、经济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结构为客观历史生成,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文化史”受“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影响,认为历史上的符号、仪式、意象和理念,是通过语言、记忆和想象而塑造出来的。就像萨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或者说安德森笔下“想像的共同体”的国族,虽不一定为结构性的历史真实,却肯定是各种权力/权利的角逐和博弈之现实存在。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生产和不断地建构,均着眼于当下或眼前的价值考量,以及所属群体成员之间每日面对面的“短时段”互动。这种基于日常权力话语的实践,通常是易变、零碎和不确定的,相关研究自然也就不太会关注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历史“长时段”。
再次,是“新文化史”还注重探讨“空间化”的历史。
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可被认为是历史上人们的生活环境,弥漫着各种相互对抗的社会关系。就像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将知识、权力与“身体”的“空间”建构联系在一起,通过探究“全景式监控”的监狱或海军医院,以及“泰勒式工厂”的生产车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一个个封闭的、区隔的、经过精密计算和严格管理的惩罚和规训空间。由于权力关系被视为“空间”意义上的建构、运作与实践,“新文化史”研究还主张将目光转向那些被歧视、被压抑、被侮辱和被排斥之人,如处在历史边边角角的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这就更趋向物质性,更注重探讨具体人与事的个性及歧异性,更多强调在历史共时性上的相互关联,“新文化史”史家自然会舍弃相对偏爱研究抽象性和统一性的历史“长时段”。
如果将“长时段”作为一个可能选项,我们还需要在“范式”意义上再做些回顾性地探讨。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似乎还不是当下我们国内史学的重点关注之所在。毕竟,这些年来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史学研究的讨论,见诸于文字较多的,是关于“大问题”/“小问题”、 “碎片化”/“总体史”、“微观研究”/“宏大叙事”,而很少直接论及“短时段”/“长时段”的议题。或许,这是由于相关“历史时间”的讨论,并非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致使史家对此不太敏感,也没有更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开掘和汲取。
就像《春秋》的三统之说,按照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解释,“时间”是“黑”、“白”、“赤”的循环往复。孟子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司马迁《史记·汉高祖本记》中则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甚至直到晚清最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也认为“时间”就是“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再用《三国演义》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则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历史循环论”,将 “时间”视为外在“天意”或“天命”,圣人通常“存而不论”,常人不必就此想入非非。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说。由于没有仪式化、典籍化,乃至神圣化,华夏虽也有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却只是一个世代流传于民间的动人神话。
与之不同,基督教以“创世”之说为基线,构筑了关于耶稣的降生、传教、牺牲和复活的救赎过程。“时间”也就成为一个总在被智者沉思冥想的话题。古罗马思想家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说过:“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过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也可能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用十五年的心血写成了《上帝之城》,向世人勾勒出一个从“世俗之城”趋向“上帝之城”的“时间”之旅。
漫长中世纪的欧洲农民,与中国农民的“时间”观念,倒并无二致。二者都是以日常生活的“劳作”为基准,诸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放牧、耕种、用餐、以及猎人在夜间设置陷阱、渔夫就潮汐涨落时间规划捕鱼。根据著名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的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时间”,始于十四世纪初在英国发端的“工业资本主义”。其时在棉纺织厂的工人,受到了一种新型的、抽象的、线性的、重复的工厂劳动制度的严格约束。汤普森指出:这种“朝六晚六”的十二小时的劳动时间,不仅由获取政治权力的资本家,通过修改国家法令等外在压力所强制性形塑;更重要还藉由新教不能浪费“时间”的伦理、以及增加工资等因素而将之“内在化”(the internalization of new discipline),致使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是心甘情愿,趋之若鹜。
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近代转换,是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率先将“时间”视为人的感性直观的内在认知形式,与人们的自由意志相联系,从而使之具有了主体性。接下来则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 W. F. Hegel,1770—1831)、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等人的深入研究。我们或可以认为,对“时间”的体悟,造就了学者的思想深度。然最先将“时间”引入到历史学研究之中,是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986-1944)。他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强调:“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
对布洛克就“历史时间”问题的思考,同是年鉴学派创始人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 在该书出版时,撰写的《序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布洛克的思想与柏格森关于延绵性、思想和生命流动性的哲学是一致的”。紧随其后,是他的得意门生,也是第二代年鉴学派领军人物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将之发扬光大。布罗代尔先在《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博士论文,后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提出及系统论述了史学研究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区分,及其各自的研究意义。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从来不能摆脱“历史时间”的问题,时间粘着他的思想,一如泥土粘着园丁的铁铲。他说:“从短时段转向长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不会被这种前景所吸引!”
布罗代尔之所以比上一代年鉴学派的布洛克、费弗尔,更看重“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在于他看到了随着其时新兴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强势崛起,史学受到了根本置疑,被贬为素材,一门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排斥所有模式化的守旧学科。布罗代尔的回应之道,是相对于这些作为史学四邻的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但凡研究涉及到时段和分期,就必须要由历史学家来当领导。布罗代尔满怀信心地写道:“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接受与否,在近年来历史学的试验和努力中,产生了日益明确的关于时间的多元性质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的思想。这个最新的思想甚至会比历史本身——各种各样的历史——更能引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四邻的关注和兴趣。”
毋庸赘言,不论是布洛克、费弗尔,抑或是布罗代尔,以及随后的年鉴学派,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布罗代尔谈到自己的“长时段”时,充满敬意地声称:“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的确,是马克思最先将哲学讨论中的“时间”,引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之中。被认为是他的两个伟大理论发现: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是唯物史观,都与“时间”或“历史时间”密切关联。前者指马克思将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和“剩余”两个部分,资本剥削的秘密,就在于狡诈地占有了“剩余劳动时间”里的“剩余价值”;后者指马克思通过探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勾勒出一个作为所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共产主义之历史演化愿景。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布罗代尔虽对马克思满怀敬意,在思想上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在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力超过他的,是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当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欧洲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失望而纷纷改变立场,萨特是少有几位为苏联当局辩护的左派学人,并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逾越的哲学”。布罗代尔对萨特有颇多不满,酸味十足地称其观点虽完全错误,居然还能以辉煌的方式投入到法国的生活之中。在他看来,萨特虽有权利幻想一个消除了不平等和人统治人现象的社会,但在当今世界,任何社会都没有放弃传统和特权惯例。与萨特相反,布罗代尔试图证明,人类自由是一扇极为狭窄并不断缩小的门。他说:“用历史‘长时段’尺度来衡量,任何人类意志论都毫无意义”。
概括地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时段”,认为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是可以被改造的,因之未来也可能更美好。已故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 1948-2010)引用了一位马克思传纪作家的话说:“马克思的信念的道德严肃性,使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同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引美国历史学家艾利撰写的那本《一条曲线:从文化史到社会的历史》学术回忆录,谈及他于1967年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读本科,意识到要成为历史学家,就必须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呼吁从“新文化史”转向“社会史”,意味着在整体上重新研究各种社会,将其内聚力和不安定的基础理论化,并分析各种变动模式。艾利相信:“对未来的历史研究,一定需要重新复兴那种反叛精神(an insurgent spirit again)。”
再至上引那俩位美国学者合著的《历史学宣言》,似更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时段”的巨大生命力。作者毫不隐讳效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声称鼓吹史学研究的“长时段”,就在于积极参与和讨论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三项深刻危机——气候变迁、国际公共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如果将这三个问题排列比较,马克思投入心血最多,终生殚思尽虑之所在的,无疑是关系到那些“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的社会不平等。曾任匹兹堡大学讲座教授的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 1941-),研究以非洲史为重点的世界史和全球史,荣休后于2016年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当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他的主旨演讲以“不平等:史学和学科方法”(Inequality: Historical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es)为题。在他看来,面对当下世界各国急遽恶化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史家应立足于“长时段”和“大数据”,尽可能多地投入到(large-scale involvement)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去。
由此返回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长时段”,对那些“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予以了最多的呕心沥血和最多的义无反顾。作为比较,早在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的二十世纪初,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之下,一些新派学者引入了西方的线性“时间”理念,开始有了主体内在感受意义上的历史分期和时段的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他们中有人将之分为“积弱”、“变政”以及“共和”三个阶段。然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的胡绳,于1954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线索,应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三次革命高潮”。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提法较前人更多关注了国族的独立和解放,目的还在于尽可能地消除与“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密切相关的诸多不平等。
逮至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长时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引领角色。从那个时代过来之人,都不会忘记《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的主持之下,刊发了一系列关于“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以及“谁是历史创造者”的文章。这些文字气势恢宏,振聋发聩,有力推动了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再至1988年,时任《历史研究》编辑,后来担任主编的张亦工(1942-2003),撰文谈及中国近代史研究规范与时俱进时,称:“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不断提高的追求,对于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的渴望,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探索,使人们要求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鉴于此,我们似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时段”,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时段”之间的区别,就如坐落在英国北伦敦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的马克思墓,矗立墓碑上铭刻着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让我们再次回到上面提及的《历史学宣言》,在思想史意义上进一步定位史学“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关系。英文中的“宣言”(Manifesto)一词本来自拉丁语,最初出现在1640年代的意大利,原有公开声明、表达意愿,呼吁采取行动等意涵。就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目的在于唤醒随着工业革命而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宣言》的俩位作者也期望由此唤醒史家的“时间”意识,积极投入到“长时段”的史学研究之中。他们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期率先将“宣言”一词,赋予了不可逆的权威性和神召般的特质,“使之既是修辞和实践,又是诊断和改革(have been both rhetorical and practical, diagnostic as well as reformative)。”
然而,学术批评或学术讨论,理应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毕竟,当下“宣言”频繁见诸于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带有太多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之意向。上面谈及《美国历史评论》刊发的那篇对《历史学宣言》的批评文章,反唇相讥《历史学宣言》与“短时段”的势不两立,称: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这俩位批评者不客气地指出,是书“或许有些目光偏狹和轻微的威权主义(one-eyed and just a little authoritarian)”。在这俩位批评者看来,学术研究应鼓励各种范式的竞争,大力开展“长时段”的研究,并非一定要贬斥“短时段”和“中时段”的研究范式。
的确,“历史时间”并非只是像钟表那样,有其固定间隔而严格一致。上引最早提出“长时段”概念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布洛克,就“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多样性,提出了有别于“长时段”的历史“时刻(moment)”的概念。
在他看来,历史时间具有的不同层级和尺度,历史学家可依据现象本身来寻求符合他们的时间研究路径。他的精辟论述是:历史学者不免摆荡于下述两者之间,“有时是由穿越时光之流的相似现象构成的洪流(the great waves),有时则是这些洪流将各种意识会聚于一点的独特时刻(the specific moments)。”
毋庸勉为其难的,是史家选择“短时段”、“中时段”,抑或“长时段”,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生存状态。上述《美国历史评论》刊发的那篇对《历史学宣言》的批评文章,指出该书误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列为“长时段”的代表作。实际上,此书是1940年法国战败之后,作为战俘的布罗代尔在德军战俘营里被关押了五年,凭着记忆和不完全的资料构思而写成。菲力普二世(1527—1598)在世七十年,时间跨度则为布罗代尔自己定义属于个人时间的“短时段”。同样,陈寅恪也曾批评过“国人治学,罕具通识”,憧憬晚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年老体衰,瞽目膑足,再以大环境不那么舒心,只能撰写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短时段”之著述。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尽管我们不排斥“短时段”,但从史学的职业追求来看,却不能由此不分高下,在价值层面上也将之与“长时段”等同视之。康德曾率先指出,由于空间与外部事物的表象相连,时间则是人类的内部意识本身,故在构成知识方面,时间比空间具有更加深刻的本源作用。同样的道理,历史学职业的独特性和普适性,决定着史家应尽可能从“历史时间”的万古不息、源远流长,探讨何谓推动人类社会演化的原动力。严耕望先生就此指出:“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这也意味着“登高望远”,体现了史家的视野、胸襟、气度和格局。有时虽不得已而做一些“短时段”的研究;然“长时段”则犹如史家心中的灯塔,始终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至善境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作者:胡成 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