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檢視「日常生活」概念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有效性,透過分析與比較晚近的著作來說明,在多大的程度上「日常生活」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成果,提出新觀點來詮釋中國近代史。本文將先扼要地介紹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脈絡,並界定「日常生活」的範圍及核心概念,以作為學術對話的前提。然後把焦點轉回近代中國,探討晚近中國史學界如何利用這個概念進行研究:他們提問的方式、內容及限制。文章最後則探討「日常生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及方法論上所可能的貢獻。
關鍵詞:日常生活 小市民 上海 北京 成都

最近三十年西方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史學流派——「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史學,研究者開始把過去所認為「雞毛蒜皮」的瑣事納人學術研究的範瞭内,這些成果豐富了吾人對過去的認識我們對古人的了解可以細緻到他們所吃的食物、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所把玩的物品等。這些細節讓後世讀者更容易想像古人的生活空間,進而了解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當然,日常生活研究的野心往往不止於此,學者更希望透過新領域的建構來挑戰過去的研究典範(paradigm), 突破原有方法論的限制。對他們而言,從事這些研究最大的報酬是在新的視點下看見不同的歷史圖像,嘗試對主流敘述有所補充或修正。
這個研究取徑也影響到中國史的發展。早在1959年法國史學家Jacques Gernet已出版南宋的日常生活史,到了198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陸續出版關於小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著作, 1990年以來則較密集地出現城市日常生活的專書。這些論著多半由博士論文修改出版而成,顯示年輕學者對日常生活史的濃厚興趣;並且這股熱潮還正持續之中。
問題是,「日常生活」是否真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框架而形成新的典範?它是否真的能夠說明、甚至解決問題而成為有用的分析工具?如果這些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日常生活」研究取徑的優勢及限制又何在?這些是吾人在閱讀、甚至研究中國「日常生活史」時所必須正視的問題。
基於這些關注點,這篇文章旨在檢視「日常生活」概念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有效性,透過分析與比較晚近的著作來說明,在多大的程度上「日常生活」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成果,提出新觀點來詮釋中國近代史。為了更清楚地討論問題,在回顧研究成果之前,本文將先扼要地介紹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脈絡,並界定「日常生活」的範圍及核心概念,以作為學術對話的前提。然後把焦點轉回近代中國,探討晚近中國史學界如何利用這個概念進行研究:他們提問的方式、内容及限制。文章最後則探討「日常生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及方法論上所可能的貢獻。由於本文旨在檢討日常生活研究方法的應用,因此不打算作整個領域的回顧;文章中所討論的著作以中英文的學術專著為主,近年來所出版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照片畫册與通俗性書籍,則不在討論之列。
一、史学家为什么要讨论「日常生活」
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知識發生興趣並不是近代的現象,以中國為例,晚明出版大量的「日用類書」,其內容除了修身治家的原則外, 還包括與人交際的應對禮節、鑑賞書畫的知識、商業交易的祕訣等。西方亦有類似的現象,如十八世紀的英國與德國即有各種商業手冊的出版,描述商人心態及商業文化。近代則有各類的城市指南,不但提供外來遊客導覽資訊,也是商業廣告的一種形式。更有意思的是《中國的一日》及《上海一日》的編纂及出版:茅盾受到俄國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i, 1868-1936)的啟發,向社會大眾徵文,報導1936年5月21日所發生的事件。由於作者來自不同省份城市及各個社會階層,記錄的内容包羅萬象,包括醫院裡的見聞、同事對長官的卑躬屈膝、小理髮匠因繳不起攤捐而遭鞭刑等,性質上是1936年5月21日的「集體日記」,生動地披露各行各業生活的真實面貌。《上海一日》的出版過程類似,但投稿人可以在1937年8月13日至1938年8月13日之間自行選擇一日記事。1937年8月13日發生灑戰,日本人轟炸上海,三個月後華界淪陷。因此從編輯目的上來說,《中國的一日》意在揭發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以作為革命基礎;《上海一日》旨在暴露帝國主義侵略的惡行,並挑起愛國主義的情緒。儘管《中國的一日》及《上海一日》的出版帶有強烈的政治意涵,編者似乎肯定民眾對日常生活知識的濃厚興趣,以致他們選擇以出版「集體日記」作為達成政治目的途徑。
不過「日常生活」作為史學研究的領域、用以概念化歷史知識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1970年代起,西方史學界出現一個很大的轉折,即Lawrence Stone所說的「敘述的復興」(revival of narrative)在此之前歐美的史學研究深受社會科學的影響,認為其目的在尋求歷史演變的規律,不論是馬克思史學或是年鑑學派(The Annales)均試圖找出社會發展的路線或結構。然而愈來愈多的史學家們不滿足於「社會結構」的呈現,特別對造就「大歷史」 (macro-history)的「小人物」(small people)失於歷史敘述感到挫折。他們認為歷史必須回到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看似平凡無奇的生活事件中才能找到歷史的真正意義並且主張過去所認為的「邊緣人物」才應該是歷史書寫的中心。
造成這個學術轉折,主要可歸納為四方面的原因。首先,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197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對長久以來的「現代化」典範產生質疑:工業革命使人們樂觀地相信工業資本主義及技術革新能持續帶來進步與繁榮,但層出不窮的社會抗爭與對立卻顯示工業化使社會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根植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馬克思學派及年鑑學派也因此遭到空前的挑戰。基於對弱者的同情,史學家認為有必要為「受害者」撰寫歷史。
其次,文化人類學也對日常生活史學的形成帶來影響。文化人類學通常以非西方(主要是第三世界社會為研究對象,觀察其傳統文化及習俗如何規範人們的生活方式。人類學家對「邊緣地區」的關注引起一些歷史學家的高度興趣, Natalie Davis便曾指出,人類學家對於社會互動的細密觀察及對象徵性行為的詮釋,對歷史研究起了刺激的作用,促使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問題,也對所謂的「歷史重要性」有了新的定義——能對社會産生重大影響的,不只是政治精英及其相關機制;民間宗教的領袖所傳講的信息及所施行的禮儀,我們看來會認為是「非理性行為」,它們卻是一般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兩種社會成員及其行動,都突顯了該社會的特殊性格。這種新的學術興趣帶動了史學研究的轉向,不但在研究對象上從帝王將相轉向市井小民,進而引發「新社會史」的熱潮,研究主題也從市場機制、官僚體系等結構性問題轉向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個人性問題。其中以E. P. Thompson 、Natalie Davis 、 Lawrence Stone的著作最受矚目。儘管他們的著作並不以「日常生活」為主題,但日常生活史學辯論的健將往往以他們為學術典範。從這個角度來看,日常生活史學可說是「新社會史」的分支流派。
第三,文化理論的發展刺激歷史學家以日常生活的視角來思考並概念化問題。從Georg Simmel 、 Walter Benjamin 、Henri Lefebvre到Michel de Certeau ,這些理論家的共同關懷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討現代性的問題。如Benjamin的「垃圾美學」,把日常生活中一些過時的、被遺棄的素材並置(juxtaposition)在一起,使之看起來像是一種「偶然的機遇」,而不是「方法論的步驟」。因此,從日常生活所呈現出來的現代性,是歷經工業化的衝擊後,「各種殘骸碎片(debris)的持續累積」。相對於Benjamin將日常生活視為社會被快速消費、「零碎化」的表現, Lefebvre則認為日常生活所表現的是社會整體性,現代資本主義的擴張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裡,因此「革命不能只是改變政治人物或制度,它必須改變日常生活,一個已經被資本主義確切地加以殖民化的日常生活。」不論這些理論家如何扣連日常生活與現代性,對現代化、工業化及資本主義化的批判,嚴然成為日常生活文化理論的主軸。從這一點看,日常生活很自然地成為馬克思史學家的「新武器」,透過對生活細節的描述,深刻地暴露資本主義對現代人的宰制。

骆驼祥子
第四,從史學本身的發展來看,日常生活史學最大的野心是企圖回答長久以來社會史研究所懸而未決的根本問題,即如何理解個體經驗與總體結構之間的關係。歷史學家的主要責任並不在突顯個人英雄色彩,而是表達某個時代的集體心靈;然而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家的敘述卻又是從一個個具體事例累積而成。以馬克思學派及年鑑學派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式史學雖然試圖尋找超過個案之上的社會結構,但卻也在同時失去個別的經驗,以致無法理解並表現歷史過程的二元性質。因此史學家希望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尋找歷史變遷的動力。不過日常生活史學出現以來,也招致不少批評,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界定日常生活範圍。論者以為日常生活的概念不夠精確、界線也不清楚,以致它該包含哪些內容,言人人殊。不過日常生活史學家仍有一些共同的關懷,其一是把焦點放在一般人(ordinary people),也就是那些並未留名青史的小人物身上——日常生活史學正是建立在這種「默默無名」(nameless)的特質之上。不過史學家的野心並非只想擴充原有的研究領域,而是希望以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重新看待社會科學式史學所不斷強調的「超越個人的形塑力量」(shaping power of supraindividual forces) ,即「社會結構與過程」(societ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想法是反轉原有的思考方向。德國日常生活史學家Alf Lüdtke便直言,這些所調的社會結構其實也都是歷史的產物,不能只將它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這樣的想法迫使我們重新形構問題,甚至重新思考過去所習以為常的研究範疇。例如過去研究工人運動時通常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當作背景或是勞資糾紛的「結構性」因素;但從日常生活史學的角度,問題就變成工人如何「經驗」或「感受」資本主義經濟,甚至資本主義、階級等概念也不再像過去所認為具有相對穩定的界線。換言之,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被「歷史化」(historicized)的分析對象,而不是人類行為的決定因素。日常生活史學的終極關懷並非填補歷史知識的空白處(儘管建立「全面性歷史」total history也是它的目標之一),而是挑戰過去對歷史的詮釋及歷史知識的分類方式,因此它的企圖是方法論及知識論上的突破,並樹立新的研究典範。
除了強調「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以及歷史化社會結構之外,日常生活史學家還把重點放在例行的、重複的生活方式上,不過他們並不像年鑑學派一樣,試圖在重複的、不變的模式中尋找結構。一方面他們承認生活的重複性,並認為正是這種生活的重複性使人們的「思想與行動變得很實際,因為慣例的作用是使人從懷疑及不確定感中得到解脫。」另一方面他們認為任何的變化乃源於真實生活中人們産生不同的利益、需求與渴望;當人們日復一日地重複生活韻律時,歷史動力亦潛藏其中。更簡單地說,日常生活史學所要呈現的主題是人如何同時成為歷史主體與客體的故事。
日常生活史學是否真能像研究者所承諾的,開創新的歷史思考方向及研究取徑,仍有待觀察與評估;不過其影響力的確擴及非西方學界。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對日常生活史學亦開始產生興趣,尤其幾本關於近代城市的著作都把焦點放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上,以下筆者將按照這些新著的共同主題加以探討,以期觀察究竟日常生活史學對中國史研究產生怎樣的影響。
二、近代中国的日常生活
(一)誰的日常生活
198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史研究出現很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趨勢之一是「邊緣人物中心化」,而這正是日常生活史學的重要使命。最近幾部關於民國時期日常生活的著作均把焦點放在一般大眾、尤其是社會底層的身上,如勞工(特別是纱廠女工) 、妓女、黃包車夫、以及飽受歧視的上海少數族群蘇北人等。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貧窮、且被深刻地捲入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輕易地以他們為階級鬥爭的分析對象。不過,許多作者均有意識地避開階級鬥爭的論述,而將重點放在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工作與居住環境、人際關係、例行活動等。從這些城市貧民的生活經驗發現,「階級鬥爭」並不是他們生活的全部、甚至是關鍵部分,有時鄰里間的磨擦反而是他們更重要的生活片段。這個思考可能會改變我們勾勒歷史圖像的方式:描述黄包車夫眼中的北京及上海時,街道里弄文化可能比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事件更重要。換言之,日常生活的面向幫助我們看到更複雜、也更貼近社會現實的城市生活面貌。
除了城市貧民之外,另一種「邊緣人物」是所調的「小市民階級」。受到中共革命史學的影響,中國社會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到社會階層的兩端,即剝削大眾的官僚和資本家,以及被剝削的農民及勞工,介於這兩端之間的民眾則長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因此他們可說是歷史研究與書寫的「邊緣人物」。1990年代以後學者開始對「小市民」的生活樣態産生興趣,認為這個領域可能為城市史研究開出新局。不過「小市民」是個定義模糊的概念:社會群體研究多半以職業、性別或籍貫作為分類標準,「小市民」則是對非上層精英分子的城市居民的一種籠統稱呼。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Perry Links認為包括小商人、各行業的店職員、高中學生、家庭主婦等的「小市民」是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主要讀者,這個定義雖預設了「小市民」具備一定的教育水準及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得起閱讀小說的文化(或休關活動,但事實上「小市民階級」的内聚力量極低,很難將它視為一具有統合性的社會群體。葉文心研究鄉輕奮及《生活週刊》時,採取了Links對小市民的定義,但除了刊物所要傳達給「小市民」的信息之外,我們其實對「小市民階級」的影像仍然感到模糊。為了更進一步探討「小市民階級」,葉文心乃以1930年代中國銀行行員為研究對象,特別著重探討公司裡各種機制(包括物質的時鐘及非物質的業餘活動對行員日常生活的規範。這樣的研究固然使讀者對「小市民」産生具體的印象,但由於一開始便以特定行業中的一家公司為研究對象,便失去了「小市民階級」的概括性。因此,從中國銀行的例子當中,日常生活史並不能使吾人更清晰地概念化「小市民」的群體性質。盧漢超研究上海「小市民」的方式則採取不同的策略,從民居的角度來界定這個群體:他們住在所謂的「石庫門」的里弄房子裡,狹窄卻又稍有隱密性的居住空間,表現出他們與城市貧民在經濟與文化地位的區隔。當然,這個定義同樣以物質條件為基調,但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以居住環境所界定的「小市民」更富有「社區」的意味,並具備社會群體的意義。從這一點來看,日常生活研究不但有助於吾人了解社會組成份子的多元與複雜性,也有助於吾人以新的界線來劃分社會群體——這可能比社會科學式的人口學因素更貼近人們的生活經驗,進而更接近歷史真實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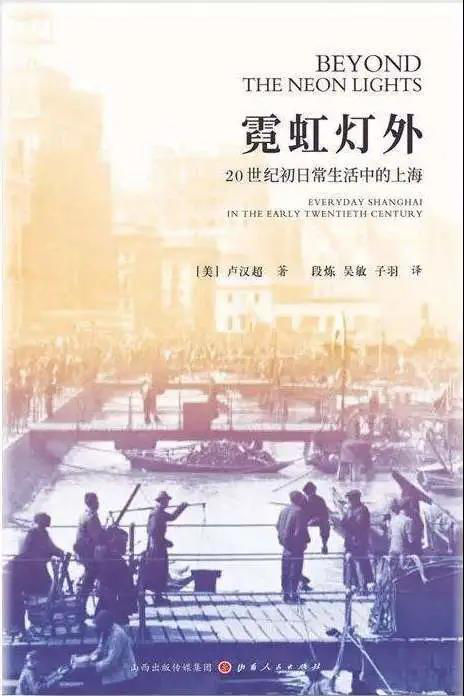
不過並非所有的日常生活研究都真的能夠幫助釐清「小市民」的獨特性及其群體意義,王笛關於近代成都街道文化的新著便是一例。他所定義的「城市普通人」(urban commoners) ,指的是「社會的下層階級,可以是無名小卒、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每一個人、平凡的人,甚至可以是『危險階級」。這些人在街上工作並與人交誼,創造E.P.Thompson所說的『庶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 。這些人的名字可能被歷史遺忘,但他們每天占領著公共空間,創造街道文化。」這個定義其實與盧漢超所謂的「小市民」相去不遠,只不過王笛更強調形塑這個群體的「空間公共性」。問題是,「空間公共性」是否可以有效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界定「城市普通人」?當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占用相同的街道空間,我們就很難以「空間公共性」來有效地說明「城市普通人」這個社會群體的特色與內涵,結果作者還是必須訴諸過去馬克思階級論來定義「城市普通人」,而對「城市普通人」街道文化的精緻描述只能證實一個普通常識,即「城市普通人在公共空間也占有一席之地」。這樣的日常生活研究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超越過去的學術典範。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以華人的生活經驗為主,少數關於在華外籍人士的研究,也以傳教士的宗教傳播及外商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為主。1950到70年代間,有一群曾住在黃浦江邊的英美人士回憶他們在上海的生活經歷,這些故事多半強調租界政府對上海近代化的貢獻,對住在上海的幾百萬華人卻著墨不多。這些人乃社會精英,因此他們的著作非屬日常生活史的範疇。然而在華外籍人士並非個個屬於有錢、有教養的上層階級,許多人或為了躲避祖國的戰亂迫害、或為了追求快速發財的機會,千里迢迢來到上海,但終究只能勉強在異地餓口度日。例如有「金絲貓」之稱的白俄羅斯妓女、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落難的猶太人等都屬於上海「邊緣人物」的一種。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在上海的猶太人社群較多,這些著作多半隱含強烈的政治目的,即藉著紀念猶太人遭逼迫、求生存的故事來提醒世人納粹屠殺的罪惡,因此以傳記及回憶錄的形式為主,亦較少談論他們與上海華人的互動。Maisie J. Meyer則探討1845至1949年間猶太人如何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社群,一方面努力為其它外國社群所接納,另一方面必須維持猶太傳統文化。最近Robert Bickers透過上海工部局警察的故事來描繪英籍人士在上海的生活樣態。這些警察不但在社會經濟生活上屬於「邊緣角色」 ,地理空間上他們也身處大英帝國的邊緣。從外籍「普通人」的角度來看上海生活經驗,不但有助於了解上海文化的混雜性(hybridism),更使我們重新思考「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意義:它不但是一種侵略,也是一種機會;對中國人是如此,對在上海的底層外國人亦復如此。
(二)邊緣人物的主體性
日常生活研究最大的挑戰還不在於擴大研究對象,而是如何在許多零碎片斷的生活細節中梳理出有意義的歷史脈絡、並提出重要的歷史問題。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來,學者們的共同焦點之一是「邊緣人物」的主體性問題。在盧漢超的上海圖像中,黃包車夫固然屬於社會底層,但這並不代表貧窮可憐是他們永遠的宿命——他不但強調黃包車夫的生活步調有相當的彈性與自主性,也指出他們向上流動、成為車行老闆的可能性。更令人驚訝的是,作者以黃包車夫的口述記錄、記者的描述及當時中山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的調查報告為證,指出黃包車夫的勞動強度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強。而他筆下的「小市民」 ,雖然生活空間受到限制,但他們似乎總是能夠找到樂趣,政治力量也似乎並未對日常生活的韻律帶來根本的改變。這些細節一方面補充吾人對城市生活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改寫下層社會受到階級剥削的馬克思史學。
其他學者則對這種主體性不這麼樂觀。葉文心所描述的中國銀行行員,每天在機械鐘的規範及公司各種課程的安排下,失去自主性而感到生活的無聊及工作的無意義。董玥及王笛分別關於近代北京及成都的研究同樣把焦點放在市井小民身上,他們一方面強調民國時期小市民對公眾事務的興趣與參與,另一方面則突顯社會興論在政治力的監視及控制之下,呈現相對軟弱的姿態——即使他們的確曾經對妨害私人利益的城市公共建設發出反抗的聲音,這些抗爭並未帶來立即的效果。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這些著作不但很少強調「小市民」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他們所描述的城市生活與街道文化的變化動因,也直接根源於新政策的推行,「小市民」所能享受的主體性是很有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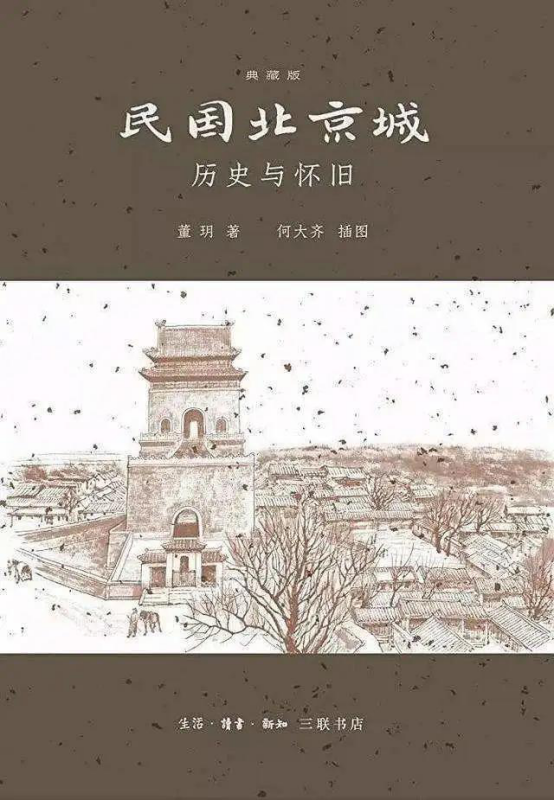
這兩派學者對「邊緣人物主體性」的不同詮釋,主要源自於作者對國家角色的認定。在盧漢超的上海生活圖像中,「小市民」似乎對政治問題不甚關心,「國家」或其它政治性權威也扮演次要的角色。在這一點上,盧漢超比其它作者更堅持日常生活史學的信條,即跳開原本大家所習以為常的大結構,直接從日常生活著手來呈現「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董玥及王笛則不同,儘管在他們的敘述中充滿「小市民」的生活片段,其背後仍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主宰一切,就是過去研究中所不斷強調的「政府」——在這裡所指的不但是地方性的政治權威,有時國家權力亦涉入,特別在北京的例子更為明顯。這使我們不得不追問,我們應如何認識國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一方面,我們的確必須承認,國家或政治權力對個人生活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不過如果日常生活研究仍然重複過去以「國家」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也就是把國家當作形塑日常生活的結構力量,那麼日常生活史學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可以開創新的典範?這個意義上的日常生活史學除了提供更多的資料,它在方法論及歷史解釋上如何突破過去的框架?我們是否需要「日常生活史學」來證明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另一方面,若採取盧漢超的作法,完全避開政治面向,則「政治權力」的位置該如何擺放?個人生活的主體性是否真能揮去政治力的魅影?值得一提的是,盧漢超在2003年出版一篇文章,一改其「非政治」(a-political)日常生活史的態度,以革命歌曲的改編為例,說明一般人如何看待政治。他認為一般老百姓最關心的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細節,而面對政治壓力與動員,老百姓的抱怨往往表現在幽默的大眾文化中,即便在政治氣氛緊張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亦然。例如,文革時期最受歡迎的「我愛祖國的藍天」,歌詞便被改編成「我愛武漢的熱乾麵」,藉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食物,表達對現實政治的挪揄,並以迂迴(也較安全的方式諷刺政府糧食政策的錯誤。換言之,盧漢超自己都已經意識到,即使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史,亦無法完全迴避政治。至於要如何扣連日常生活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一個可能的作法是,反轉國家在歷史書寫中的位置,不把它當作日常生活的基礎結構,而是從日常生活的眼光來看國家,認識國家對市井小民的意義。如此,「國家」便不再是一種本質性存在,而是在不同脈絡下,被以不同方式解讀的權力客體。換言之,國家/人民之間的那條權力界線,恐怕才是日常生活史。
(三)日常生活中的「認同」
此外,學者也透過日常生活的研究來檢視「認同」(identity)問題。研究知識份子的認同可以從他們的著述及言論著手,對於小老百姓、特別是目不識丁的社會底層,則需要從行動(如集體抗爭或慶典儀式的參與)來探索他們如何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而日常生活的細節正可為研究者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從目前的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看來,上海似乎比其它城市存在更明顯的認同焦慮,這可能是上海作為一移民社會,聚集了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型態一方面源自於原鄉文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其它文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出現認同的問題,特別是原鄉認同與上海認同的衝擊與融合。Emily Honig對「蘇北人」的研究提到,「蘇北」乃為上海的江南人士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標籤,它只在移民的脈絡才有意義一事實上這些「蘇北人」來到上海之前從未聽過「蘇北」這個詞彙。對他們而言,同一縣份才是更重要的認同根源。儘管某些蘇北北部縣份的旅浥人士的確組成「江淮旅灑同鄉會」,透過創造新的地域認同以對抗被污名化的「蘇北」,他們卻不認為自己是「新上海人」,換言之,他們並未對新的落腳地産生認同感。盧漢超則認為這些上海新移民形成一種「雙重認同」(dual-identity),一方面他們樂於稱為「上海人」,因為這是進步、現代與財富的象徵,另一方面他們與原鄉維持緊密的關係——不但按時將餘錢寄回家鄉、參加同鄉會組織、甚至希望死後能安葬在家鄉。Honig與盧漢超在觀點上的差異可能來自於他們討論不同的社會群體: Honig所討論蘇北人絕大多數是貧窮的農民,因農村經濟破產才游離至上海謀生,他們對上海的新生活除了求生存外沒有太多的奢望,因此「上海人」的認同並不是他們關注的事。盧漢超談「上海人」認同時主要徵引作家、企業家的話,對這些人而言,「新上海人」的認同可以成為他們的一種文化資本以鞏固在新落腳處的地位。此外,盧漢超對「上海人」認同的討論並不十分令人信服,主要因為他並未說明這種「雙重認同」是在同一群人身上出現,還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認同。若是前者,則他應該以一群人為主要對象來探討不同的社會身份對他們的認同産生何種效應。
除了地域/族群之外,尚有其它區分人我的社會界線,如職業、性別、階級等,不過也許刻意撇清與馬克思主義及女性主義的關係上述研究甚少討論階級意識或性別意識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與表達。王笛對成都婦女試圖取得公共空間可見度的敘述,本來有機會探索普通婦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主張性別認同,但他僅將當時社會改革者對婦女的評論及報紙對社會新聞的描述當作婦女生活實況的反映,以致他無法深入地探討各種論述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只能對個別事件中所透露的性別關係作表面的處理。例如他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婦女被地方當局禁止成群地前往城裡的寺廟進香,她們便轉往郊區的白馬寺及三聖宮,以致於這兩座廟香火鼎盛,週邊的商業也跟著發達。可惜的是,他只停在這裡,並未對這個現象進一步分析。事實上他可以繼續追問:這些宗教活動對婦女的意義是什麼?這群「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層婦女公然違抗當局誠令,有何明顯或隱含的主張?這些都是探討日常生活與性別認同的重要問題,而作者卻只藉此事例說明近代婦女參與公共活動的程度提高,並單純描述她們的「興奮感」 ,致使日常生活史學未能發揮其作為一研究典範所應有的分析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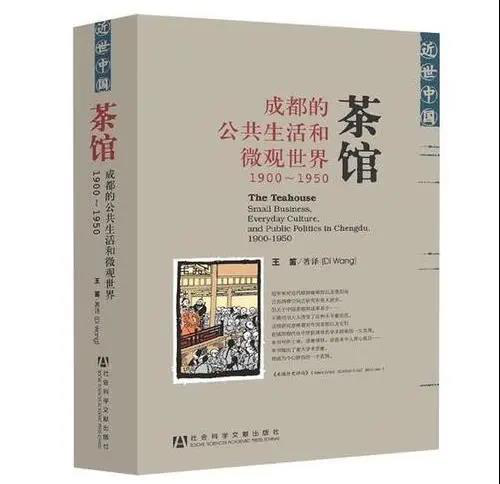
日常生活研究之所以無法使我們對一般民眾的認同産生更清晰的概念至少可以歸咎於兩重原因,一是作者本身對資料中的權力關係不夠敏銳。王笛了解到社會改革者對大眾文化帶有強烈的偏見,但他從這些偏見中所粹取出來的是大眾的確做出如社會改革者所批評的「偏差行為」,只不過他並不加以道德判斷罷了(在較小的程度上,盧漢超的著作亦出現類似的情況)。另一原因則是認識論的問題:當研究對象是年代久遠的歷史、研究者無法進行口述訪問、只能依賴精英份子所留下的記錄時,日常生活研究是否可能?社會底層能為他們自己說話嗎?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並沒有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這也是學界爭論不已的課題,但日常生活研究必須比其它領域更嚴肅地反省這個問題,畢竟它最大的野心便是呈現底層社會的面貌,並從他們的角度觀看世界。
(四)再探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還試圖釐清一個大問題,即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這幾乎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共同話題。從1970年代盛行的「現代化理論」,強調西方産業及行政技術對中國通商口岸現代化所起的示範作用,進而帶動中國整體的「突破」——這當然是合理化西方帝國主義的史觀。美國學者Paul Cohen提出「中國中心」的歷史觀,希望找到中國歷史發展本身的動力。這個呼顧得到很大的迥響, 1980年代起許多學者紛紛投入「早期近代歷史」(early modern history)的領域,注意到西方帝國主義人侵之前中國社會內部所呈現的動態變遷(如人口增長、市場興起、社會分工等) ,結果造成近二十年來對十八世紀中國史的蓬勃發展。日常生活史同樣以「中國中心」史觀為基本立場,不過與前者不同的是,他們多半從二十世紀日常生活的圖像尋找未受帝國主義影響、或即使受西方文化的環伺亦堅持傳統的部分。如果說十八世紀的研究者試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傳統根源」,那麼二十世紀日常生活的研究者便是希望在近代中國找到「傳統餘緒」。
從這個角度看便不難了解何以Emily Honig、盧漢超、王笛、董玥等人把焦點放在社會底層了——這些「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與傳統的情形並沒太大的差異。Honig的研究顯示,西方文明對紗廠女工及蘇北人只有表面的影響,他們可能會購買一些便宜的洋貨、甚至偶爾看看電影,但他們對婚姻家庭的看法及社會關係的運用,仍深受傳統影響。盧漢超尤其強調,儘管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國都市,但在十里洋場之外、甚至在南京路附近的弄堂裡,仍住著大群操傳統生活方式的小市民,對他們而言,「消費文化」指的不是富麗堂皇的大型百貨公司,而是石庫門裡的小飯館及小雜貨鋪。
有趣的是,當Honig與盧漢超試圖尋找近代上海的傳統影子,王笛卻希望找到成都現代化的軌跡——當然這與其城市形象有關。成都作為一内陸城市,經常被認為是「傳統、落後」的象徵,巴金著名的小說《家》也形容它為「保守、專制」的典型。為了打破這個刻板印象,王笛刻意從街道公共空間的變化及街道控制的角度談成都「進步」的一面,如新式的公共娛樂及物質生活、街道秩序的維持等。儘管如此,成都現代化的步調仍然緩慢,成都市民也不斷抵制或抗拒現代規範,結果王笛筆下的成都故事仍然再生產了清末民初精英分子對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前述的進香婦女即為一例。作者本來希望透過日常生活的描述來突顯大眾文化的活力與自主性,但我們所聽到的仍多半是社會精英試圖「改造」老百姓的努力。

民国报刊中的大饼油条与开水老虎灶
王笛的問題可能起因於在他的故事中,日常生活並不能有助於釐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他希望證明成都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一成不變,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貼近社會底層的經驗,因而陷入兩難。這並不是說像盧漢超一樣只突顯傳統就解決問題了,他對小市民傳統性格的過度強調容易使人誤以為這些小市民住在「另一個上海」,但現代商業文化及租界政府的法令的確衝擊了小市民、甚至黃包車夫的日常生活,他們並不是一味抗拒改變的頑固份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董玥提出了「回收」(recycling)的概念。她了解到北京是揉合傳統與現代的城市,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兩者的痕跡處處可見。她借用人類學的觀點,認為人們對傳統與現代的看法就像資源回收,某些傳統的東西若能在現代被再利用,就會被保留下來,若不能用,就會被丟棄,某一件東西在過去與現在的用法也可能不一樣,視使用者的需要而定。董玥最大的貢獻便是從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提煉出概念性原則來重新思考近代中國史的大問題,「回收」是個相當明智的選擇,它不但是近代北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清楚地說明了傳統與現代間的辯證關係,儘管她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說法的人。
在上述著作中,不論作者如何闡述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他們基本上均宣稱拒絕一種社會科學式、單線進行的「現代化」模式,他們的故事中也不斷地突顯現代的行政制度及社會規範如何(無倩地)關入日常生活的領域,打亂老百姓原有的生活節奏與秩序。因此在他們的敘述中,日常生活與現代化通常被置於互相競爭的地位。最近在中國也開始出現「日常生活史」的熱潮,不但社會生活史叢書相繼出版,研究單位也提出整合型計畫從事社會生活史研究。不過中國學者與上述西方學者(包括在美國受教育的華裔學者)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出發點及對現代化的立場有很大的差異。以下所討論關於上海日常生活的兩本著作,即把現代化當作論點的主軸。忻平在《從上海發現歷史》的導論中即表示,現代化是「一個包括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諸領域在內的全方位立體化向『現代類型變遷的過程」。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無論是大規模的社會征服,還是某種被選擇的文化傳播,「都沒有像現代化這樣對極其普遍的人類生活起到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現代化的後來者說更是如此。」李長莉在《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中亦主張,「我們需要回到民間社會,回到歷史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裡,去探尋中國社會生活近代化的實態,從中追尋中國社會近代化變革的内在源流。」忻平與李長莉的學術野心在於建構一幅「全面性」的近代上海圖像,它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及所有的組成份子,尤其是長期被忽略的市井小民——這一點與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關懷是一致的。但他們並未意圖駁斥社會科學式的研究取徑(忻平還利用生物學上的「全息理論」作為研究「全面性」歷史的基礎,期望將史學研究科學化), 也未對「現代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任何批評,事實上他們皆將「現代化」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演進前提。這並不是說他們對「現代化」的結果沒有任何批評,忻平特別指出社會轉型的負面效應,李長莉也描述晚清以來上海的「怪誕」現象,但他們仍認為「現代化」是上海、甚至是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唯一道路。這個觀點其實反映了他們對當代中國「現代化」的樂觀與期待,希望透過對二十世紀前半上海現代化經驗的認識,以找到未來上海、甚至中國發展的目標及可能性。長期主持上海史大型研究計畫的中國學者熊月之談到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價值時指出,「人們正站在這個轉變時期。若回觀過去,當然訊咒上海,但若翻轉頭來,膽望将來,那就不能不歌贊上海,因為上海有無可限量的將來。」從這個角度思考,也就難怪中國學者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乃在尋找「現代化」的可能性,而非挑戰「現代化」的史學典範。
三、典范还是危机
日常生活史是否能突破舊的研究框架、為中國史開出一條新路?那得看我們採取怎樣的研究取徑。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專注於描寫中下階層的生活細節,殊難超越原有的研究架構,形成一新的典範。更大的潛在問題是,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狹窄,不厭其煩地詳細敘述各種瑣碎事物,卻不能從中說明其歷史意義,歷史學家的工作只剩下在舊報紙雜誌堆裡尋找人們茶餘飯後的開談、再將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
但如果我們不只將日常生活的內容當作佐證論點的材料,而是一種幫助我們提問的分析工具,則日常生活史學便可能成為一種新的研究典範,不但有助於提出新的問題,更能使我們重新反省既有的研究架構。例如討論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時,透過日常生活的視點,的確使我們認識到「國家」這個概念,並不像我們所想像那樣,有著清晰而穩定的界線。簡而言之,日常生活研究作為一種「由下而上」的史觀旨在顛覆人們對「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的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
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源自於西方學術發展的日常生活史學是否適用於中國史研究?這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討論,第一是材料問題:我們能否掌握足夠的史料,撰寫「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這一直是研究底層社會最棘手的問題之一。絕大多數人們並不會為自己的生活留下記錄,我們多半透過別人的眼睛來認識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這使得撰寫「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幾成「不可能的任務」。不過近年來開放的檔案資料,使研究日常生活成為可能。例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內閣題本刑科命案類」,便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寶庫。這些由地方衙門審訊、中央判決的命案奏折,雖由官員撰寫,但其中不乏當事人及證人的口供,因此仍然透露下層社會的觀點。前述《中國的一日》 、《上海一日》等書,亦收錄商店學徒、工人的所見所聞,雖然經過編輯的篩選,但仍是來自下層的聲音,得以作為日常生活史的基礎。
第二是本質問題:日常生活史學是否適合用來研究中國社會?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日常生活所提供的是思考問題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文化限制;可是從日常生活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意義,恐怕就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了。前述Benjamin及Lefebvre均以日常生活探討現代性的問題,他們所舉的例子也都以城市經驗為中心,也就是說,他們的關注點都放在日常生活與現代化之間的疏離。在相當程度上,盧漢超等人的著作也把日常生活的焦點放在城市現代性的問題;不過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仍在現代化的門外,農村裡的生存掙扎,與前一世紀相差不遠。因此,如果我們堅持日常生活史是一種以城市為基礎的研究,則大部分的中國農民便落在日常生活史的範瞭之外;如果日常生活史可以打破城鄉界線,則不一定與現代性相關連。換言之,日常生活史學所能貢獻於中國史學的,在於問題意識的提出,更甚於邏輯性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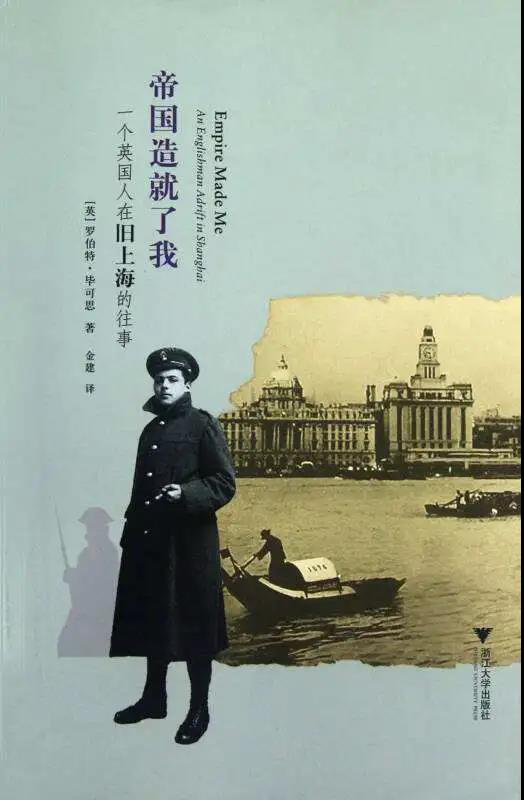
從這幾點想法回到前節所討論的學術成果,究竟日常生活幫助我們認識了中國的哪些層面?又忽略了哪些重要問題?從資料面來說,作者們窮盡力量發掘「關於」市井小民的史料,試圖把這些小人物帶入歷史圖像中,貢獻當然不小,尤其王笛及董玥對成都及北京的研究,更有助於平衡當前過度偏重上海的城市史研究。同時,小市民故事的平易近人,使人產生極為愉悅的閱讀經驗。不過由於多半的資料是從「別人」的眼光看小市民,尚難建立一種「向下而上」的歷史觀點。正因為如此,使日常生活史的書寫無法跳脫既有的框架,而僅成為原有歷史敘述的「次文化」。
因此,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可以有兩個努力的方向,一是挖掘更多的市井小民自己所生産的史料,如日記、自傳、自訴狀等。不過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幸運地找到這些材料;即使找到,我們仍然要問這些材料在怎樣的情境下生產出來的?這也是研究者可以努力的第二個方向,注意到史料生産的權力關係。以日記來說,近代中國及臺灣中小學校向來把寫日記(或週記)當作學生的例行功課,老師需要「批改」日記,因此它並不一定是學生日常生活的如實反映。了解這一點,對我們認識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師生互動關係、甚至教育制度的運作都有重大啟發。換言之,日常生活研究者的職志,並非只在發掘市井小民的生活細節,而是透過其間的權力關係,重新詮釋我們原來所習以為常的歷史。
盧漢超教授致力於日常生活史研究十餘年後,曾語重心長地下一結論: 「研究一般百姓的生活對吾人了解中國及中國史是必要的。這業的研究就像是建築物的磚塊,沒有它們,是無法建造任何建築物的。我們需要磚客來生產好磚來建築中國史,重建中國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這座磚窑。」我也同樣肯定日常生活是一座可以生産好磚的磚客,不過,在製造好磚之餘,如何為中國史研究構思更宏大的藍圖,讓這些磚塊發揮更大的效用,恐怕是更重要的課題。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2020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