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2期
“问题意识”是人类思维的强大动力,是基本的科学探索精神,无问题意识便无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无学术研究的推进。但是,过于强化的“问题意识”,则易导致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所以,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倡导一些“非问题意识”,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和升华情怀中超越问题,可能更符合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这些学科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或许更为强大、更为深远。

“问题意识”及因“问题意识”而产生的成果早已有之。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君臣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讨论,贾谊《过秦论》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分析,都可以说是由“问题意识”催生的作品。当然,如果要归类,这些作品大抵应该归于“社会”或“人文”学科,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或者是“政治学”的范畴。随着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并非虚言。尽管各学科之间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则决定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不同。本文拟以历史研究为关照,就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略抒己见,希望能够引起共鸣,更希望能够得到批评。
学术界对“问题意识”的认识,从来没有像最近20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样强烈,强烈到成为学术研究乃至公共话语的重要甚至“核心”理念。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论文答辩,往往必须回答:“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你准备解决或者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弄得一些博士、硕士也忘乎所以地宣称:“这个问题已经被我解决。”更有不少学者现身说法,指明自己的成功经验,乃是持续不断的“问题意识”的结果,因而倡导青年学者增强“问题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意识”之所以被特别提出并且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而在当今中国,任何事情一旦贴上和“国际”接轨的标签,遂成时髦。“问题意识”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问题意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是人们不断探求未知、不断破解难题的强大动力。可以说,无问题意识便无科学技术的进步,无问题意识便无学术研究的推进,无问题意识便进不了学术之门。“问题意识” 的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已经产生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各类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有大量高品质的作品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被社会诟病的“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以及著作等身、思想贫乏,学者成堆、大师稀缺的状况,却也不能不说与“问题意识”过于强烈有一定关系。因为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违背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容易导致忽略过程直奔结果、关注细节忽略大局,特别是容易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
所以,在对一些尚未步入学术门槛或者虽然已经步入门槛却仍在徘徊的学者,建立或强化“问题意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时髦、成为标签的今日,给 “问题意识”降降温,应该说也有必要。少一些“问题意识”,多一些 “非问题意识”,学者的生产欲望可能会少一些,科学精神或许会多一些;科研成果可能会少一些,传世之作或许会多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可能会少一些,博学通达的学者可能会多一些。这或许也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缺乏问题意识的时候,我们倡导多一些问题意识;当问题意识过于强烈的时候,我们倡导多一些“非问题意识”。
这里所说的“非问题意识”,并非不要“问题意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问题意识,关注“问题”之外的事物、关注看似并非“问题”却是问题所由发生的事物。具体地说,是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情怀中超越问题。如果说“问题意识”是务实,“非问题意识”便是务虚。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也就是说,当急功近利的“务实”冲动使我们“只顾拉车”而“无暇看路”的时候,“务虚”的客观冷静可能会使我们适时放缓脚步并调整前进的方向。
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问题”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成的,“问题意识”则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过程中积极寻找问题并试图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意图或动机。人类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有其自身的规律,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有意识”到意识到“问题”、再到产生“问题意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前提与基础,有意识则是问题意识的前提与基础。弗洛伊德将其归纳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三个层次的递进。

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恰恰是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正是这些心理能量、这些内驱力,从深层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但是,人们首先感觉到的,却是最表层的意识,然后才是前意识,而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潜意识。所以,弗洛伊德在展示他的研究时,是从最容易感觉到的意识开始,向不易感觉到的前意识、潜意识逆向推进。而且,即使在“意识”这个层面,也有从“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递进;而在“潜意识”发生的过程中,还应该经历过“无意识”。从这个角度说,“问题意识”恰恰是思维的表层现象,而“非问题意识”才是思维的深层现象。
可以说,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非问题意识到问题意识,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到人们认识到问题,从人们认识到问题到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动机,是人类的认知过程或者说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新一轮的无意识、有意识、问题意识,以及问题意识、意识、无意识的思维循环,也早在人们的不自觉中开始。在这个过程或循环中发现问题和带着目的寻找问题,是两个不同层级的不同意识。人们发现的问题,有些可能随着人们生活阅历的丰富、知识积累的充实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自然化解,有些则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甚至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生活阅历的加深、社会文明的进步反复出现。正是这些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问题,才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问题意识”,导致人们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意图和动机,或者说,只有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启动“问题意识”进行破解的问题。
所以,从认识到问题到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意图和动机,同样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问题”是要进行“筛选”的,而这种“筛选”也多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跳过过程直接寻找问题、跳过筛选直接解决问题,寻找到的问题固然多、解决的问题固然多,但未必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省略过程直奔结论,往往是欲速而不达。
犹如前些年在学术研究中同样时髦的“填补空白”。当“填补空白”说刚刚兴起的时候,“填补空白”是对学者研究成果的最高褒扬;而当“填补空白”成为时髦、成为标签时,对成果鉴定不说“填补空白”就等于说这项成果没有价值。但是,难道所有的“空白”都必须“填补”吗?或者说,难道所有的所谓“问题”都需要去花大力气解决吗?
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容易在认知的两个阶段发生“问题”。第一,在学习阶段或积累阶段,它跃过欣赏材料感知材料的过程,而这恰恰是在学习和积累阶段必须经历的过程。第二,在研究阶段或突破阶段,它妨碍了直接从材料出发,而是将已有研究作为起点或作为“靶子”。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许多“问题”其实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预设”或者“失误”,其中不少属于“伪问题”。如果不是从“预设”或“失误”出发,而是从原始材料出发,完全有可能直接“论从史出”。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两个途径,是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材料”出发,是“论从史出”还是“论从论出”。
有学者将“问题意识”概括为“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五个环节,认为这五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问题意识。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概括严格地说也只是对自然科学更为适合,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人文学科则未必如此拘泥。如上文所说,发现问题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过程中的“自然而然”,另一种则是带有某种目的的“刻意寻找”。后者可以归为“问题意识”,前者却属“非问题意识”。在自然科学中,“验证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无法验证,结论就说不上是科学的、客观的。但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中,强调 “验证”却过于苛求。而且,越是涉及“人”,越是涉及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就越是难以验证乃至无法验证。
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乃至大众都十分重视的事情。前文提及的秦始皇君臣正是从周朝灭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讨论秦朝的制度建设。讨论的结果,是西周分封子弟,数代之后关系疏远,遂至诸侯纷争、天下大乱。这个结论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此后还部分地被西汉分封、完全地被西晋分封所“验证”。但是,由于这场讨论的主角秦始皇过于直奔主题,“问题意识”过于强烈,过于“功利”,致使完全不屑于不同的意见,完全无视西周分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特别是忽略秦统一中国后“封建”理念的惯性影响及对“分封”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所以,尽管废分封而行郡县,秦朝却是二世而亡,比西周的瓦解迅速得多。但是,秦废分封行郡县的大趋势却是对的。继秦而起的西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秦朝进两步,西汉退一步,在中央势力能够达到的地区行郡县制,中央势力一时难以达到的地区在郡县之上同时建立王国加以控制(始为异姓王国后为同姓王国),是为郡国并行。这个措施看似无为而治,却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看似制度倒退,却成就了两汉的大一统。但是,当西晋刻意效法时,却同样是二世而亡。

贾谊《过秦论》是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反思,固然也是带着“问题意识”,但这时的“问题意识” 已经升华为一种人文情怀,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讨论王朝的兴亡过程。而且,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是贾谊在关注,而是“自然而然”地摆在人们面前,全社会都在“自然而然”地讨论、“自然而然”地进行总结。此后,柳宗元、苏轼等人也加入到“封建”与“郡县”的讨论之中,顾炎武则在分析“封建”与“郡县”的利弊中,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折衷方案。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考察了当年楚汉相争的战场后发表评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被阮籍称为“竖子”的,自然是汉高祖刘邦,以及被他打败的对手项羽。暂且不论阮籍是否不知天高地厚,但他的说法却在不经意间重复了陈胜的理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的出身和个性是没有固定版本的,虽然我们可以寻找到其间的共同点,但作为个体的汉高祖刘邦却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既难以复制也无法验证。一个底层亭长,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一个动辄称儒生为“腐儒”的半文盲,一个几乎被所有的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竟然借着秦末农民战争之势,夺取天下,做了皇帝。而父亲为他树立的榜样、种田能手哥哥刘仲,却在这个乱世之中受其奚落。但是,两百多年之后,也是两兄弟——刘縯、刘秀,哥哥刘縯有刘邦的气象,弟弟刘秀却有刘仲的爱好,但最后“复兴汉室”的,却不是酷似刘邦英雄气象的刘縯,却是颇类刘仲的种田能手和经营高手刘秀。
人文学科可以探求也必须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总规律,但在具体问题上如果强行要“验证问题”,其结果经常让人大跌眼镜,这和自然科学可能恰恰相反。这也导致“历史教训”人人都想吸取、“历史经验”人人都想借鉴,但真正能够顺利吸取、成功借鉴的,却又十分罕见。历史问题,人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加一可以等于二的。
坦率地说,在撰写本文之前,笔者没有任何“问题意识”,完全是从欣赏过程中产生的兴趣、生成的潜意识。回想起来,大概和曾经读过的几种文献以及自己的学术经历有关。
第一种文献是老子的《道德经》(暂且从众说,视老子为《道德经》的作者)。
《道德经》中有两段流传甚广的话。第一段: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窍)。(卷上《体道第一》)
这一段话是《道德经》的开篇,不但为喜好者津津乐道,也为学术研究、历史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常理”和“人情”。而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研究态度,最好是“循常理、顺人情”。
《道德经》这段话对我的启示是:其一,“可道”之道,即通过人们观察、领悟并描述出来的“道”,其实已非客观存在的“道”,因为客观存在的道是不可“道”或难以“道”的。虽然我们不断地想探讨历史的真相乃至试图“复原”历史,但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穷极的,历史的原貌也是不可能被复原的;尽管我们不断地想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我们所描述的仍然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很难相信人类以后的发展真会像现在人们所预测的那样行进。
其二,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通过各种的努力,尽可能地揭示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历史,尽可能在局部和细节上复原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尽可能地在大趋势上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且随着时代的行进,不断修正这些预测。这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动力和终极价值。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被描述的“道”并非完全是客观存在的 “道”,但仍然得继续去探求“道”、描述“道”。
其三,那么,如何尽可能地揭示接近真相的历史、如何尽可能地在局部和细节上复原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如何尽可能地在大趋势上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如何使“可道”之“道”接近“常道”之“道”?那就应该是既“无欲”而又“有欲”,无欲和有欲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道德经》所谓的“无欲”,我喻之为“非问题意识”。只有不带任何的成见、任何的企盼、任何的预设,才可能客观地欣赏历史发展的过程、真切地感受历史发展的脉搏、欣喜地发现历史发展的无穷妙趣,或许能够从中领悟到历史的某些规律。所谓的“有欲”,我喻之为“问题意识”。我们在欣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其间的关节和问题,并且产生出解释或解决这些关节和问题的动机和愿望,同时将这些关节和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做出我们的判断、推进我们的研究。如果没有 “无欲”地欣赏过程,也就难以真正“有欲”地解释或解决问题。
《道德经》的另一段话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卷上 《象元第二十五》)
这段话简洁而富有节奏,熟悉的人更多。有朋友提示,这段话的要害,就是“人法自然”。可以说是一句中的、直奔主题。但是,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情,老子为何要分四句,读起来甚至有些“玄之又玄”?这就是我们对老子的不理解了,说到底,老子是在强调事物的“过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一段文字,有利于我们理解老子为何一句话分四句说。《史记》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有一番告诫: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让孔子把自己的诸多欲望、诸多想法,以及时时以文武周公代言人自居的傲气,统统放下,这样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礼”。“圣人”孔子尚且多欲,尚且多骄气、多态色、多淫志,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所以,“人法自然”要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法地”。地的特点是:“安静柔和,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只有放下种种欲望,像地那样安静平和、奉献不争,然后才可能“法天”。天的特点是:“湛泊不动,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只有像天那样光明无私、包容万物,然后才可能“法道”。只有像“道”那样清净、那样无声无息、那样一切自成,然后才可能“法自然”,才可能像“自然”那样,没有羁绊、没有崖岸,生生息息、永不停顿。说到底,人法自然,是要一切因势利导、顺乎自然。但即使是这样,也只能是“法自然”而不可能就“成自然”。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的境界,这个境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顺乎自然”,才能接近于“道法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才可能更加循乎常理而顺乎人情。
第二种文献是王阳明弟子所录的《传习录》。《传习录》收集了王阳明与朋友及弟子有关学术的通信,以及和弟子们讨论学术的对话。其中王阳明和弟子薛侃之间关于“花”与“草”的对话,在某种程度启发了我对“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的认识,特别是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感受。节选如下:
(薛)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侃关于花善草恶的认识,可以说是“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有欲”;王阳明的“天地生意,花草一般”,可以说是“非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无欲”。只有持“无善无恶”的“非问题意识”,才可能发现:在我们的认识中,当“以花为善”时,往往“以草为恶”;当我们“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假如“问题意识”过于强烈,站在“今日”或“现时”的立场上,立即判断花为善而草为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另一个时空设定下,发现曾经认为“恶”的草,对于人类甚至比一直被认为“善”的花更为可贵时,草已经在当时的“善恶”“意识”下被铲除殆尽了。
所以,后来王阳明给弟子不断宣讲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由“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也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直接为善而去恶,所去之恶未必是真恶,而所为之善也许并非真善。
学术研究其实也是这样,以明史研究为例。明太祖曾经杀功臣、杀贪官、剥夺富人、打击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此是“善”还是“恶”?对当时和之后的明朝有何“善”果、有何“恶”果?明神宗二十年不上朝,除了和皇室利益有关之事,大抵不过问,明朝官场及明代社会在“惯性”中运行。此是“善”还是“恶”?对于明代社会的开放和明朝的灭亡有何“善”果、有何“恶”果?我们只有站在当时人、后世人的双重立场上,在欣赏过程的客观中,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在“理解之同情”的立场上,才可能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花与草、从明朝的存与亡,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精华、何为糟粕?道家是善、是精华?但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被批判为小国寡民、与世隔绝?儒家是善、是精华?但儒家的“中庸”、“仁义道德”不也曾经被批判为“伪善”?那么佛家是善、是精华?基督教是善、是精华?如果用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存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道家、儒家、佛家、基督教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去后、留后还叫道家、儒家、佛家、基督教吗?
虽然王阳明不断教诲弟子,遇事不要“着相”、心中要少一些“芥蒂”,要“儒佛老庄皆为我用”,但王学末流的“空疏”仍然为世所讥。虽然更多是因为时代所赐,但也不能不说和王阳明自己的急迫有关。

《传习录》中收录了王阳明自撰的《朱子晚年定论序》: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
王阳明自己经历过“溺志词章”、“从事正学”、“求诸老释”的长期探索过程,又有“居夷三年”的感悟,并经历了剿灭南赣汀漳民变、平定南昌宁王宸濠兵变,以及应对各种复杂局势的经历后,才提出“良知”的心得,因此他自称这一心得是从“百死千难”中所得。但是,王阳明一方面担心学生“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另一方面又唯恐学生走了弯路,故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于是往往忽略过程,直接讲求“尽性至命”、直接将学生带入“良知”。犹如时下所谓的“心灵鸡汤”,在修心养性上或许立竿见影,但在修习学术上,如果不是本来学有根基,那就只能是“空疏无物”。
第三种文献是徐复观的《我的读书生活》。
徐复观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说到自己拜熊十力先生为师的一段轶事:
第一次我穿军服到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看他(熊十力)时,请教应该读什么书。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经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候再去见他,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他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我接二连三的说出我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他老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
徐复观当时刚刚三十岁,已经是国民党陆军少将,可谓春风得意。熊十力的一番骂,骂得这位“陆军少将”目瞪口呆。但徐复观认为,正是这一骂,骂得他在学术上“起死回生”。按时下的说法,徐复观在“国学大师”熊十力的要求下重读《读通鉴论》,是带着批评的眼光、带着“问题意识”去读的,却被骂得狗血淋头。在熊十力看来,读书首先应该是“欣赏”,特别是对于《读通鉴论》这样的名著,应该先看到书中的好处,吸取书中的营养。在欣赏中发现问题,并且进行超越。
这个故事不少人都知道,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读书的方法、研究的方法。读书本来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可以充分享受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各种信息、感受作者传递给我们的各种情感。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作者的一些问题。前者是强大自我、提出创见的基础,后者是超越前人的关节和契机,二者相辅相成。没有过程的欣赏,很难发现“原生”的问题。问题从哪里来?当然可以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来。但是,如果忽略了欣赏的过程,没有发现“原生”问题,可能一开始就陷入和已有研究的“预设”对话,而不是和古人、和历史直接对话。
曾经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激发出诸多的优秀作品。但是,这些真正优秀作品的特点,恰恰不是因为它们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如有无萌芽、何时发生萌芽、以及这些萌芽是否能够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淡化“萌芽”的“问题意识”,老老实实地阅读史料,在阅读中欣赏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态,发现具体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然后解读或解决问题。而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导致学者把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有清代萌芽说、明中后期萌芽说、元末明初萌芽说,以及元代、南宋、北宋、唐代、南北朝、东汉、西汉、战国等“萌芽”说。
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尽管我们宣称是在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研究问题,但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中,最被忽略的恰恰是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一个原则:“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一场运动、是一个过程,是一场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偶然”。由于这个偶然在后来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于是我们就认为它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而这个特定的问题假设,促使几代学者苦苦寻找我们自身的这种“必然”的蛛丝马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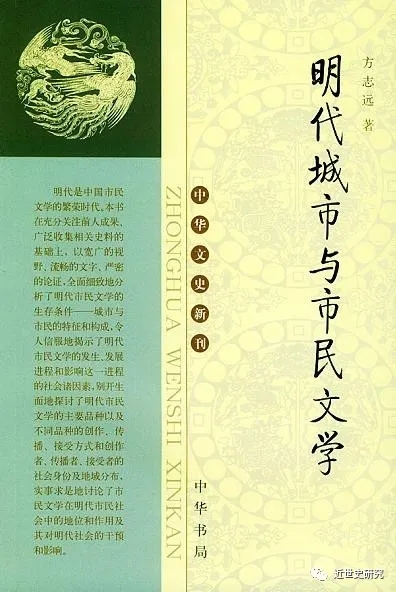
或许是受业师欧阳琛教授的影响,也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书”气氛的浓烈,笔者在步入史学门槛的一段时间里,得以安心读书,而且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不带任何“问题意识”的读书。读什么书?读最为常见的书。读通史的顺序是《春秋左传正义》《史记》《资治通鉴》,读明史的顺序是《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会典》。同时读明朝人的笔记。读哪些?学校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有的《纪录汇编》《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初编》等收录的明人笔记,有什么读什么、见什么读什么。
一年多下来,笔记和卡片做了许多,文章一篇也没写。当时有关心我的老师觉得奇怪,说有几十张卡片就可以写论文了,你抄了几千张吧,怎么不写论文?我说我老师不让写,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写,还有许多书没有读。为何会是这样,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逐渐明白,先师是让我在阅读中“走进”历史、“感受”历史,“走进”明朝、“感受”明朝。如果不是要写毕业论文,我估计先师还会让我再读下去。写毕业论文怎么办?还是读书,读《明实录》和相关文集、笔记,而不是读已有的研究成果。毕业以后的若干年,仍然是不带任何目的读书,读先师早年为中正大学(江西师大前身)购置的南京图书馆藏钞本《明实录》(当时黄彰健先生主持校勘的台湾“中研院”校勘本尚未在大陆流行),许多“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当一些朋友将《明实录》《明史》视为“常见史料”而弃之不顾时,我却感觉从中受益巨大。
大概是因为这个过程,我的研究习惯或“路数”和很多学者不太一样,第一步不是从“学术史”中寻找问题,与研究者对话,而是在“阅读文献”即“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与古人对话。开始写“内阁”“巡抚”“镇守中官”“御马监”,后来写“江右商”“传奉官”“山人”“冠带荣身”,都是在写完初稿之后再去关注“学术史”。十分幸运的是,竟然少有“撞车”;即使“撞车”,由于资料比较详实、视野比较舒展、角度比较独特,所以“闯关”也比较顺利。这大概是因为认识直接从史料中来,较少被后人的研究“先入为主”,较少“成见”与“崖岸”,所以可能更为接近当时的 “实况”。
只有欣赏过程,才可能使学者站在更加客观的立场上,尊重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如明朝的灭亡,是李自成推翻、多尔衮终结的。但是,如果站在更加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灭亡”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契机不止一个,当时种种看似偶然的因素聚集在一起,已经到了不得不亡的时候了。万事万物,有生就有灭,从来没有真正“传之万世”的朝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文学语言,其实也是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过程的研究境界。
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一文中曾发过这样的感慨:
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应该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却不必也不可能揽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背上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
重读这段感慨,发现其实是在说两个概念:一个是“情怀”,一个是“问题”。我一直认为,自然科学需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应该更为强烈;人文学科更多的是在“解释”或“解读”问题,所以需要多一些“非问题意识”以培育人文情怀、超越具体问题。即使是“自然”科学家,当研究达到一定境界时,也必然会注入更多的人文情怀,这才是他们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终极动力。我们熟知的许多华人科学家,如华罗庚、李政道等,恰恰是因为拥有博大的人文情怀,才促使他们走上研究科学的道路。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能够通过“问题意识”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主要是具体的考证问题。如前见顾诚教授考证沈万三的活动时间是在元朝还是明朝,以及为何明明是元朝人却被误认为是明初人的问题;再如近见南炳文教授考证之“沈周”何时到南京,以及为何有关于沈周11岁或15岁到南京的记载的问题;再如我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考证诸多“传奉官”真实身份,以及他们的公开职务与真实身份关系的问题;等等。以历史学科为例,人文学科能够解决的,主要是“有形”的问题, 即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事项,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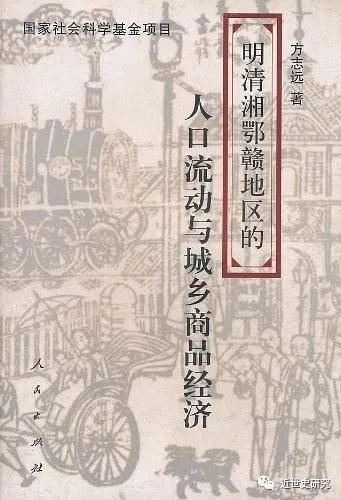
对于“无形”的问题,如谷霁光教授关于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之“拗”的解释、吴晗先生关于明太祖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的解释,以及《“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关于传奉官现象与明代中期多元化社会的关系的解释,等等,都只能是解释而很难说是已经解决,更不用说明朝为何亡而清朝为何兴、中国走出中世纪为何如此艰难等“巨大”而且“无形”的问题。
其实,许多人文与社会问题,是无法真正有定论的。我一直为忘记一则史料的出处而耿耿于怀。这则史料是一位晚明官员的笔记,说是在崇祯十三、十四年间(1640—1641),西北有张献忠、李自成,东北有皇太极、多尔衮,官场中文官爱财、武将怕死,皇帝又是没有经过实践历练的青年,明朝眼看无法收拾,于是人们竟然怀念起魏忠贤来:觉得如果这个时候“魏珰”还在,以“魏珰”的铁腕,国家恐怕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而就在十年前,魏忠贤还是人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
当然,即使是看似“有形”的问题,我们常常也未必能够“解决”而只能“解读”。比如陈寅恪先生关于“牛李党争”中牛党多寒门而李党多世族的著名论断,再如田余庆先生《蜀史四题》中关于刘备集团中的中原、荆州、蜀中三大势力关系的分析,等等,都是言之有据且鞭辟入里,但历史的“真实”未必完全如此。再如我在《阳明史事三题》中提出的王阳明没有生育能力的推测,自以为理由充分。但《阳明年谱》明明记载,在原配诸氏去世之后,续弦的张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继承王阳明“新建伯”爵位的 “嗣子”王正億。真相到底怎样?恐怕只有动用“DNA”了。
周一良先生曾经用六个“W”概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诸要素: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为何)。我们能够解决的,充其量只有两个半“W”,即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或事件的部分内容,其他的只能是解释。那么,用什么理念进行解释,当然要有“问题意识”,但我认为,更需要的是“人文情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人文关怀”,也可以说是“非问题意识”。
前些年读刘大椿教授的《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感到有知音;近日读黄宗智教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更感到振奋。在当代知名学者中,黄宗智教授是十分强调“问题意识”的,但就在《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这样讨论“问题意识”的文章中,他开篇就说:
今天回顾,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也许是个人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对我来说,主要是在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并存和矛盾之中,怎样来对待其间的张力、拉锯、磨合,甚或融合和超越。这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甚至更是感情层面上的过程。这样的矛盾可能成为迷茫和颓废的陷阱,但也可以是独立思考和求真的动力;它可以使自己沮丧,但也可以成为深层的建设性动力。
黄宗智说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虽然用了“也许”两个字,但真切地呼唤出“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而这个“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显然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问题意识”所说的“问题”,而是深切的人文情怀。所以,他说自己50年的学术历程,既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更是“感情层面上的过程”。那么,是什么样的“感情”推动作者做出学术的转变并向学界和社会贡献出一部又一部高品质的作品?

黄宗智并没有把答案放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而是放在“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作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正是这种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为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的感情和情怀,成为黄宗智价值观上的“关键动力”。而黄宗智所说的这个“关键动力”,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之前的“潜意识”。如果黄宗智自己不揭示出来,谁也不会把他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1948年的一场使上海一夜之间冻死三千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自然更不会把这些著作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闲书”的影响,和“侠义”的精神、“抱不平”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虽然黄宗智为这篇“回顾五十年”的文章取名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但自始至终都在阐述自己的人文情怀,并且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强调:
回顾自己过去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们习惯认为“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理论修养,而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它其实更来自于感情。而且,感情的驱动,区别于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更可能成为个人长期的激励。
这种情怀开始的时候往往不易被察觉到,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但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恰恰是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正是这些心理能量、这些内驱力,从深层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
黄宗智的这种人文情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非问题意识”,正是老子所说的 “无欲以观其妙”的境界。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然是由无数的问题组成的 “问题意识”在推动,这也是老子所说的“有欲以观其窍”的过程。
不仅仅是黄宗智,黄宗智的老师萧公权、和萧公权同辈的钱穆,同样是具有深切人文情怀的学者。萧公权先生“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境界,决非一般的 “问题意识”可以企及。钱穆先生的巨制《国史大纲》,首揭中华文化的三大特征:历史的“悠久”、发展的“不间断”,记载的“详密”。可以说,“中华文化”这一大情怀,是钱穆所有著作的“原动力”,是超越和驾驭研究过程中所有“问题”的大视野。
岂止黄宗智、萧公权、钱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伟大学者,皆有大情怀。司马迁的情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我们常常说“无欲则刚”,既然“无欲”,为何要“刚”?“刚”的目的又是什么?“刚”说明有欲,但非一般的欲、非世俗意义上的具体的“欲”,而是有大“欲”,有大的抱负和大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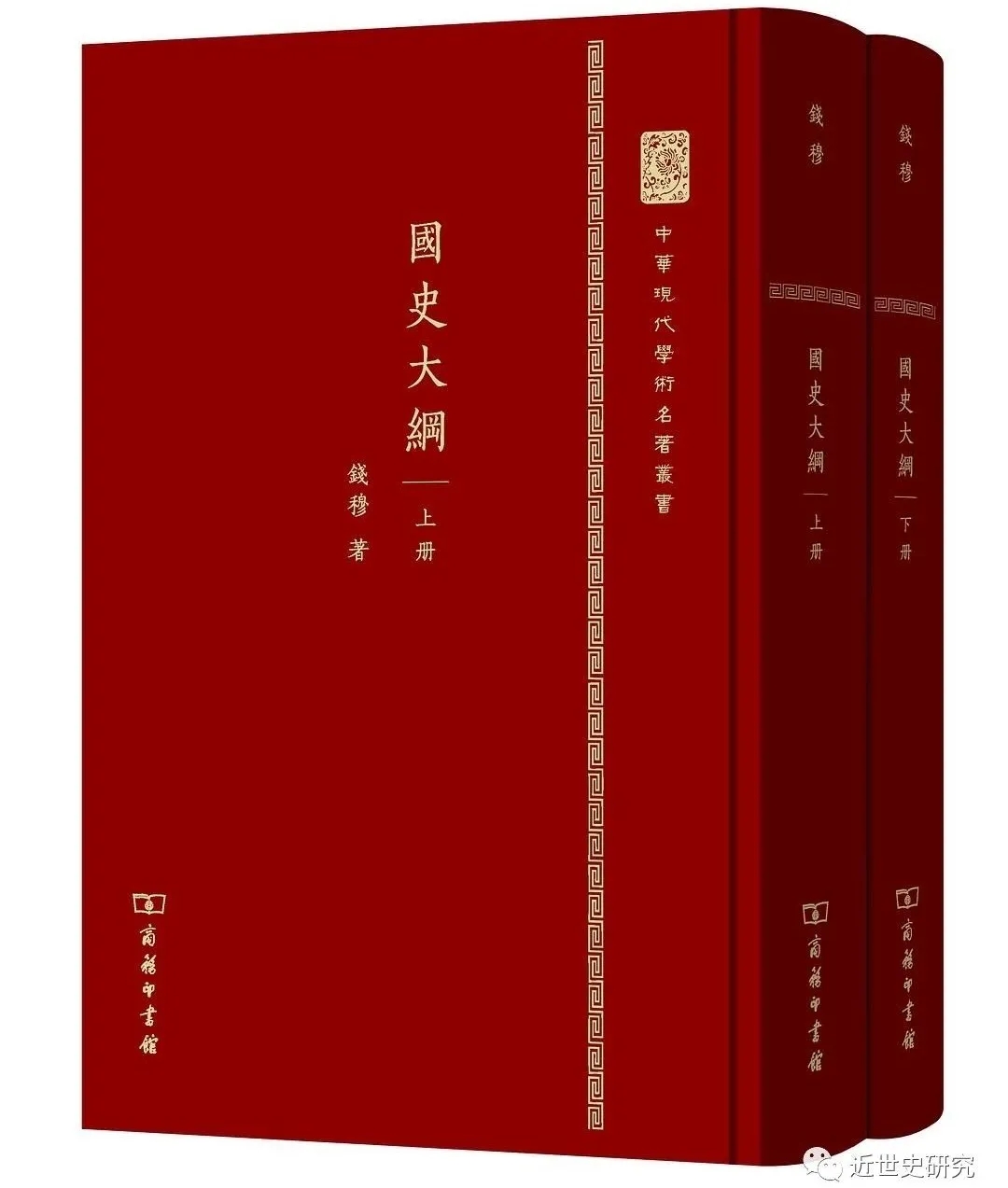
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命题:“为学术而学术。”就我看来,“为学术而学术”也应该有两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心无旁骛地关注正在学习或研究的对象,把学习或研究做到就专业要求而言可能达到的极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意识”应该是基本的动力。没有这个层面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问题意识”,就根本进入不了学术。但是,当学术做到一定的层面,得进入第二层境界也是更高的境界。
那么,一个学者所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是什么?不同的学科可能各有不同,就历史学而言,我认为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我们最终也许只是自以为“通古今之变”,但是,我们却需要带着这样深切的人文情怀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才是历史学 “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
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人文”,与其称之为“科学”,倒不如称为“学科”,除非我们建立起划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不同的界定标准。否则,按自然科学的要求,人文是无法进入“科学”范畴的。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完全没有必要硬挤进以 “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科学”行列,也没有必要用自然科学般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其科学性。否则,或许成为“科学”了,但“人文”也就剥离了。
近几十年人文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各种困境,与用“自然科学”的理念进行要求、用“自然科学”的办法进行管理不无关系。这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并非福祇,而是灾难。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完全在管理者,也在一些人文研究者自身,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学问,为何硬要往公式化的“科学”行列中挤?
今日的人文学科论著不可谓不多,问题意识不可谓不强,但为何难以出“大制作”,恐怕在于“非问题意识”不够,急功近利,人文情怀缺乏。似乎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好的作品;没有“非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大的制作。而缺乏人文情怀的作品,则不可能奢望得到社会的人文认同。
相比许多勤奋的学者,我比较懒散;相比许多高产的朋友,我属于低产。人与人之间,性情、阅历、师从和环境不一样,学习、研究的路数可能也不一样。这篇文章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不主张过于“刻意寻求”问题,而是建议多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主张在倡导“问题意识”的过程中,多一些“非问题意识”,多注入一些人文情怀。如果这样,学者的胸怀可能更加博大、视野可能更加宽广,境界可能更加升华,作品的穿透力可能会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