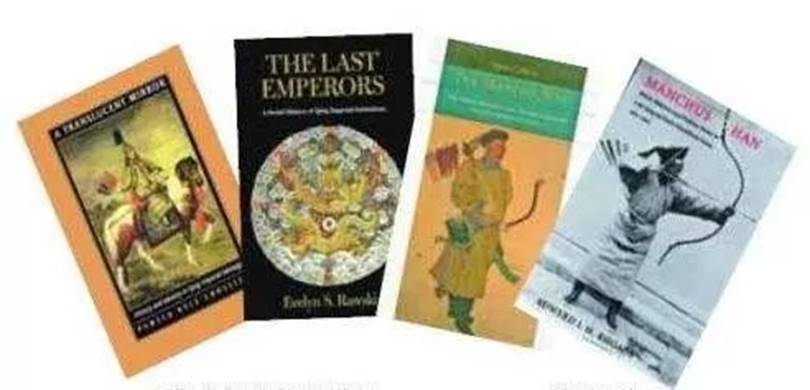
近几年来,对于美国新清史研究的讨论已经逐渐成为国内清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在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还主办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对有关新清史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很深人的辩论。我也旁听了这个会议,加上在美国学习期间对新清史的学者和著作有一些了解,因此,在这个报告中,我属于班门弄斧,简单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新清史,它的起源和现状,主要论点,以及它对美国和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影响。
首先谈谈美国“新清史”的起源。“新清史”并非空穴来风,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在美国清史学界,是和当时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潮流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独霸美国中国史学界一时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区域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关注逐渐由政治、外交、儒学等“上层建筑”下移至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的地方史;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理论逐渐被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变量的区域社会史所替代。
在90年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热潮又有一次转变,新文化史逐渐兴起,使得美国的清史研究更加多元化。许多“新文化史”的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新认识史料的主观性和局限性,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重新定位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
我认为,所谓的美国“新清史”,是90年代兴起的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其方法和理论多受到当时美国文化史学者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新清史兴起于90年代中期,与新文化史在美国中国史学界的兴起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2)新清史研究着重强调满洲人和满洲统治文化在清帝国时期的作用,这种对于满洲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源于新文化史中对于传统史学所忽视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强调。
(3)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新清史中对于新文化史中广泛使用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非常强调,这几乎是许多新清史著作的理论出发点。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个很庞大的理论体系,简单来讲,在历史学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西方文明对于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体系的重建,以及这种知识体系的重建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后现代、殖民主义理论还强调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影响。
新清史正是应此而生,其中心理论是让清史研究者跳出“中华民族”或“汉族——少数民族”这一在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重新认识满洲人和清帝国。

何炳棣(1917-2012)
值得一提的是,新清史在美国并不能称之为一个学派。被称为新清史的学者,主要分散在满族史、边疆史和清代中期的政治文化史等研究领域。其主要代表作有:在满族史方面,有欧力德《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民族认同》和柯娇燕《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在边疆史方面,有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和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在清代中期政治文化史方面,主要有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民族认同》和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1680-1785年清帝南巡与清朝统治的构建》。
这些学术著作在理论和结论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其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野不尽相同,有些学术著作甚至在相同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如同样是针对满洲人在有清一代的民族认同问题,虽然欧力德和柯娇燕都批驳以往学术界的满洲人在清代后期全盘汉化、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性、消失在汉人的群体之中的观点,都认为满洲人即使在清代后期、甚至清代灭亡之后仍保持着民族认同,但是柯娇燕认为这种民族认同主要来源于满洲人应对晚清诸次危机——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的一种内生的心理变化,而欧力德则强调外部因素——如清政府政策和八旗驻防等对于满洲人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新清史在美国学界是由许多同时兴起的、自发的、分散的研究汇集而成的一种学术潮流,并非有组织、有负责机构和期刊、有特定目的的学术研究团体。其着重于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中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批驳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清史学界对于清帝国的性质和满洲人汉化等问题的研究,如梅谷《满洲统治的起源》,何炳棣《论清史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芮玛丽《中国最后的保守主义:同治中兴》等论著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论断,而并非主要针对中国学者对于清史中关于边疆、民族等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很多美国新清史的学者曾来中国进行过长时间的调研,并且从中国学者对于边疆、民族等问题的研究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使得他们可以进一步反思美国学界以往对于这些问题认识的不足。
由上可知,新清史在美国学界经历了一个自发的、纷乱的发展过程,其代表作甚多,观点也不一而同。在下文中,我将简单的介绍这些新清史研究的主要著作,并尝试将其归类为三个主要观点,其挂一漏万之处,请读者见谅。
一、“满洲中心论”
总体来说,美国新清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论点之一,“去汉族中心论”,或者称为“满族中心论”或“满洲中心论”,这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的新清史的论点。以往美国清史学界非常强调满洲人的汉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为芝加哥大学的何柄棣在196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论清史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
在这篇论文中,何柄棣从清代的疆域、人口、政治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指出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其中在定义清王朝性质的问题上,他指出:“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的统治者采纳了系统的汉化政策。”这些系统汉化的政策体现在满洲统治者在入关后对于明代政治制度的全盘采纳,清代皇帝自康熙始便将朱子理学奉为正统并参拜孔庙,用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宗室子弟,并且支持出版了如《四库全书》之类的宣扬儒家正统学说的书籍等等方面。新清史的学者则对于何柄棣等学者所提出的满洲全盘汉化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美国亚洲研究会会长的罗友枝在1996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的主席致词《重新审视清史: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罗友枝系统地总结了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关于清代国家性质和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动向,针对三十年前何柄棣提出的满洲全盘汉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她指出,最近学者们发掘的新的满语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清帝国和满洲人的认识,使用这些满语史料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史料,改变了传统以汉文史料为中心作清史研究而导致的认识偏差。
例如,尽管清代皇帝在汉文史料中的形象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统治者,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根据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帝国的不同属民之前,满洲皇帝们塑造了不同的统治者的形象。何柄棣认为清帝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满洲早期统治者的系统汉化,而罗友枝和其他新清史学者所持观点则与何柄棣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汉族聚居的地区”。罗友枝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影响重大,可以视为新清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基石之一,自此之后,新清史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些著作也日益获得学者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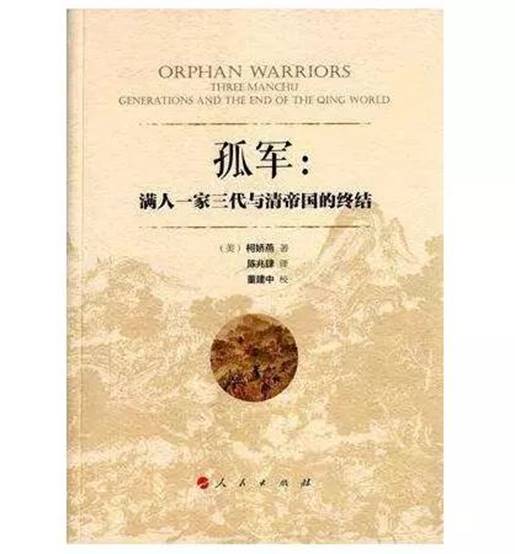
柯娇燕著《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书影
针对满洲汉化问题,除罗友枝这篇研究综述之外,还有几部颇具分量的研究专著。早在1990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柯娇燕教授便发表了《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一书,从一个满洲家族的三代人——杭州驻防的苏完瓜尔佳氏的观成、凤瑞、金梁三人的角度来叙述清代中后期的满洲人的历史。柯娇燕将这一家三代人的荣辱沉浮融人到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以他们为视角来审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八旗驻防制度变迁以及满洲人的民族认同等重大历史问题。
她指出用“汉化”这一话语来研究满洲人的历史不但非常模糊,而且饱含民族主义偏见。她所得出的结论是满洲人在清朝的中后期并没有汉化,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保留了作为满洲人的民族认同。在19世纪中期,随着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逐渐缩减对于各地驻防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扶持,随着作为旗人的诸多特权的逐渐消失,地方驻防中的满洲人,如杭州驻防的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祖孙三代,并没有在文化上和心态上放弃自己是满洲人的事实,反而在诸次社会动荡的磨难中增强了他们与汉人的隔离和作为满洲人内生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性。
在此书出版的11年之后,欧力德教授出版了《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民族认同》一书。柯娇燕对于满洲人的研究是一个对于八旗驻防满洲家族的个案研究,并且几乎没有使用满文资料;而欧力德的这本书是对于清代八旗和满洲民族认同的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研究著作,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满文材料。
欧力德着重于的八旗制度的研究,并且将“民族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析变量来研究八旗史和清史。他认为满洲的民族认同是和八旗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清代八旗制度的延续性和成功性,才使满洲人保持其民族认同。他进一步论证清帝国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帝国,不仅仅在于满洲统治者采用了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更在于它运用八旗制度,成功地使满洲人在有清一代都保持其民族认同,没有消融于汉人群体之间。
总之,多数美国新清史的学者强调满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对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些材料才是正确认识满洲统治和清代政治的关键。他们主张更谨慎的定义“汉化”,区分“汉化”、“同化”和“涵化”之间在民族史研究上的不同含义,尽量避免使用“汉化”这一带有歧义的话语来定义清代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他们认为清帝国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够开拓广大的疆土,并非因为满洲人汉化,而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将其与中国传统统治文化相结合。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的反思。这些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几乎都认为20世纪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多多少少扭曲了我们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清帝国这种少数民族征服王朝的认识。他们认为受中国民族主义影响的近现代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出于民族国家政治利益的考虑,过于强调“民族融合”,过于强调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过于强调少数民族的“汉化”,从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自身的民族认同和统治特点。
二、清王朝的“帝国性”
新清史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是重新审视清朝的“帝国性”。除了上文所述的民族史外,边疆史研究也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话题。新清史的学者们重新审视了清帝国的扩张,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如耶鲁大学的濮德培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从康熙至乾隆朝清军和准噶尔部的诸次战争的性质,他指出将清廷对于准噶尔部的征服描绘成中央政权对于地方叛乱的平息是扭曲事实的,进而指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真正性质是清帝国和准噶尔帝国争夺欧亚中部内陆的霸权,最终以清帝国的胜利和准噶尔帝国的失败而告终。
濮德培不但关心历史事实的本身,还关心在这些征服战争结束之后,清代的学者、民国的学者以及共和国的学者是如何书写和构建这些战争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关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影响。除了以上对于清朝的领土扩张是否是帝国扩张的征服战争还是民族主义历史框架之下的平定叛乱的讨论之外,部分新清史的学者还讨论了清朝对于这些新扩张领土的统治的性质。如乔治敦大学的米华健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邓津华分别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和《台湾的想象地理:中国殖民写作及图片,1683-1895》讨论了清政府对于新疆和台湾的统治性质,并指出这种统治与同时代的欧洲殖民国家对于殖民地的统治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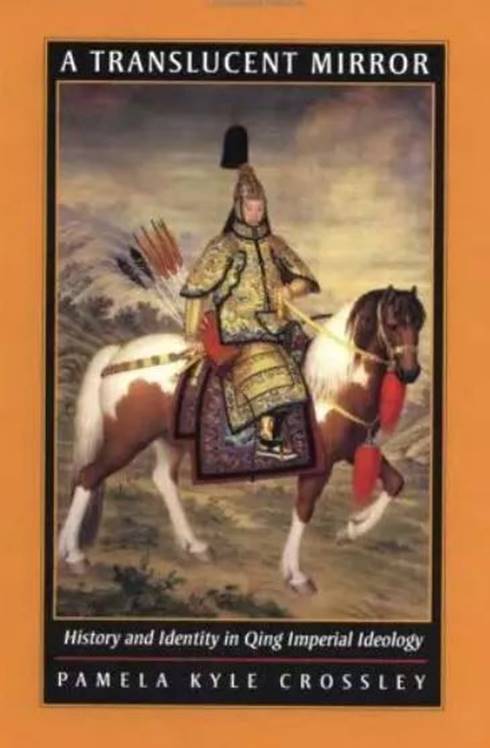
柯娇燕著《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民族认同》书影
除领土扩张之外,一些新清史的学者还对清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加以研究,以重新审视清王朝的“帝国性”。他们强调清王朝在统治的意识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中原王朝,清帝国并非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由汉化的满洲人所统治的如汉朝、唐朝等中原王朝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普世性帝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柯娇燕在2000年出版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民族认同》一书。
此书虽然晦涩难懂,却是新清史重要的理论奠基石。她指出,在清代中前期不断的领土扩张中,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对臣民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清代民族和民族性界限也受到政治因素和征服战争的影响。在乾隆朝,随着领土扩张的基本结束,清帝国也终于在统治的意识形态上日臻成熟,将其定义为一个包含有满、蒙、汉、藏、回五族的一个普世性帝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或者是汉化的满洲人所统治的王朝。
乔治梅森大学的张勉治教授于2007年出版的《马背上的朝廷:1680-1785年清帝南巡与清朝统治的构建》一书也是新清史中讨论清中前期统治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书中,张勉治详细分析了清帝历次南巡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并以南巡为视角来审视清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他指出,南巡是清代中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帝的历次南巡,不但是为了笼络江南的士绅、巩固统治,也是展现满洲皇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统治者后裔的传统。他指出在乾隆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民族-王朝统治”;乾隆皇帝通过历次南巡,希望对“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有支配地位的江南地方精英”建立起“家长式的支配”。
三、清帝国的“世界性”
新清史第三个主要论点是重新审视清帝国的“世界性”。新清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清帝国并非一个孤立的帝国,而是作为在16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印度卧莫尔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司徒琳主编的《清帝国在世界历史时间中的形成》一书,许多新清史的学者,如濮德培、米华健、罗友枝等均在此书中发表论述,他们阐述了清帝国和其同时期的大帝国在领土扩张、帝国内的多民族统治和帝国内的行政、财政运作等相似性;从而认为不应将清帝国视为孤立的、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国,而是应将清帝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进行考察。
正如司徒琳在序言中所说:“这些学者将清帝国视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多民族帝国和殖民帝国,而不是将其视为文化上狭隘、地缘上孤立的明王朝的延续,从而进一步否定了清王朝的性质是一个由被同化的异族统治者通过‘汉化’来实现其统治中原王朝。”同时,司徒琳还强调了清帝国的“早期现代性”,并将其纳入到同一时期欧亚大陆的诸多帝国的政治统和和文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去。又如濮德培在《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中,将清帝国视为同准噶尔帝国和沙皇俄国竞争争夺亚洲中部的霸权的帝国之一,并详细阐述了这三个帝国在为取得这场霸权争夺战的胜利而在军事、制度和经济财政方面的竞争。在柯娇燕和张勉治对于清代中期统治意识形态的论述中,也有不少清帝国和同时期的亚欧大陆上的帝国在统治意识形态上的比较和分析。可见,新清史的学者认为在清代边疆史、政治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不应该将清帝国同这些同时期的欧亚大陆帝国的联系割断,而是应当将清史放置于世界史之中,将清帝国的统治发展趋势与16世纪后期以来欧亚大陆的帝国发展潮流相联系,以丰富和深入对于清朝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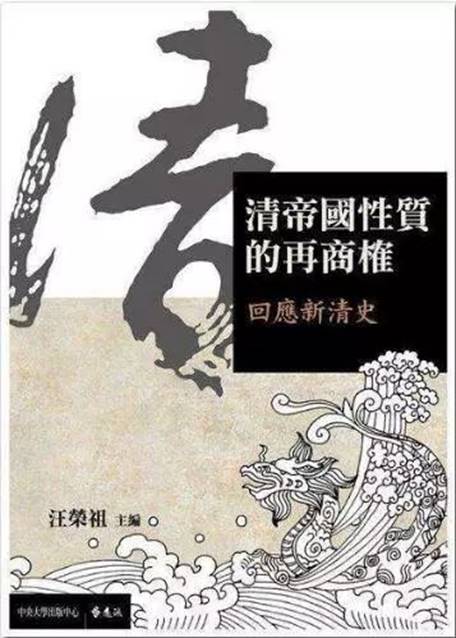
汪荣祖著《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书影
总之,虽然在美国中国史界的新清史研究已经不能称之为“新”,许多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主要的论点也被普遍接受;但是美国学者对于民族史、边疆史研究的热情并未减退,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会有更多的相关学术著作问世。
新清史的许多观点,如对民族国家历史架构的反思,对于清帝国“世界性”的认识,对于清帝国统治文化的理解,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审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新清史的局限性,如对满洲是否汉化的论断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如急于划清自己同传统史学的界限而导致的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偏差,如很多学术著作都集中于清代中前期——尤其是乾隆一朝——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对于清代中后期如嘉道等朝的讨论略显不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满学论丛》第一辑,作者张婷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满族文化网 2020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