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 《乡里的圣人》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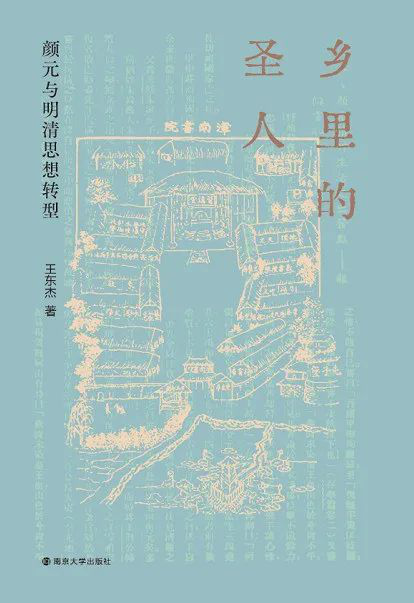
颜元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要角,任何一部讨论明清思想转型的著作,都难以绕过他的名字。可是,多数读者虽耳闻其名,却很少留下特别深入的印象。就当代史学的潮流看,颜元处在不上不下的境地:往上,其影响力无法与同时代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相比;往下,他也不是深受晚近史家追捧的“匹夫匹妇”。颜元虽似知名(在“听闻”的意义上),却又不怎么为人所知(在“了解”的意义上)。
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大都倾向于强调颜元思想的突破性甚至“现代性”。他的气质论、习行论和以致用为标准的学术取向,被不同程度地拿来同“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民主主义”相比,乃至被视作“礼教”批判的先声,而全然不顾颜元本人就是礼教的推动者。这些抽离颜元时空所在的论点,无疑歪曲乃至颠倒了他的本意。
现代史家深受社会科学影响,更关注物质性、群体性、结构性的因素,倾向于低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同时代多数儒者不同,颜元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而是生长在一个基层小吏和农民家庭,自己亦曾耕田劳作,日常所接触者,也多以乡民为主。这种生活环境和经历构成颜元一生事业的底色,使其思想取向流露出一种拙朴坚毅的农家风味,其长短之处皆在于此。
晚近以来,明清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视域渐趋融合,“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得以进入公众视野。本书从颜元的生命体验、时代风潮、乡里交游等多个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何以深入民间。作者认为,若想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了解思想的历史,就绝不能忽视颜元这样的“基层圣贤”的作用。他们既通过引用“大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统一,也通过自己的选择决定经典和精英理念进入社会的渠道和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思想的流向和力度。透过“基层圣贤”这一中介,作者进一步阐释了作为受教化群体的阎闾小民,如何按照自己的想法再次改写了正统思想。
后 记
这项研究本不在我的学术计划中,只能视为自己偶尔的一次放逸之举。而我之所以不务正业,溜出来与颜元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一个原因是我的上一个课题已经结束,下一个课题尚未展开,中间休息,东看西看,一时兴起,不免“误入歧途”。
这些文章的最初推动者是张循,第一章原本就是由他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激发的,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细读了颜元史料,又牵连出新的线索,遂有后续的第二、三两章。各章写作完毕,亦经其费力一阅,提出若干修改意见。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与内子辛旭及学友韦兵等分享和研讨其中的一些观点,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的刘文楠慷慨拨冗通读一道。他们热情的鼓励和精彩的质疑都体现于修改后的文字中,为本书增色不少。当然,余下的缺陷和错误,则统由我文责自负。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清华大学的靳帅、郑思俊,北京大学的李辉祥几位同学都为我提供了资料方面的帮助,也一并感谢。
2018年6月,经当时还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瑞教授邀请,我曾前往该校演讲,其间拜访了研究颜李学派的大家陈山榜教授,蒙其慷慨惠赠一套《颜李学派文库》。陈先生多年致力此一课题,为学专注,为人豁达,令人钦佩。与王坚、李敏两位年轻学友的交流,亦使我受益良多。
此次又经博野县文联主席孔繁浩和颜元研究室郑文林(现已调回博野中学)两位先生安排,前往博野北杨村和蠡县西曹佐村,拜访颜习斋祠堂和李恕谷墓。颜元族人颜世绪提供了有关祠堂和颜元的资料。这次拜访途中,有两件事使我至今难忘:一件是,习斋祠堂房屋破损,灰尘遍布,油漆脱落,院子里摆放着几块石碑,其中一些是从颜元墓中迁来,而墓地在“文革”中被破坏已尽,于今竟然无存!另一件是,寻找李塨墓时,我们几次向当地人打听,均不得要领,直到遇到一位赶车(在颜元的认识中,赶车就相当于六艺中的“御”)的老人,告诉我们:不知道有“李塨墓”,但这附近有个“恕谷墓”。这才柳暗花明。此事使我意识到当地仍保留着许多今日已难得一见的礼数。见到父老对李塨的尊重,然而又不无几分隔膜,多少构成本书第三章未有明言的认知“原型”。
郑文林先生是一位素心且热心的绩学之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对之如数家珍。离开博野后,我多次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叨扰文林兄,皆承他不厌其烦,慷慨指授。2021年5月16日,我与陈卓先生再访博、蠡,承文林兄全程招待,辛苦奔波。到蠡县后,并邀请蠡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第二部《蠡县志》责任编辑张立伟先生作陪。张先生和文林兄一样熟知当地文献,更难得的是,他就是刘村人。因此,在他的指点下,我得以亲睹颜元的出生地——那里现在已无房舍,夹在两户人家中间,只余几株绿槐。这类信息,若非当地饱学之士明告,是无法知晓的。自“路程本”上得来,不如亲自行过。习斋诚不我欺。
本书部分章节曾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系列讨论会上提出,并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演讲。2020年,复经清华大学“中国近世文化史专题研究”课程班讨论。参与这些会议、讲座和课程的学友皆曾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唯因人数太多,不能一一列出。我只想特别提到其中一位,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袁天赐,他的课堂发言表现出的学术积累和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5月底最后一次在线课程,他告诉我自己正在住院,遵医嘱要尽早休息,但又不愿错过课程。为此,我安排他在那节课上第一个发言,九点半(那门课排在晚上)就让他下线。当时我全未曾料到,就此竟成永诀!一个月后,忽知他身罹癌症;又过一个月,他竟遽而去世。他交来的课程报告还放在我的案头,而人已去往另一个世界。天妒英才,运命乖戾,令人结舌!我只能祝他在那边安宁快乐,继续他喜欢的读书、思考生活。
书中三章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感谢孔令琴老师、黄兴涛教授和应星教授为此所做的工作。陈卓兄在读过心理史学那章后,鼓励我继续写下后边两章,才有了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清为本书的编辑投注了大量精力;刘静涵手绘了一幅清初冀中地图,以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颜元主要活动的空间状况。
以上诸位都是本书的接生士,我心存感念,一并表示谢意!
2021年5月18日
又记:
经与陈卓兄商定,本书增入一篇“主题索引”。中文书一向不重索引,学者利用不便。在中国学术正逐步走向世界之时,这一点,还是应该向西人学习。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有时凭借索引,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学界是一共同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编制索引是一份辛苦乏味的工作,必须手工操作,仅凭电脑检索,可能出现离奇的错误,比如物理学、地理学、生理学都被归入“理学”之目,等等。但手工劳作,同样有疏误的可能。这一点,恳请同仁谅解。
2021年7月2日
附记: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一大早传来消息:余英时先生已于四天前遽归道山。乍闻噩耗,一时无言。我是被余先生的著作喂养长大的。初读其著述,算来已是三十年前。大三开学返校,火车抵达成都正值夜半,赶到学校时,宿舍还大门紧闭,刚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又清凉又悲伤的气息。无奈何,我走到食堂外的台阶上,借着路灯打开了《士与中国文化》。
没有想到,那次平平常常的阅读成为我此后人生的起点。今日看来,《士与中国文化》重新界定了中国知识人的认同,让我们在历经半世动荡与漂泊之后,还能有根可依,知所趋向。在这四十年来出版的著作中,至少对我个人来说,仅此一部,无可替代。
我在无言中,打开余先生的书,恰好翻到《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这也是十多年前读过的。这次重读,忽然想到,颜元对时事的“沉默”,恐怕不只是因为我在《导言》中提到的那些理由。他曾在五十五岁时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此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观点上虽有详略高下之不同,在精神上实不无相通共贯之处,令我们想及那一时期的“政治生态”有可能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自然,阳明转向“觉民行道”,是因悟及“得君行道”之路受阻,这和颜元的思路有天壤之别,我这里没有将之混同的意思。我想指出的是,余先生拈出“觉民行道”四字,不但涉及儒学思想史上一个大事件,且对今日之学者尤具非凡之启发。
余先生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儒家相信人人可以成圣,那与外在的职业、地位无关。哪怕一个端茶童子,能够尽到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有益于人,也可以说是圣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也让我想起颜元的话:即使不能做到整体的“圣人”,只能得圣人之“一端”,亦是“得尺是尺,得寸是寸。”圣人毕竟“是我做得”的。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曾借托马斯・曼的一句语式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里面那个“我”字,便可指任意一个人。此外,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又全因每一个自居为“中国人”的“我”身上所焕发的那种“文章光华礼仪”。我们无法把自己归入“狼”族,化作禽兽。
谢谢陈卓兄,邀请我在本书马上要送入印刷厂前,匆匆添上几句话,用来向余先生表达一个晚辈读书人的敬意。
2021年8月5日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天健文史社 2021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