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每位学者都有着不同的求学与治学经历,不论是对学者自身,还是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后进,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请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
你说得很对。正如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学者的学术经历不可能完全一样。不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世界上也很难找到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不同学者的学术经历,尤其是治学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共性。否则,学者之间无法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说起来非常偶然。上大学之前,我从未想过吃历史研究这碗饭。但这种偶然,恐怕不是什么个例。1981年我参加高考,分数居全县文科前几名,其中地理分数是最高的。当时老师似乎没有给予报考学校和专业的建议,我报了经济系和法律系,至于为什么报这两个专业,我也不知道,模模糊糊地觉得国家可能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经历过生活的贫困,总想着未来能有一个实用的去处。有些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回忆说,只有高才生才会录取到文史哲专业,也许我年少无知,对历史系没什么光荣的感觉。然而,命运捉弄人,我被糊里糊涂地录取到河北大学历史系。尽管怅然若失,但还是高兴的,那个年代,能考上中专都是值得家里庆贺的事情,何况是大学,而且是在河北省还算很不错的综合性大学。对大学史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曾提到河北大学是历史悠久的好大学。这就是我走上历史学道路的起点,没有特别的期盼和兴奋。
说老实话,我不仅对历史学没有预定的志向,对其他专业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总之没有什么目标。现在想来,一个年仅16岁、没见过世面、读书“童子功”极弱的懵懂少年,哪来的什么成熟的目标!对于那些一开始就对所选专业有浓厚兴趣的人,我是特别羡慕的,有的有家学渊源,有的天赋异禀,有的受名家指点,人家才是真正走对了路。不过,我也发现有的人讲得太过,甚至令人难以相信。我常参加历史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面试,不少学生在自我介绍时都会谈到“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受祖父母的影响、受父母的影响、受老师的影响、受一本书的影响,等等。不能否认,这里面一定有人真的对历史感兴趣,甚至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但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更不相信那么早就确立了人生的目标。也许有的学生认为不如此,就不会得到面试老师的认可,这显然是一种自觉合理的想象。在我看来,说真话才是历史学者的起码要求。
我讲以上这番话,无非是想表明,无论以何种情况、以何种理由进入历史专业,都毋庸妄自菲薄。原生兴趣和未来志业能够很好地结合,固然值得赞赏;没有原生兴趣,后来经过学习,逐渐生发兴趣,并对此追求一生,同样令人钦佩;即便从事其他行业,也无可遗憾,更没什么可指责的。历史专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除了专业的教学科研人才之外,恰恰是因为人才培养和就业的多元化。
我从未梦想过做历史研究,结果却一辈子注定做历史研究。我的个性是: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尽力。与专业老师接触多了,读历史书多了,也就慢慢有了兴趣,所谓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并完成博士后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历史专业,从事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有30多年了,如果没有一些兴趣,没有发觉自己有一些能力,是不可能支撑下来的。总之,进入历史研究这个领域,始于糊涂,逐渐清晰,探索历史的冲动愈益强烈。看来,最关键的,不在于开始是否想过做历史研究,而是进门之后是否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进取精神。
问:每个人的学术成长道路,都离不开老师的培养。您对求学之路上帮助和影响过您的老一辈学者、特别是老师,有什么想说的话?
在学者的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对历史学习和研究能够产生兴趣,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也必须感谢老一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师恩难忘!其实,不仅是老一辈,同辈、同学乃至更晚的同行也对我有过帮助,我一直都是铭记在心的。
1981—1985年本科阶段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不少老先生还授课,他们出身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名校,也有留学英国、美国的博士,开设了中国图书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外交通史、世界宗教史、拉丁美洲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法国大革命史等专题课。漆侠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等对历史系学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合大学老师的风采和中国古代经济有两个“马鞍型”的特征,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校外著名学者荣孟源、丁守和、胡如雷等也去河北大学演讲,胡先生的名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是我翻烂了的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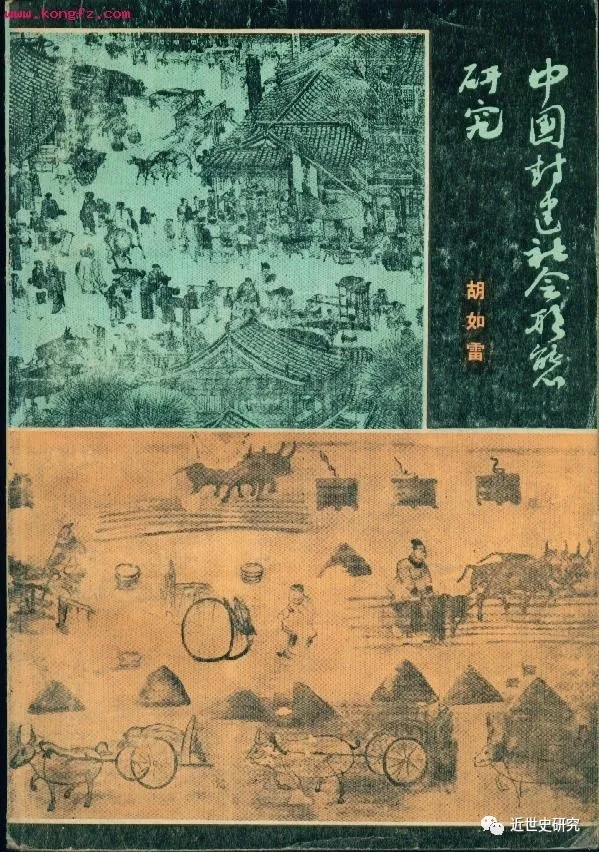
魏光奇先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辅导老师。他是乔志强先生的弟子,思维活跃,常有独到见解。我的论文《近代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与延续》,因和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家庭手工业的解体乃至崩溃了的观点不同,得到魏老师的赞赏。他认为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说我有前途。其实,一篇本科论文的水平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但他的充分肯定,激发了我研究历史的信心。
1985—1988年硕士阶段,我没有离开河北大学,从傅尚文先生继续学习。傅先生出身于山东聊城望族,深受傅斯年的影响。上大学时,与老师张东荪交往甚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先生参与创办了第一家历史学刊物——《历史教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读本科时,我选修过傅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课;读研究生期间,他开列书单,我系统阅读了几乎所有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名著,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共陕甘宁边区、华北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参加了他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讲义”“中国近代工商业家传略”等项目,随他走访了北京多位著名学者。除了历史系的黎任凯、魏光奇先生,傅先生还请经济系的张云岭、张俊、高重生先生开设资本论、统计学等课程,给了我不少经济学知识。我的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得以初步确立。
1996—1999年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导师为魏宏运先生。魏先生是参加过革命的红色学者,中国现代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改革开放后,他走访欧美、日本、韩国、澳洲等多个国家,深入了解国际史学前沿,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和太行山农村调查”,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资料编纂和研究,引介国外著名学者来南开大学做讲座,使南开大学成为华北乡村史、抗日根据地史的重镇。我躬逢其盛,参与太行山农村调查和研究,阅读了大量华北抗日根据地未刊资料,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创新思维更加强烈。
1999—2001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导师为姜义华先生。名义上博士后已脱离学生身份,但实际上当时各界将其视为一个高于博士的求学阶段,比考博士的竞争还激烈。姜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农民史、史学理论等方面均有重大成就,学术格局宏阔,思想见解深刻,每每给我以刺激和启发。复旦大学对博士后报告的要求丝毫不减于博士论文,流动站的邹逸麟、金重远、张广智、樊树志、葛剑雄、周振鹤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吴景平、戴鞍钢先生都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在复旦大学两年多的学习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更多新的理解,甚至有脱胎换骨之感。
在求学之路上,我还要特别感谢李文治、从翰香、吴承明、汪敬虞、董志凯等先生。他们都是人格高尚的前辈。我撰写硕士论文时,论文题目和提纲的确定曾得到李文治、汪敬虞、从翰香先生的亲切指导。李文治、从翰香先生不仅对论文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在我研究生毕业后,耄耋之年的文治老先生还不时地寄送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写信提醒我不要为下海浪潮所动,知识分子的待遇必将有提高的一天,更指导我的研究区域当由冀中而河北,由河北而华北,由华北而南方,持之以恒,必有所成。我撰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时,曾就选题和具体问题向吴承明先生请教,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和解答。董志凯先生为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还帮我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只有1个名额的博士后。经过努力,成功录取,通知都发了,但因原工作单位不放档案而作罢。以上各位老师的无私关怀,对我的为人处世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是必须与人为善,必须善待学生。
问:您最先将中国近代乡村史,尤其是乡村社会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而且持续至今。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后来又是如何持续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问到了根上。我所理解的初衷,应该指最初进入研究时的想法,而不是后来逐渐发展乃至成熟的想法,更不是事后系统总结的结果。我这里谈初衷,虽然也是事后,但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
前面说过,我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都是以乡村社会经济史为选题的。而本科论文,既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我进入乡村史研究的起点,所谓初衷应从这里谈起。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其实并无太过复杂的思考。当时毕业论文的写作和辅导模式,是学生提交论文选题,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选出相应的论文进行指导。说老实话,在本科阶段我还算比较用功的,读了不少中国断代史、专题史和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的著作,但对学界动态、学术前沿并无一个总体把握,几乎不可能完全从学术史的梳理中选出有价值的题目。对我选题有直接推动作用的有两点:一是选课。后来成为我硕导的傅先生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选修课,他对我青睐有加,期末考试分数给了最高分,又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也正是基于此,我决定选择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的题目。二是个人经历。我生于河北农村,既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学生身份的农民。在集体化时期,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我都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一天能拿到最低的2个工分,也曾经参与队里夜间的粮食私分;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还为家里拾柴、拔草、割野菜。那个年代,大多有吃穿匮乏的痛苦经历,也成为一辈子难以抹去的记忆。1980年前后我上高中时,家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饱问题很快解决。前后对比,让我格外关注农村的变迁,毫不犹豫地以乡村经济史作为论文选题的对象。除此之外,也和阅读相关的论著、资料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中关于家庭手工业的描述,一般都是在洋货的冲击下解体、崩溃了,但我阅读彭泽益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时发现,家庭手工业尽管受到冲击,但直到1949年仍是存在的,这就和流行说法产生了矛盾。于是,我想通过毕业论文对此做出解释。显然,这个选题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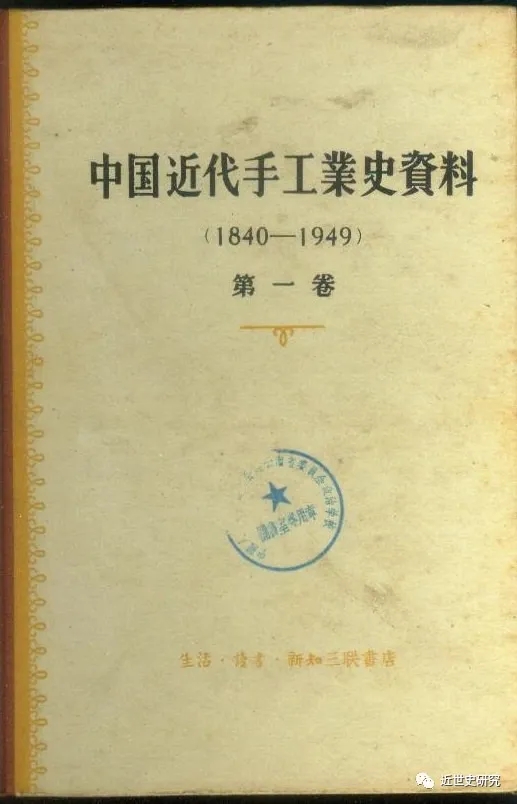
万事开头难。本科论文选题虽无学术史梳理的自觉,但结果是比较成功的,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后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报告阶段,我对乡村史的认识大大提升,研究方法也有明显的改进。我愈益坚信,中国向为农民大国、农业大国,不研究农村是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近代乡村史既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传统与现代互相交织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之高是不用多说的。我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看到,老一辈学者认为目录索引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为此我自学了文献检索、目录学之类的书。我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华北乡村)、华北根据地史等领域整理出详细的论著资料目录索引,并分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大阶段。而且,对每年的最新成果,不断追踪、补充。由此,不仅了解了学界动态,还可结合平时对论著资料的阅读,发现可能具有价值的选题。如此越积越多,基本保证了优化选择,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偶然性,增加了必然性和自信心。所谓仓中有粮、心里不慌,学术问题的累积也当如此吧。但在当今数据库的应用十分广泛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否仍然值得提倡,就不一定了。
硕士论文,傅先生建议我以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为选题。这是可做的题目,当时国内外对乡村改良派及其实验的关注不多,教科书中的简单介绍仍多持否定意见,但以我对乡村史的了解,觉得不如先对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进行实证研究,否则无法对定县实验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傅先生是一个非常民主的老师,他很赞成我的想法。我的硕士论文《近代冀中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之研究》,运用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对自耕农的优势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得到答辩专家李文治、从翰香先生的高度评价。
博士论文,魏先生没有给过具体建议,但要求找到一个既有价值、他人研究又较少的题目。我从已积累的问题中,确定以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借贷关系为选题。尽管一般认为,借贷是一个较为狭窄的课题,其实借贷农户所占比例比大家熟知的租佃、雇佣比例要大。我的博士论文《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研究》,对传统借贷、新式借贷和革命借贷都提出了新的观点,获得答辩专家李文海、丁守和先生的高度赞扬。
博士后报告,姜先生也让我自己决定选题。前面谈到过,李文治先生曾对我讲过,我在研究华北之后,可以涉足南方。既然到了复旦大学,我就试图抓住机会,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继续研究乡村借贷关系,并与华北乡村进行比较,这一想法得到了姜先生的认可。我的出站报告《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对传统借贷和新式借贷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得到流动站各位老师的高度肯定。
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出版后,学界认为我是中国近代乡村借贷研究的集大成者,这当然是过誉之论了。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还涉猎过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国民政府金融、军事教育、城市史等。尤其是革命史,用力还较多,我提出的“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产生了强烈反响。不过,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乡村社会经济史的探索。我以为,一旦方向明确,保持定力、专注对于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一种比聪明才智还重要的素养,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任何人的时间、精力、才力都是有限的,四处出击、贪多求全,只能蜻蜓点水,是难期深入的。有人批判专家太多、通才太少、大师几无,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专家的出现恰恰是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批判者自己哪一个不是专家呢!就以历史而言,“通”中国近现代史都很难,何况中国通史、外国通史,更何况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至于众多的自然科学门类就更无从谈起了。通与专的关系,我是从两个角度理解的:一是由博返约。读书尽可能广泛涉猎,追求知识、技艺的广博和理论、视野的广阔,但研究范围须集中于适合个人能力的范围,广博是为返约服务的。成为通晓多个领域的大家固然可喜可贺,在一个领域做出贡献也属不易,同样值得肯定。二是由约返博。通过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为更大的学科问题、领域问题乃至宏大的法则、规律性问题提供解释。其实,从终极目标来说,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是同样的问题,各个学科都是基于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增加理解人类社会的维度。一个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能否傲然于学术之林,这是最有力量的判准。
问:在乡村史领域,相比较来说,您对定县的研究时间最长,发表过多篇优秀论文。为什么会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定县对于近代华北乃至中国乡村史研究有何特殊意义?
这个问题关乎我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
硕士毕业论文《近代冀中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之研究》,尽管篇幅达十几万字,答辩专家也给了很高的评价,但与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相比,远谈不上成熟,不可能很快出版。我至今还在进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有时我甚至觉得,硕士论文俨然成了我研究乡村史的主旋律,而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倒显得像插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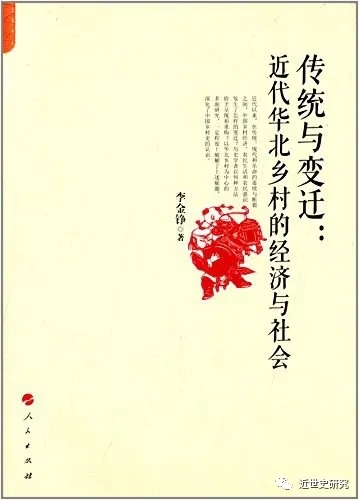
为什么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呢?简单地说,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不是某项专题,而是广及人口、家庭、土地关系、农业经营、家庭手工业、集市贸易、民间借贷、农民负担、农家消费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在我看来,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两个类型,都有其合理性,但实践证明,后者更有延展性、辐射性,更具生命力。
硕士论文所涉范围如此广阔,是不可能特别深入的。毕业后,我越发觉得原来的研究多属微观的、区域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宏大的社会经济史关怀,缺乏与学界同行的充分对话和论辩,缺乏个人洞见。尽管不能说一点意识也没有,但大多是模糊的、薄弱的。为了弥补以上缺陷,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研究目标:一是对近代冀中定县乡村经济的结构、运作形态及其变迁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农民生存之所系和区域的特性;二是将之置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脉络之中,寻求冀中乃至华北平原区域的特殊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共性,并讨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为深化乡村史、乡村经济史的认识提供一得之见。
我不是定县人,不像地方史学者有为地方“人杰地灵”进行辩护的责任,在我看来定县是研究近代华北乃至中国乡村史的一个载体,研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从学术角度探究真相,发现法则。按照这一逻辑,不仅仅是定县,其他县域也是如此,更大的市域、省域或更小的乡域、镇域、村域同样可作如是观。区域的选择,当然以具有内在联系紧密的社会经济区域为宜,但也无须画地为牢,任何区域都是有价值的,关键是能不能挖掘出它的普遍意义。就此而论,定县对于近代华北乃至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更具一般意义,而无特殊意义。
在以上思路之下,我在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出版或者说进入21世纪之后,抽出很大的精力用于定县的再研究。我不仅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乡村史成果,也尽力拓展资料,更是学习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我陆续整理出15篇论文,已发表14篇,包括《历史研究》2篇、《近代史研究》4篇、《社会学研究》2篇、《中国经济史研究》2篇、《二十一世纪》1篇、《河北学刊》1篇、《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篇,《现代中国变动与东亚新格局》论文集收录1篇。还有1篇没有发表,参加了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期刊发表并不意味着全部,但从一篇硕士论文衍生出以上成果,我的确是有一些成就感的。
通过定县的研究,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在家庭结构、性别比例、人地比例、土地分配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农业生产、手工业经营、集市贸易、农民借贷、赋税负担、农家生活以及乡村建设实验、农村社会调查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近代乡村变迁的认识。当然,这些看法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仍需得到学界的进一步检验。我觉得,现在快到结集出版的时候了。
问:近些年,您发表了多篇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如2020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讨论费孝通城乡关系论的文章。请您谈谈这个方面的想法。
因费孝通本人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权威地位,这篇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城乡关系论的文章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学界,在社会学界也有一些反响。
近五六年来,我对乡村史的研究稍有一些转向,开始关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尤其是乡村经济思想,陆续发表了六七篇论文。如2013年在《江海学刊》发表的《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2014年《近代史研究》的《“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2015年《江海学刊》的《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2016年《近代史研究》的《“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2017年《人文杂志》的《近代中国耕地“红线”之争》、《近代史研究》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等。
以前我主要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什么会发生思想史这个转向呢?其实,并不是我对思想史不感兴趣,而是不敢轻易涉猎这个领域。我早就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应该先对历史上的社会实际进行研究,才有条件、有底气探究思想史。否则,思想言说究竟是符合历史实际还是超前或滞后于历史实际,依据什么来判断呢?我做硕士论文时,没有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入手,而是先对定县的社会经济实际进行研究,就出自类似的理由。我给研究生上课,在谈到如何选择主攻方向和研究领域时,也强调初学者不宜做思想史,应先从社会实际的研究做起。后来看到大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一段话,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他说他一生治学的“保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何先生是何等资质的大师,他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应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然,万事不可一刀切,如果有人确有既通晓历史实际又敏于思想雄辩之才,一开始就进入思想史也是顺理成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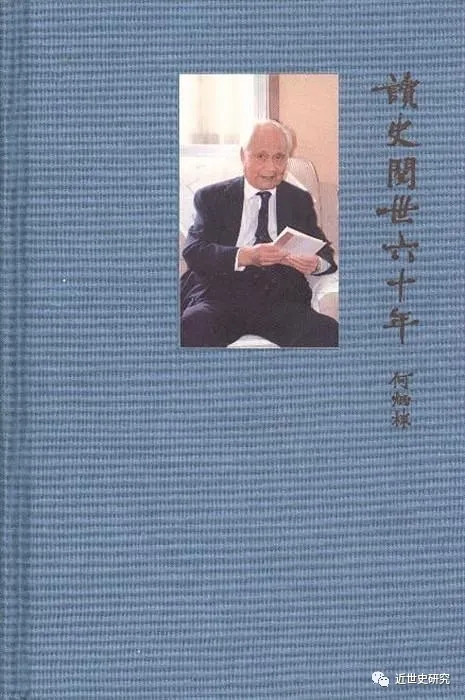
我自觉对乡村社会经济史已有较多的研究基础,才开始涉足经济思想史。我计划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研究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中西的碰撞愈益激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愈益复杂,社会各界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的乡村经济问题乃至如何改变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影响较大的有: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或称“分配派”),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以《中国经济》杂志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派”,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派”,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都市派”等。不仅要研究各派的经济思想,还要对各派进行比较,发现异同。二是从乡村社会经济现象或者从社会经济的问题、结构和运作形态的角度进行研究。譬如人地比例关系、土地分配关系、农业经营规模、生产工具现代化、主佃关系与雇佣关系、家庭手工业前途、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关系、商品化与农家经济及农民生活的关系、赋税改革、农民贫困的原因等等,都值得从思想史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上研究不一定对当今中国特别是乡村发展有直接作用,但作为源流和参照还是有意义的。
与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相比,经济思想史研究似乎是稍逊一筹的。大多论著仍限于知识精英、政治领袖的文本整理和简单分类,缺乏思想与历史的互动,鲜有历史语境的分析。我希望经济史学者参与进来,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
问:结合您多年的从教经验,您认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对于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您认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就留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已有30余年。我为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过十多门课程,授课本科生难以计数,培养博士、硕士七八十名,其中有7人晋升教授、18人晋升副教授,有的成为博士生导师。学生有出息,是老师最大的欣慰、最大的荣光。
你问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有何不同特点,我建议看看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的一篇文章《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里面对此有过精彩的解释,大致的意思是: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但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一旦进入研究生阶段,就不只是完全乐在其中,更要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从而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王汎森先生讲得非常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对于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及其方式,很有针对性。当然,他说“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我并不完全赞同。大学生的确处于打基础的学习阶段,但不能说就是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也需要提高思维能力,需要培育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制造知识。我甚至认为,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生,也应该加强这方面意识的培养。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

在王汎森先生所讲的基础上,我也想贡献一点自己的理解。我以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都应该以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和创新知识为目标。但因层次不同,又有差别。本科生的目标是,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初步具备利用专业知识和理论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硕士生的目标,能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和理论独立地解决较为重要的问题,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多或少解决了前人所不曾解决的知识和理论问题;博士生阶段,则应具备独立地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成果须具有“原创性”,解决了前人不曾解决的重大知识和理论问题。当然,以上都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须心向往之。
老师的职责,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实现以上目标而努力。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能否做出优秀的论文,内因固然起主要作用,但对老师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教学和指导效果的试金石。遇到可造之才,实在是老师的幸运。
对于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我还想强调几点:一是培育自主意识。凡属成功的学者,一定不是完全仰仗老师,而是独立自主、努力奋斗的结果。导师的作用主要是点拨、启发,而不是保姆式的代替。二是精读经典名作。无论是历史学专业还是相关学科,经典名作都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读一本胜过读百本、千本,不可将有限的时间、精力耗费于平庸之作。凡属经典名作,都不会像通俗读物那样易读,要敢于啃硬骨头。三是注重理论方法的学习和运用。理论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必备工具,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挖掘史料、取舍史料、解读史料,都须臾不可或缺。面对同样的史料,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理论水平,尤其是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弥补,历史学者少有理论发明,借鉴相关学科势为常态。四是不断积累有价值的课题。学术研究最难的一步是提出问题,要从学术史反思中、从论著资料阅读中、从现实关怀中,发现矛盾点和突破点。问题积累越多,越有优化选择的可能性。五是培养严谨的规范意识和独到的创新意识。学术研究是有门槛的,门槛就是规范,规范意识就是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包括最低要求的技术规范。创新意识本属学术规范的核心指向,但因极为重要而被单独提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资料挖掘、方法视角,以及观点阐发,都要在尊重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劳动。那种所谓“以往缺乏系统的、专门的研究”的模糊表述,既是对以往成果的不尊重,也非有的放矢的“批判”,不可能得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以上几点,其实已是常识,本无须我在这里啰唆的。所谓强调,不仅是要求学生,对泡在历史里面数十年的我,大多也是适用的。
感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