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华北村治》(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6-1936),《乡村中国纪事》(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重构近代中国》(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00-1950,中文版待出)。
本文为访谈整理。
从国内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在美国高校任教,做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在估计不下于五六十人。这里有一个学术团体,叫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US)。现在也在吸收美国本土研究汉学的白人,也吸收了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会员大约一百多人。但其中,真正从国内出来在美国留学,并且在美国高校教历史的,我估计就那么五六十位。就整个美国而论,假如有5000所正规高校的话,吃中国历史这碗饭的,估计不下于1000,东亚史更多,可能达到2000人,因为美国有好多二流、三流学校,人太多了。CHUS会员当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都不是历史的科班出生。有些在国内是英语专业,或者是英美文学专业,到了美国后,发现在美国继续搞英美文学,缺少本土优势,于是改学了中国历史,这是一拨人。当然也有人改学中国文学或别的学科。还有一拨人,确实是学历史的,但是原来在国内学世界史专业,他们认为学了世界史更容易出国。80年代到90年代那会有出国热,和现在大家比较看淡出国不一样,当时年轻人很向往去国外。事实上,确实很多学世界史的出国了,但是到了国外后发现,其实美国的大学历史系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专业,美国只有国别史,比如美国史、法国史、中国史等,再往上是西方文明、非洲史、拉美史、东亚史等等。即使有世界史这门课,也是围绕殖民帝国、跨大西洋贸易、丝绸之路、全球化之类的内容,也就是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跟国内的世界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国内学了世界史到了美国也不管用,有些人改行学美国史,有极少数是非常成功的,更多的是改学中国史。还有一批人,不管当初是美国史还是世界史,到美国之后专攻中美外交史,但是最后落实到工作,都投向了中国历史这个教职。所以,真正科班出身,也就是从本科开始就专攻历史,然后一路到今天,没有改变初衷的,其实并没多少。

李怀印
1
从苏州到北京
我是从1980年开始在苏州大学读历史本科专业的。当年秋季入学,是所谓“80年代新一辈”,就是说80年以后,整个校园气氛就不一样了。80年以前,校园基本上还是属于“老三届”,比我们大好几岁,大一二十岁的也有,都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很多年,然后又入学的,社会经验丰富。但从80年以后,都是高考毕业后进入大学的,面孔都是全新的。我上大学时是15周岁,班上还有比我更小的。
苏州大学是我学习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后来为什么会走向历史研究这条路,现在回想起来,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已经把方向定下来。当时我的老师有董蔡时、段本洛。董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史,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黄宗智先生的夫人白凯,Kathryn Bernhardt,曾经赶到苏州跟他研习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史。段本洛也研究太平天国,但更多研究经济史。这两位老先生当时给我们开设专业课。董先生的课程名字叫《太平天国史》,段本洛开设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我们当时不仅要求要选这些课,而且要求写毕业论文。本科生毕业写毕业论文,美国没有这种做法。美国的大学里往往有Honors Program,甚至还有Honors College,我们UT有Plan II,都是针对优秀本科生的。他们毕业前要求要写honors thesis。我当时跟着董蔡时先生做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写完后,董先生大为赞赏。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也很受他的影响,他曾写了一本《左宗棠传》。我为了写这篇论文,专门到苏州大学的红楼图书馆,里面有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特别是里面的奏稿、文牍啊,我都梳理过了。凡是涉及到经济和洋务的资料,全部都加以搜集整理,然后写成了这篇论文。这个写完之后交给了董先生,老先生写了评语,说是“已具备科研能力”。然后他推荐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学历史》上。这份刊物当时是国内公开发行的。发表文章对我算是一个小小的激励。快毕业时,要开一个全系的师生会议,在小礼堂里,大约是有一两百人。1984年本科毕业论文奖就给了我,很意外,还发了一个奖品,是《现代汉语词典》,我还在用,在家里存放着。现在已经又旧又烂,但舍不得丢。
话说回来,虽然已经是80年代,当时大学里用的教材,有些还是文革时期编的。特别是世界史教材,叫《简明世界史》,前面的序言里还说,这套教材是工农兵学员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合编,这些都是文革的遗风在里头,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教材。中国古代史的教材已经变了,去掉了文革的痕迹。《中国近代史》,我记得是李侃编的,多多少少还有文革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那一代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用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比如董先生,他研究太平天国,一直在强调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太平天国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也是一家之言。他这个人是真心觉得要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历史的。
不过,80年代已经有所谓思想启蒙,有“启蒙史学”在挑战以前的阶级斗争史学。大凡做学生的总有求新的想法,所以老先生讲的我们兴趣不大,但是作为老师,我很尊重他们。包括董老师后来研究左宗棠,替左宗棠讲话,但对左宗棠的定位还是地主阶级当中的开明派,也能自圆其说。但是他本人很开明,他的学生不论写什么,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他都是鼓励的。董先生起初想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自己也有这个打算,但是后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在招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就开始准备考试。过年了,人家都回去了,我们毕业班,大约五六个人,都不回去。因为当时考研究生是过了春节的大约二三月份的时候。一旦春节回去,整个一个月就浪费了。所以大家春节都在学校过,系主任在除夕夜还请我们吃饭,收看CCTV 的84年首届春晚。结果考上了,去北京近代史所读书,我的导师是樊百川,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
到北京跟樊先生学习,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十分执着,他很不苟同于那些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那些人是搞政治的,他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49年后,范文澜和刘大年执掌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还算学者,刘大年则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在我导师看来,他们把历史搞得政治化了。但是我的导师做历史研究要用那种地地道道的、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做他的研究生,初次见面之后就给布置任务,要读《资本论》,读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每一次见面都要谈这一周读马列的心得体会。他平时不回家,床就安置在研究室里面,吃住都在近代史研究所,周末的时候是否回家一趟,我也不太清楚。他有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要把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逐一写本专著,所以夜以继日地在做。他的近代史研究,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所有近代史研究方面做得最扎实的,应该讲扎实的程度超过了本所和经济所的同行,比如说吴承明、汪敬虞、彭泽益等等,也都是顶尖的经济史学者。你只要翻一翻他的几本书,就会明白这些话并未过头。但是这个人很低调,他不张扬,也不到外头去参加开会活动,所以外头知道他的不多。真正知道他的人,对他都非常尊敬。
我当时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张謇。他是民族资本家中最成功的一位,搞了一个企业集团,有十几个厂。我导师说,你就去研究这个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研究,看他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决定他的政治态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张謇跟当时的中国政府,跟两江总督,有很多的私人关系。所以,他是新派的资本家,但是又有很多的封建色彩。这两个背景对于他后来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对于他政治上有什么影响,让我去研究。我到南通查了各个方面的档案,把他的大生纱厂、南濠别业等等地方走了个透。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点趣味都没有,很无聊。我当时是想这么研究:我说这个张謇,他是一个状元(其实还是我的半个老乡,他在我们那里办了个“母里师范学校”。三十年前跟家乡的老人谈起张謇,都还知道有个张四先生),受到儒家传统的训练,他整个的价值观都是儒家的。但是他办厂,又是在搞现代化,所以我的思路,是想看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伦理之间有什么样的衔接。但是樊先生坚决否定,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研究,那笃定毕业不了。所以,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去写,写是写好了,他个人也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一点也不乐意,而且我从此再也不愿去碰张謇。(不过)后来为了开会,还是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儒家传统与张謇的一生》,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2
南京的六年光阴
毕业后去了南京。近代史所要留人,可是我对留北京一点都不感兴趣。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总体上还是要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民国这段时期。研究民国,它的史料都集中在南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区域,最发达的还是在江浙一带。那我待在北京干嘛,要去南京。我老家在江苏。回家乡的话,会活得更滋润些。
在南京待了六年,单位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边上就是南京艺术学院和优美的古林公园,多好的地方。日子过得如鱼得水,物质上很一般,都跟大家一样,但精神上非常愉快。那六年,除了成家,基本上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做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其实这个课题,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我的导师做学问在方法上十分正统,我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但写硕士论文还得听他的。硕士论文之外,自己一直在琢磨干些别的事情,那时最感兴趣的是在美国已经做得很多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应该讲,到了8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不过,当时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化,在美国也还有人在做。有一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收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里头,在国内影响比较大,但在美国几乎没有学术市场,书名是《中国现代化》,主编是Gilbert Rozman,这本书在美国大约1981年出版,红面子的,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从头到尾看过,算国内最早看完英文版的读者之一吧。
顺便一说,我当时做研究生,看英文不是问题。我们苏州大学原来叫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原来是美国的教会大学。当时大学里有开设专业英语的老师,叫张梦白。这位张梦白先生是49年前老东吴的教授,去世之前还是东吴校友总会的会长。他是仅存的旧东吴的教授,给我们开专业英语和美国史专业课。要求我们学英文都必须要背诵。我在本科的时候背诵了二十来份英文演讲,每天一早赶到树林里大声朗读背诵,天天如此。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入学时,先有分班考试,我的英语课直接就免修了。
除了《中国现代化》之外,还有一本书,叫《在中国发现历史》,是柯文写的,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作者送给所里丁名楠老师一本,我有幸读完了。我后来在《重构近代中国》这本书里提到柯文的书,柯文本人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给我写书评。所以有一次AAS(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组织讨论柯文那本书出版30年来在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我受邀专门谈了这个题目。(最近柯文出了本回忆录,A Path Twice Traveled,也提到这件事。)他这本书把在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个情况做了一个综述。当时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一下子就被美国的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吸引住了。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国内学了那么多年,一直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但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而且现代化历史后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很长,简单的说就是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然后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是把韦伯的理论发扬光大,之后普林斯顿大学等地方有一批人在研究现代化理论,其中有一个人叫Marion Levy, Jr. ,他研究现代化也是权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作者之一。Levy有一次来江苏社科院学术交流,我当时是助理研究员,当时有七八个人参加,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跟他对话。他懂点中文,学过繁体字,但他是社会学家,解放之前来过中国。
由于看过这些英文书籍,了解到国外的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现代化研究状况,所以早在1986年,也就是在近代史所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就在国内的《社会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标题是《从对立到渗透——西方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到南京工作后,又跟人合著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在附录里收了这篇文章,把文章标题改了一下,叫《从冲突到交融——国外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包括标题后来被某位教授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袭了,我也懒得去管这个事情。
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当时做研究生的时候,就想跳出我导师的传统治史的路数,所以到了南京之后,就干了一件事,是把国外的现代化研究介绍、引进、翻译、评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另外就是把国外的这种现代化研究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上。到南京后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江海学刊》上,标题叫《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历史透视》,就是用现代化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的政治史。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而是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整个解读都不一样,当时人大(复印资料)也转载了。也参加过北大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他自己编过一本论文集,《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把我的文章放在第二篇,紧随他自己的论文,后来给我来信,说很看重这篇文章。总之,在南京六年时间,发了几十篇论文。最后的成果是合著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整个策划是我做的,但主编请的是院领导胡福明,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那篇文章的作者。那时全国都在批自由化,这本书在全院大会上被点名,据说有自由化倾向在里头,这已经是我出国之后的事了。
3
师从黄宗智先生
1993年到美国做博士研究生,直到2000年,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UCLA,导师是黄宗智。黄宗智先生已经退休十多年。但现在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讲座教授。我跟他做博士生前后六年,从93年到99年。99年的时候,我离开了UCLA,博士论文还没写完,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所以99年就离开了UCLA,到密苏里大学历史系,做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因为博士论文还没写完,要等到2000年博士论文写完,才算正式从UCLA毕业。黄宗智先生,我觉得特别值得多讲几句。他做学问应该讲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块是最出色的学者之一,你不能讲谁最厉害,应该讲有那么四五位学者,都是非常棒的,黄先生应该算是其中一位,而且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头一本书,是写梁启超,写中国思想史,但是他自己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所以后来就转到中国乡村研究这一块。

黄宗智
华北研究过去使用的都是日本人在30年代所做的华北村落调查,在华北好多村落做了调查,我们把它叫做满铁调查。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东北,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面有一个研究部,派了一批人到华北各地做调查,后来出版了几十卷调查报告,每个村落它的人口多少,每个农户的家庭结构、收入,他们日常的社会活动、婚姻、宗教等等,非常详细。这个报告在黄之前有人做过研究,但是只出了一本,那个人叫马若孟,Ramon Myers,是斯坦福大学的,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民经济》。那本书影响力不大,至少它的影响力不如黄宗智的书那么大。黄研究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两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就奠定了;以前他的第一本出版后没什么人理他,自己也不满意。但是这两本书出来之后,他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就得到大家的公认。他还办过一个杂志,叫《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从70年代一直连续出版,到今天还在出,并且从当初的季刊变成现在的双月刊。早已经是国内讲的SSCI Indexed Journal,大家都很看重这份杂志,他是主编、创始人。
黄先生做学问,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或者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提炼能力。黄本人可以归类为美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左翼学者,所谓左翼,就是说比较同情中国的革命,或者对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抱一种比较同情的态度,而不是说像右翼学者对共产党革命也好,对49年以后的中国的状况也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研究中国乡村,如果就研究方法而言,是把几个重要的流派结合在一块。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阶级结构的分析,强调地租剥削,土地所有制,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黄借用了这个方法,这是一块。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更多的我觉得是受到所谓实体主义流派的影响。这里面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就是俄国的恰亚诺夫,A. V. Chayanov,他研究俄国的小农,特别强调小农经济的逻辑,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场主不一样。农场主经营农场,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养那么多牛干嘛,无非就是为了赚钱,为了以最小的成本赚最多的钱,就是所谓的利润最大化,跟资本家办工厂都是一样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但是恰亚诺夫他认为小农种田跟资本家办厂或者是农场主经营农场,想法完全不一样。它并不一定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利润,它不是这样。它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一旦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他的劳动投入就会越来越少,这是农民种田的想法。黄先生对中国乡村的研究,还有一个方法,受“理性小农”理论的影响。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小农是理性的,小农跟资本家的想法,没有两样,也是想多赚钱,也是想以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率的办法来种田。黄的华北那本书,包括他后来研究长江三角洲,在方法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加上俄国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分析,再加上理性小农的概念,把这三个不同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农民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我觉得他做得对。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各有它的合理性,处在不同阶层的农民,想法各不相同,所以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借鉴过来,用来研究中国农民。这也是黄先生做学问最成功的地方。当然他实证研究的功底也很扎实,加上理论分析,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强;他之所以能够在咱们这个领域里面奠定他的地位,我觉得主要就是靠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理论方面的借鉴,第二个就是他的实证研究。后来黄先生又从乡村史转到法律史,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方法上也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到兼顾实践与表达两个侧面,推动建立一个扎根中国实际的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至今笔耕不辍。
4
我的乡村史研究路径
我自己的乡村研究,如果说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一个,就是说除了刚才讲的这三个理论传统之外,更多地还是受到90年代思想界两位巨擘的影响,一个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现在是海内外学人无人不知的一个人物,另外一个就是福柯,也是人人皆知,Michel Foucault,但在90年代初,国内了解的不多,在美国也还是刚刚受重视。这两人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在这些传统的概念之外,把研究视角延伸到以往马克思主义不太重视的方面。比如说Bourdieu,我们传统讲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们从高中到大学,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这一套一套的原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都没错,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人,每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群体,他的想法是很复杂的。你就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这样笼统地讲,实际上就把所有的事情太简单化。
我认为这两位学术巨擘,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的视角从这些传统的概念,延伸到以往我们不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说Bourdieu,他发明了好多的概念。对我自己的研究来说,觉得最有用的一个还是“惯习”,原文叫habitus。把习惯两个字颠倒过来,那就是惯习,不知谁起的头这样翻译的。惯习就比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更加精确,也比社会意识这个概念更加灵活,更能说明问题。你可以去看我研究华北乡村的那本书,中文译名叫《华北村治》,我研究华北农村里的村民,在日常社会生活里面,怎样进行交往,怎样参加群体合作,你怎么去解读他个人的想法?我们以前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是贫农,还是中农或者富农,你的态度就是什么样,其实没那么简单。所以我研究农民的个人行为,对自己的分析、研究来讲,受影响最大,最有帮助的,首推Bourdieu的惯习概念。那另外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非常管用,就是Foucault的“话语”,英文叫discourse。它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概念的拓展,更加精细化,更加丰富,因为话语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个人的社会意识,它是一种大家在公共场合,或者人与人之间交往当中大家的言谈,这种言谈它怎么产生的?它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种言谈是如何折射了个人的社会背景,同时又折射了你所处的社会群体乃至更大的历史背景,大家的社会意识,它是这么一种东西。我研究中国乡村,研究农民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日常行为,觉得话语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的日常言谈、议论,往往决定了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事情做起来大家是认可的,哪些事情做了之后会影响到你个人在群体里面的地位,影响到人家对你的评价。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有自己的话语,乃至于我在那本书里面论说,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甚至每个村落里面它不同的街坊,有自己的话语,你生活在你的话语世界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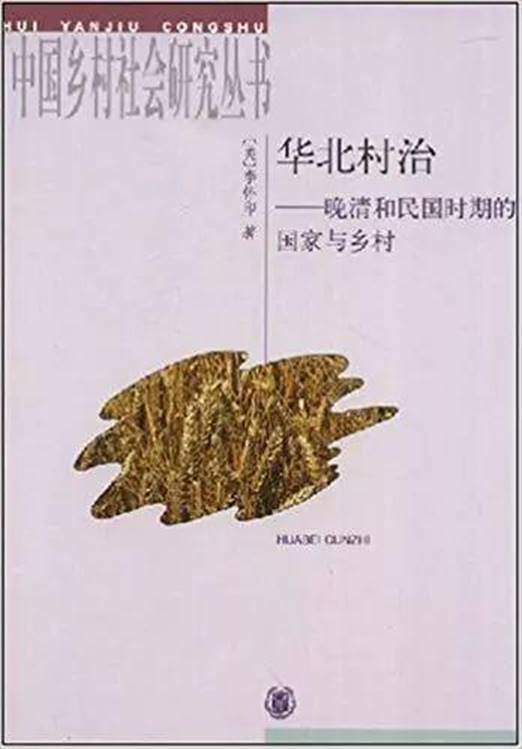
我在UCLA读博时,曾经跟一位教授修德国史,名叫David Sabean,他有本书研究德国的一个村庄,叫Neckarhausen。他就认为德国乡村的农民共同体是由话语打造的,对我影响很大。所以,你在想什么,你想做什么,实际上都要受到整个话语的影响,这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里面没有的,我们光讲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实际上太笼统。管用的倒是Foucault的话语,或者更进一步讲是他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再加上Bourdieu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研究。除了惯习之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场域,field,实际上跟我讲的话语体系、话语空间或者语境十分相近。话语空间可能是一个村落,可能是一个邻里,一个街坊,可能是个更大的范围。所有这些概念,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或背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是大大拓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的维度,难怪那两位法国学者也都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研究的课题本身来讲,黄先生更多地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小农,主要还是研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集体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主要还是从农民的经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农民的政治上面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黄先生的乡村史研究的归结,是要理解乡村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最终为何走向共产党革命。他研究的重心,归根到底是农民的集体行为和革命问题,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相较之下,我的头两本书,关心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农民的日常行为。具体来讲,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其中第一本书《华北村治》,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05年由斯坦福出的,就是研究农民在纳税的时候,或者在参与乡村的日常治理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我的研究利用了河北省(更早叫直隶)获鹿县的诉讼档案。村民经常打官司,为了缴纳田赋要打官司,为了做村长,当时叫村正,也打官司。有些人要做村长,有些人不想做。还有就是你要纳税,你要交税给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叫乡地,他代表同一个村或者同一个街坊的村民去垫交田赋,或者挨家挨户地催人家还垫。这叫乡地。你为什么想做乡地,或者你现在正在做乡地,但是突然不想干了。或者说,你为什么想当村长,或者有时候你不想当村长。到了20世纪初办清末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办学堂,办学堂,课堂放在哪里?学费怎么收?教师怎么请?给教师开多少工资?谁去做学校的校长,当时不叫校长叫学董。有些人想做学董,想尽一切办法要做学董。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纠纷,你怎么去理解这些纠纷?为什么他们有些人想干,有些人不想干,有时候干的好好的,突然中途辞职不干,那你要去理解农民的行为,以往的概念都不管用了。我觉得真正管用的,就是“话语”、“惯习”、“话语空间”、“场域”等等这些概念,有了这些概念,你来理解中国农民的日常行为,好多问题迎刃而解。所以我的研究是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关心的是农民的个人和群体行为,不是革命或集体暴力,而是农民作为一个个人或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日常社会行为。所以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跟过去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我的第二本书还是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乡村,时间跨度从土地改革、集体化、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一直研究到2008年。
5
重新认识集体化和改革时期的中国乡村
2009年我的第二本书出版,书名叫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还是斯坦福大学出的。这本书的重心之一,还是农民的日常行为。比如说集体化之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些人干活非常勤快,认真、负责,另外一些人干活就不认真,懒散、拖拉,这又是一个问题,国内的标准教科书上的那套概念没法加以解释。所以真正有用的,还是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分析,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这个问题,我写过两篇文章也是强调这个问题。应该讲话语分析是贯穿整本书始终的方法之一。但除此之外,我还强调其他一系列的因素,比如地方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土地生产率,当然国家政策也很重要。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对农民来说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它特别强调劳动计酬。农民集体生产劳动,获得报酬的方式是所谓的工分。它在农民的收入里面占多少比例,这会影响他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一个地方自然条件好,土地生产率高,当然农民的收入会高一点,生产积极性也会高一点;干部的管理方式也很重要,干部会不会管理,怎样分派农活,给农民的报酬是否合理等等。但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话语,农民生活在一个地方,他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做得对还是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一项农活,你怎么干才能让大家接受,这也直接关系到人家对你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而话语体系,本身又跟一个地方的农民群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价值认知判断有关系,当然也受到经济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干部管理方式的影响。如果一个干部管理不当,大家都很不满,可能都有一种反叛的心理。如果干部管理得当,那大家做事情都很兢兢业业,是不是这样?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相互制约,构成一个语境。话语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点,也在不停地变化。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要研究49年以后农民的社会行为,你也必须把不同的因素综合起来。这样对农民的研究可能会更加贴近实际,你的判断可能会更加准确一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研究中国农民,尤其在美国,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的理性小农视角。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领导人对一些政策的制定或者对一些问题的判断,也是受理性小农概念的影响。所谓理性小农,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个人,农民追求个人的投入与他的回报之间的合理比例,力求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回报,大家都认为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因为是理性小农,而集体化制度本身,过去都认为它是平均主义的,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谁都不愿意干,劳动效率很低。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终结平均主义,集体制本身被认为是平均主义的根源所在。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集体制,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责任制。田是自己的,你多种粮食,增加收入,都归自己,你就有了生产的动力。我觉得总的来讲没错,理性小农概念,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干巴巴的去简单化地描述农民的个人行为,好多问题无法深入理解,或者说我们的理解不会贴近当时的农业集体制的实际,也不能准确地解读农民的日常行为。所以我的第二本书主要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撇开以往的理性小农的简单化认识,把农民摆放在一个历史的场景里面,将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考虑进来,形成一个更加丰满,更加贴近历史实际的解读。这是我第二本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二本书出来之后,美国很多高校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课程把它当做教材。国内反应也还不错,这本书的中文版是法律出版社出的,中文书名叫《乡村中国纪事》,副标题是“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我们现在讲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我看有些文章里面还在引用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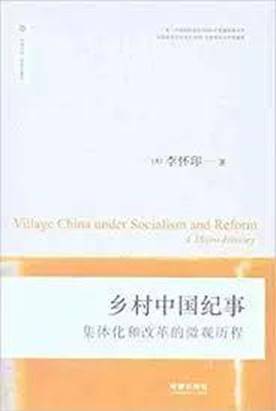
6
关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
我的第三本书,Reinventing Modern China,是写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更具体的讲就是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中国的史学家怎样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当初也没有一个计划说要写这么一本书,本来的计划是要写一本中国近现代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现代变革。当时我在构思这个题目的时候,最关心的是怎么去理解现代中国的变革,中国从19世纪初那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到21世纪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社会,一百多年中国的近代转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前我们理解这个变革过程都是用一个概念叫近代化,有些人用现代化,这些概念我觉得都成问题,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宏大的过程。所以我写完两本中国乡村之后,构思底下的研究计划时,心里想的是这么一个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根本转型。要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着眼点,应该先去看一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这个历程,那我就要去了解国内的史家是怎么写中国近现代史的。
下手之处是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是共产党的史学家。除了范文澜,还有张闻天、李平心这些人。还要看国民党的史学家是怎么写中国近现代史,那就要去看蒋廷黻、陈恭禄。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中国的一百多年来的历程做了不同的解读。共产党这一块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而蒋廷黻、陈恭禄,他们是从近代化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把他们这些人的研究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一写,我觉得要把这些问题讲透的话,那不是两篇文章能够做到的,后来索性就把这个课题加以扩展。除了蒋廷黻、范文澜他们在三四十年代的写作之外,我把它延伸到1949年以后,从5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就这样写成了第三本书,应该讲这第三本书不在我的计划之中,而是我的原计划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写完之后,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好多人认为我好像是研究史学史的,刚才还在给亚洲研究学刊评审一份关于国内新清史争论的稿件。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把自己的领域界定为史学史研究。不过这本书在中国史学史这一块,尤其是在美国,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这一块,此前还没有一本类似这样的书,去系统地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的近代史书写问题。这本书也有中文版,书名是《重构近代中国》,副标题是“中国历史写作的想象与真实”。
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在国外,书评的平台很多,国内倒不一定,国内书评到现在还没有发达起来,不像美国,美国任何一本书出来之后,三三两两都会有那么若干的书评,少的话也有三四份书评,国内写书评的很少。这本书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整个西方英文的书评已经有不少于20份。国内的中文书评,我看到有份量的是有两个人写的,一个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赵庆云,还有一位是台湾的某位年轻学者,名字忘了。他们两个人各写了一份很长的书评。我看完之后倒也是蛮欣赏的,写得都很好,我的书里面有些没有涉及到的地方,他们都很详细地讨论了。特别是台湾的这位学者,另外还有汪荣祖,他们都认为我的这本书里面没有涉及到港台学者。确实没有,因为我这本书主要是放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变化里面,看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演进脉络,港台完全不在整个的话语体系里面,没法把他们容纳进来。台湾的两位学者书评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提的也对,但是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港台,这是我的第三本书。
7
挖掘与建构:治史的双重目标
这里顺便谈一下史学研究方法问题。我觉得可能对国内的青年学者讲更加管用一点。就是说,你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到底怎么去给自己定位?怎么去寻找一个对个人、对你所在的学术领域都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这些年在国内跑了好多大学,也跟好些博士生有交流。最大的感触,还是大家研究的问题。我觉得研究得细,是没问题的,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范围,把它具体到某个地域,或者是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特别的年代,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某一个具体的现象,我觉得都没问题。博士论文,我觉得主要是起一个功能,就是你要通过你的博士论文来证明你的研究能力,而不是说要达到一个多高的理论水平,或者是说对这个领域有多少贡献。博士论文写作主要是个训练,主要是要证明,你有查找资料,筛选、鉴别、利用和消化资料的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它们组织起来,利用这些证据来支撑你的观点、你的论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培养博士生的基本的要求。至于说你的研究课题对这个领域有多大的贡献,你能不能把你的研究上升到多高的理论层次,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能力,但这不是我们的第一要求。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你要通过博士论文来证明你个人的研究能力。我觉得国内博士论文,这个方面做得都很不错。
实际上论资料的挖掘,可能比美国中国近现代史里面的博士生做得更好,因为国内资料更多,你有更多的时间,中文资料的阅读水平那更是远远超过美国这里博士生的水平,我觉得这是国内的长项。那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整个历史学研究,还没有形成新的范式体系,也看不出有一个范式转换的走向。这跟美国不一样。我上次讲,美国学术研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范式,然后时代背景改变的话,它整个的范式也是在跟着在变化。所以它的范式与范式之间的过渡,你看得很清楚。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黄宗智先生的乡村研究,它整个的一套概念体系,他的学术关怀,他整个学术最终的归结点,是跟他所处的七十、八十年代的范式问题、范式危机分不开的。我在93年以后关注晚清、民国的华北乡村,研究49年以后的中国农民,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其中的范式又跟过去不太一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代。就是说,你会看到我研究的一些取向,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延续了旧的体系,但是同时又吸纳了、引进了一些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概念和方法,我刚才讲的话语也好,场景也好,惯习也好,都是一个新的范式里头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是在摆脱旧的范式,进入新的研究范式,处在过渡状态。
实际上今天美国的史学,还是新旧两种范式并存,或者说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国内的史学研究,我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一定准确,就是不管是博士论文也好,还是博士毕业以后在大学里教书,写论文、写专著,往往是自说自话,缺少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意识。虽然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大都要求文章的开头必须有学术回顾,但是这个回顾往往做得干巴巴的,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下现有的研究,几句话介绍一下目前国内达到什么水平。这个只能说你的题目的研究现状,但是如何把你的研究嫁接到整个范式体系里面,去推动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营建,这种建构意识不太明确,甚至也没有参与建构的意愿。
好的史学论著,一定有鲜明的建构意识。就是说,不管你是研究中国史也好,美国史也好,欧洲史也好,每个领域的研究,都可以比喻成大家一起参与盖一栋房子,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范式。现代主义的范式这个楼造的很现代,是简约主义的,外面是平展的玻璃墙壁,里面是通透的走廊,感觉很现代很明亮,这是一种范式,倒退100年之前那可能是一种哥特式的古典主义的,雕梁画栋的,里里外外都很讲究。像我们这栋教学楼,是2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外面你会看到有局部的雕梁画栋,但是大面子上已经在走向现代主义简约的方式,所以就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建筑风格。那我们历史学研究,不同的时代我们也有不同的范式,就像在造一栋大楼,我们每写一篇文章,每写一本书,实际上都是在给这栋大楼添砖加瓦,我的作品塞进去之后,不管是墙壁,是窗户,是屋梁等等,要跟它协调,要跟它对话,要明确你对整栋大楼的贡献。你也可以根本不同意整栋楼的设计方案,要另起炉灶,日积月累之后,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取代现有的建筑,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不管新旧,这里面总有一个范式在规范、制约、刺激大家的选题和研究路径。比如说书架上这些《亚洲研究学刊》,发了这么多文章,其中大多数看了之后,马上可以判断这篇文章是在这栋大楼里面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可以给它定位,知道它的贡献在哪里。每个人写的时候,都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所研究的问题,所要提供的解答,会有什么潜在的贡献,大家的意识很清楚。所以说,好的文章或专著,一定有很强的建构意识。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缺少一种整体感,大家做研究、设计研究方案时,不太注意范式的建构,问题意识不那么明显。也许有解构的想法,就是要破除过去的革命史范式,但接下来朝什么方向发展,看不太清楚。大都是埋头做自己的研究,感觉有点一盘散沙,都是零零碎碎地在做,至于将来能否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全新的范式,现在看不出来。以前不是这样,在“现代化”范式初步成形的八九十年代,国内近代史学界几乎是万众一心,都在往“近代化”或“现代化”这个概念上靠,做得好的,后面都有五花八门的现代化理论、概念做支撑。在这之前的革命史范式,更不用说了。但现在看不出有一个什么方向,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解构过去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范式,其实现代化范式本身还没有长成,就已经夭折了。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比较专门的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派,有自己的研究规范、概念体系、问题意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学术国际化潮流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同行在选题、方法和概念上,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国外同行主要是美国同行保持同步,有强烈的对话和接轨意识,某种意义上,是将自己的研究嫁接到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里面。另外一些同行对跟美国接轨不感兴趣,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也不感兴趣,对于沿用过去那种概念分析方法都不感兴趣。那怎么办?曾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回到乾嘉,回到乾隆嘉庆时代的考据研究。就是说我们不谈范式,不谈概念,不谈研究理论方法,不讲史学理论,就老老实实去找资料,从资料里面找问题,然后写出一篇实实在在的论文。我前面说了,挖掘非常重要,挖掘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我们对博士生写论文的第一要求。但仅仅有挖掘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建构。如果我们把挖掘而来的资料,比做人体的血肉的话,范式的建构则等于是人身上的筋骨。最好的研究当然是既有挖掘,又有建构。但事实上,往往难以兼顾,只能偏重一头。我的感受是,在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从写博士论文,到出第一本、第二本书,多做些挖掘的工作,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解读上,做扎实些,这是立身之本,也是赢得同行认可的地方。到了学术生涯的中后期,在美国那就是拿到tenure,特别是做到正教授之后,不妨跳出自己的老本行,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多关注些大问题,多做些建构的工作。
8
国家转型视角下的近现代中国
建构不光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近代史的诠释体系、历史分期、历史主线等等宏观的问题,更多地应该是从具体的问题着手,通过具体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解读,推动整个范式体系的更新。举个例子,我们过去讲北洋军阀,都是说国内各支军阀搞割据,四分五裂,连年混战,政治上黑暗,军阀专制等等,总之是一个中国近代化进程好像中断的时期。也可以讲政治上走向衰退,原来还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那现在是四分五裂,相互混战。过去我们讲这是一个黑暗时代,是政治上走向衰败的过程。可是,如果你撇开这一套,仔细研究各支军阀,会发现军阀跟军阀实际上不一样,不能把所有的军阀不加区别地看待。为什么有些军阀最后能够做大做强?有些军阀最后就给对手吃掉,所以须做具体的研究。我看了国内外对奉系、晋系、桂系、直系、皖系的研究,包括大量的论文,我都去看。看完之后发现有意思,为什么最后奉系能够打败北方其他军阀?为什么最后是南方广东的孙中山派系能够吃掉其他的派系,最后统一全国?为什么奉系跟广东国民党这两个派系能够做大做强,最终是国民党吃掉所有其他的派系?它一定有它的内在原因,这个内在的原因就是它要搞内部的政权建设,要将自己地盘上的税收制度、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的体系,加以集中、规范、制度化。谁的制度化、规范化、集中化做得越好,它的竞争能力就越强,最终它就能打败那些不规范的派系。国民党在广东时期是做得最好的,它所产生的财政收入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军阀。它的政治凝聚力、组织力也是其他对手没法比较的。奉系也是这样,它的制度化、规范化也做得不错。其他的军阀要不就是没有固定的地盘,要不就是靠临时的非正规的手段去产生财源,制度上也没有走上轨道,所以没法跟这些制度化、集中化的对手比拼。
看了这么多材料之后,做了些提炼,最终打出一个概念,叫Centralized Regionalism。每个军阀都是割据一方,控制若干个省,这是所谓的Regionalism,地域主义。同样是地域主义,有些做得很差,有些是高度的集中,广东国民党跟东北的奉系,虽然割据一方,但是内部都是相对较高程度的集中化、制度化、正规化,所以叫集中化的地域主义。
这就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它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路径之一。我们以前讲现代国家的形成,更多地是想象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像英国、法国等等,通过强化王权,收服、打败了地方势力,把触角推向全国。可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几个关键环节,其中之一,是先由这些军阀搞地方割据,然后一方做大,打败其他军阀,从地方走向全国,自下而上进行的。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当然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欧洲那些比较后进的国家,意大利、德国,以及德川末年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也跟民国早期的做法一样,先由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相互竞争,最后一方做大做强,然后统一全国。所以,集中化的区域主义,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以前我们讲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强调革命,强调反帝反封建,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从清朝原先的专制主义走向民主化,有各种失败的尝试,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辛亥革命,都走不通,然后才有共产党革命等等。
这些我觉得就史实来讲也没错。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怀,范式也跟着在变。现在的时代背景跟以往有根本的改变,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所以要跳出民族国家历史的窠臼,放眼全球,超越过去的革命史观,也要超越现代化史观,重新认识过去的中国,给今后的中国以全新的定位。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里面,就是要历史的角度解读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史、现代化史,是用“国家转型”这个视角,从清朝入关一直讲到49年建国。清朝国家,我给它界定为“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它不是主权国家。主权这个概念是从欧洲传过来的,欧洲人讲主权,是近代国际法的一个概念,中国人以前不讲主权,19世纪以前的中国,你不能说它是一种主权国家,但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帝国。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帝国,一两句话讲不清,《历史研究》将会登出一篇文章,标题叫《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可以参看。既不是帝国,又不是主权国家,那它到底是什么国家?我觉得它有自己固定的疆域,并且早已具备了欧洲国家到了早期近代也就是16世纪以后才慢慢获得的若干特征,比如中央集权、官僚制、常备军等等。所以中国是如何从19世纪以前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转型为一个现代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更大的过程和议题,比我们讲反帝反封建革命更加宏大,比我们讲从专制到民主这样一种现代化过程更加包容,更加开阔。这是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今后的走向,更有解说力。不过,这本书的中心意图,是要打破过去在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把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理解为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而不是从殖民帝国或征服王朝向(以欧美国家为原型的)所谓“民族国家”的线性过渡。17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形成的最大特色,在于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而非前后断裂,这是理解现代中国最关键的侧面之一。
总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你要给他加以提炼。我这本新书借助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加上充分利用各类原始资料,做了自己的解读、提炼。英文版已经在网上预售,书名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中文版也已经翻译了,早就签了合同,交给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但书中涉及到很多问题,有些还很复杂,最终能不能出版,何时出版,现在都不知道。实在不行只能送到其他地方去出。
采访:郭星星 邓啸林 纪浩鹏
整理:陈蕾 郭星星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 2019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