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新亚农圃道圆亭演讲,记得好像这是第二次了。1971年,我从美国第一次回香港,(就我离开香港到美国后的第一次回香港)也在这里,做过一个简短的讲演,讨论清代的学术问题。
今天,我要讲一个比较广泛的题目(上次我讨论的是一种比较具体的、专门性的):史学、史家与时代。这个题目,非常宽泛,也非常抽象。我并不是说,我能够讲尽这里边所包括的许多问题。
我想,用这样一个大的题目,也许可以给我自己多一点自由,可以随时的变动。这个题目,我是用一个普遍的形式来提出的,就是说,我不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家,或是哪一个时代的史家,我是普遍地、抽象地讲史学、史家以及时代的关系。
这三方面,是交光互影的,在我这个简短的讨论中,会先后或者同时地出现。
我讲史学,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史学与史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从我的题目里可以初步看出来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表示了,我们的史学已经受到时代的冲击。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史学,刚刚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史家对这个问题就不是这样一种提法。比方说,最负盛名的兰克,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是要追求历史上的客观的事实,寻找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了,这是史学家的责任。
兰克有一句很有名的话: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含意,就表示说,史学家不应该有主观的判断。主观的判断,是史学家应该去掉的东西。后来按照兰克的这个说法发展下去,并且紧紧地跟他走的人,在英国、美国、法国都有。这些人慢慢变成一种科学的历史的宣传者,即所谓scientific history,科学的历史——历史要变成一种科学。
历史变成一种科学的意思,就是说,历史不能由人的主观来运用。法国的伏尔泰讲过,历史是人(史学家)对于死人玩的一种把戏,是跟死人开玩笑(play tricks on the dead)。跟死人开玩笑,就表示说,我们对于历史可以自由地改造,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这种主观的因素,在十九世纪,由于科学的冲击(科学的冲击只是一个方面的力量,还有别的力量我一会儿再提),就引起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去掉,使史学变得和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一样。这是一个很高贵的理想,很高贵的梦。从这一方面讲,兰克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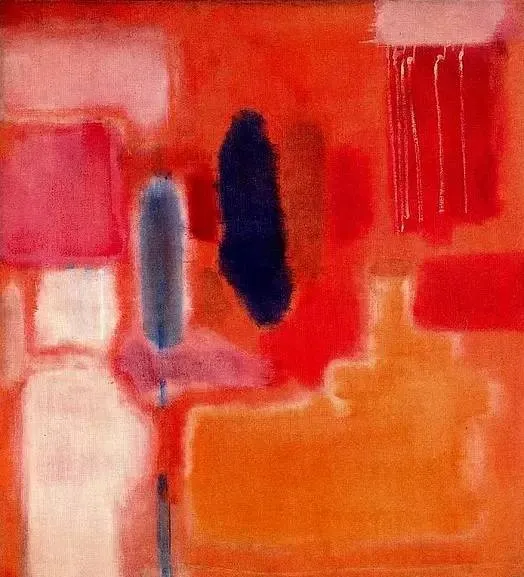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许多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可以客观了。比如,法国的Fustel de Coulanges,他也是一个主张科学的历史的人,他有一部书,是讲古代的城市,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在中国,好像是李玄伯先生翻译过)。他是十九世纪的讲课学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
人家问他,你讲历史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说,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来说话,就表示说历史完全是宽的,我不过是一个工具,像一个录音机播放出来一样。这是他们当时的理想,认为绝对客观的历史是可以有的。如果找这种说法(科学的史家),那么就无所谓史学和史家的关系了。
一位史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不能够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在实验室里面,你的结果都是客观的;你的材料、你的方法控制着你,你没有什么自由,你没有什么可以主观地运用的地方。这一点是造成近代科学的历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观念。我特别提到兰克和他的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在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上,也去过很大的作用。
我刚才讲过,兰克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受科学发展的冲击(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大家觉得,我们研究人的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研究历史问题,一样要用科学的方法,即兰克所谓客观的历史的态度)。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十五、六世纪以来的philology的发展。
philology简单地说,亦可以说是相当于中国的所谓训诂、考据。就是研究一个个拉丁字的字源,从这些字源里推断出一些古代的制度来。最初是用之于研究罗马史的,后来也应用到其他地域去。比如说,像兰克以像稍迟一点的英国Lord Acton,J. B. Bury等,这些人治史都是从古典罗马开始的,都具有古典的训诂学的,或者是考据学的训练,所以,philology很像中国乾嘉以来的所谓考据,事实上中国在乾嘉以前已早有考证了。
西方的考证学传统,加上近代的科学思想,变成了兰克的学派。这个学派,在西方有一个名称,叫它“历史主义”(Historicism)。Historicism有很多讲法,今天有很多历史主义的不同的定义,不过最原始的是讲兰克这一派的思想的,指科学的史家的思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兰克史观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训诂的背景,一个会对科学的尊重。这两个东西,在近代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刚好需要。
第一,我们有乾嘉的底子。乾嘉的底子,是我们讲二十世纪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今天,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第二,是我们需要有客观的历史,要避免历史上的主观因素。换句话说,因为在中国一向有褒贬式的历史,在历史上讲褒贬,即西方的所谓praise and blame,这一套的思想在我们的史学传统里特别浓厚;所以历史研究上,如果我们想进到客观的境界,就更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客观史学的挑战。这个挑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上刚好也合拍了。
一方面中国有考据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二十世纪需要科学。所以,进到中国史学的一部分的潮流,并且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潮流,就是语言、历史打为一片这个说法。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座全汉昇先生、严耕望先生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英文叫作History and Philology便很明显的表示德国的影响、兰克的影响。
这是因为傅斯年先生在德国留学,受了当时风气的感染。虽然二十世纪的初年,史学界的变化已经开始,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感觉到,当时还觉得,兰克这个想法是对的。当时所谓汉学,就是刚才全先生讲到的法国巴黎的汉学这一派,也都是走语言学考据学的路子,所以汉学是如此。当然,傅先生与法国汉学也有相当的接触。傅先生在德国受到兰克这一派史学思想影响,因此觉得研究历史必不能离开语言。

傅先生自己很有名的一部著作,讲性命古训辩证,就很明确地表示这个方法。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读一读那篇论文里边的序言部分,是讲方法论的,讲何以语言与历史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想,基本上说,这个说法并不错。今天有许多人批评它,就是因为它走到极端,就以兰克来说,兰克自己也没有跑到后来那样极端。兰克本人并非极端的历史主义者,就像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所以极端的历史主义,是后期的发展。
不过,傅先生把这路思想传来以后,引起了几个重要的后果(是指对中国史学有所影响方面而言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历史与语言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似乎已不成问题。第二,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讲什么呢?是讲材料,材料完备,你就可以得到完善的历史。所以材料(或说史料)便在是历史的说法,中国也一度相当地流行。
这个观念,也可以说是从历史主义里派生出来的,是副产品之一。第三方面,因为要将材料越多越好,所以讲史学,一定要渊博。这与考证学有挂你。考证学一定要渊博,你要不渊博,你就没办法把无数有关一个小问题的材料集中起来,求得一种彻底的解决。
在古代没有index的时代,你怎样找材料?完全是靠自己,靠记忆得越多越好,靠多看书。所以,渊博本身也成为治学的一个理想。这几个方面,都跟philology有密切关系。这在西方,已经可以得到证明是如此。比如,十五世纪意大利的Valla,十六世纪的Bude,都注重渊博,都是从训诂讲到历史考证。
在中国亦是如此,清初的阎若璩,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渊博的人。他自己也把“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悬为治学的理想。所以求广博的知识,这是philology所带来的的。这在中国也有影响。在理论方面,傅先生讲得比较清楚,有好几篇重要的文章,包括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渊博,也就是材料的掌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渊博,我们大家都佩服的,可是陈先生的渊博,也可能是他在德国受到的影响,就是受到考证学派兰克这一派的影响,讲历史要越全越好,一生在准备材料,要准备写一部所谓的最后的历史。
因此陈先生的重要著作都自谦为“稿”,就表示未成最后的定论。要写最后的历史,照当时的想法来说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历史真跟科学一样,达到绝对客观的境地。(当时的观念中的科学,跟现在又不同了。)当时的观念,如果我们把材料完全搜集全了,对每一小问题作过极深极细密的研究,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主观的成见。到最后,所有问题都研究完了,我们可以综合,可以写出一部最后的历史。
有这个理想在那里,因此,我们作史学研究的人,提倡史学的人,万钢觉得应该先鼓励人家做小题目,就是胡适之先生常说的所谓“小题大做”。我最近看到胡先生给吴晗的信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让你研究明史,不是要你写一部新的明史,你要做许多的小题目,吴晗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吴晗后来写明太祖传的时候就说,我的明太祖传,是根据几十篇研究明朝初年的论文来做一个基础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分析工作,历史的分析工作,应该在历史的综合工作之前。这也是在历史主义思潮之下所应有的一个发展——思想上的一个发展。

从某些方面上讲,他们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说并不错。我们刚才讲到历史主义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开始,就是肯定有客观的历史,主张用最渊博的学问和知识来治史。当时欧洲和英国的大师,包括兰克、Coulanges、Acton、Bury等都具备这样的条件,都可以说是史学界特出的人才。
可是这一派的历史思想,影响到外国去以后,慢慢发生了反应——发生相反的反应,也可以说。——我记得在1934年,在美国的历史学会上,有一位叫作Smith的学者,检讨美国从十九世纪末到1934年这几十年中间的美国史学,他把美国的史学家分成两类,第一类的人是根据兰克的理想的,要找历史上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要建立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理。他说这一派的人在美国的史学界,无论写大的书,还是写小的论文,都有很好的成绩。相反的,不根据这一套说法,不根据兰克这套思想走的人,其成绩都是很差的。
当然,后面这句话他没有明说出来,可是含意是很清楚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就是Charles Beard的反驳。Charles Beard是近代美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作“那一个高贵的梦”,因为Charles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有一个高贵的理想,高贵的梦。这个梦就是说要搞客观的历史,不带任何主观的因素的历史。Charles可是说职业史学家中,在二十世纪时,第一个正式向兰克史学派“开火”的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主管部分在史学上是永远也去不掉的。为什么去不掉呢?这个问题我等一下再讲。

先讲讲在这以前,即十九世纪的时候,是否每个人都接受兰克的说法呢?也并不然。我们知道,至少,在德国,就有好几位哲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是反对兰克的。
第一位,是H. Rickett,第二位,是W.Dilthey。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的人,也都对哲学有兴趣,当然同时对历史也都有造诣。这两位先生的思想,在当时已受到注意,可是还没有受到广泛的注意。在这以前,攻击科学史学的人也还有,比如说,稍前一点的,就有尼采。
尼采有一篇文章,叫作“历史的用处与其弊病”。尼采这篇文章,也是说,如果照兰克的说法,照这个一派科学的历史主义思想,那么,历史是没有生命的,是完全为一堆死的材料,死的东西,与人无涉的。因为尼采是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他的文章,可以说在当时是没有受到注意,一直到后来,Rickert和Dilthey提出同样的说法以后,才在史学家中引起了一些反应。
Rickert的说法,他把所谓科学分成四类,一种是所谓不涉及价值的,同时,又是讲通则的。一方面讲通则,一方面不涉及价值问题,他说这种东西,是所谓纯粹的科学,自然科学便是如此;另一种是不讲价值,但是是讲个别性的,讲特殊性的,比如地质学、生物学是属于这一类的;再一种是涉及人的价值问题,又是讲通则的,讲经济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规律,比如经济学、社会学;第四种是有价值问题,而讲特殊型的,这便是历史。历史是讲特殊的事情不讲整个的通则(当然照今天的看法,通则也是需要,这涉及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我今天不能讲那一方面了)。
历史的每一件事情,主要是个别的。(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我同意或不同意。就是说,这种说法可以接受挑战,你可以说历史并不是个别性的,这已经有人提出来,而且已经讨论很多。我们今天不能旁涉太远。)这是Rickert在当时对于科学的分类,我们同意不同意他的分类,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特别强调的人的主观性,在历史学里是不容易去掉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涉及价值(这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价值与史事的分别,及何谓史实的问题)。
Rickert的这一挑战,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注意。再进一步,就有Dilthey的理论出现,他可以说是一个注重心理学的人,是个心理学家。同时,他们又可以说是所谓大陆的理想主义哲学家。Dilthey有志模仿康德写一部“历史理性批判”,但没有成功。他讲历史特别注重心理学分析方面(不是现代佛洛依德以后的所谓心理分析),强调治史者要注重内在体验。
这一派的思想,后来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英国的科林伍德,他是近代的一个新理想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他当然受到Rickert、狄尔泰等的影响,把历史看成不仅不同于自然科学,并且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可见主张历史研究上有主观因素这一派的思想,在兰克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不过,要到Charles Beard的时代,才能真正在史学研究上发生很大的作用。
Charles Beard的That Noble Dream提出来之后,可以说近三四十年来的美国,基本上是接受他的说法的,基本上是认为研究历史,史家的主观是去不掉的,就像Mazzini所说的:我读任何历史学家的书,只要读上二十页,我马上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观点。这种说法,是相当有道理的。
尽管你嘴里说要客观,你尽量的希望没有主观,可是,你的教育,你的背景,你的价值观念,无形中都影响到你对史料的选择,对于问题的提出,甚至对问题的提法。所以,历史学上有一个主观的因素,解释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驱除不去的。只要有史家在,就没有办法完全去掉。
而且,后来人家索性研究兰克本人,就是说,既然兰克自己说有绝对客观的历史,那么,我们来研究兰克,看看他有没有表现一种价值问题在里面。试试啥,大家研究的结果,发现兰克本人也有主观,他代表一种国家主义的偏向;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他又代表一种保守派的思想。国家的观念,保守派的立场,都影响他对问题的选择。
他为什么要注意日耳曼国家的起源问题?这表示他自己同样有一套价值观念。所以,最初开创的人,同样不能排除历史的主观因素。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我相信已经证明是可以成立了,大家稍微想想,也都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可以谈所谓史家与史学问题。史学虽然说是客观的,可是不能够变成化学、无力,完全没个人的因素。
那么,是不是说,历史是完全主观的东西呢?可以随心所欲呢?是不是我们对死人开的玩笑呢?我想,也不是的。
一方面,我们现在固然要反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兰克的历史主义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很尊重考证学派与讲客观真理的这个学派的对于史学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最要紧的方面,就在于对个别史实的鉴定,个别史实的考索,能做到尽量客观的地步。因为长期从事于文献的研究,他们形成了一套很精密的研究方法。这在中国可以用乾嘉作代表,在西方,千千万万的历史论文,都可以说是遵守着一些确定的客观的标准。所以,在史学研究上,对于个别材料、个别问题的处理上,西方历史主义学派在史学界上的贡献、中国乾嘉学派在史学界上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都将永远成为史学上不可少的知识基础。
可是,他们的毛病,是建筑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上。这个假定,在当时来说是不易避免的。我们今天不能笑话他们,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有了不同的了解。我们处在几十年后,看法不一样,不能因此说:这些人怎么这样糊涂。其实不是糊涂,要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还不一定能懂他们的说法。所以不能以后笑前。

学历史的人,最要紧的,我想就是要谦虚,越看前人的成绩,就越觉得自己渺小。这话虽是题外话,我想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我们虽然批评兰克和批评考证学派,这只是从一个更高的综合观点上来批评。就是说,关于历史学上主观因素的问题,他么忽略了,看得太简单了。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一面接受考证学派、语言学派讲的客观真理。
我们得承认在实际工作上、文献处理上、个别问题解决上,语言学派、考证学派的贡献——这一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而且是永远需要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张历史研究不能只讲分析,也应有一个综合观念。历史学与史家对时代的主观感受有密切的关系。这就牵涉到所谓史学与时代的问题。
史学、史家与时代,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这一点,我们刚才讲到兰克时已经证明了,他认为他可以超出历史,事实上他没有超出历史。他认为它可以不讲时代问题,可是事实上他选择的问题表现了时代性,他已经不自觉地做了某种主观的选择。
比如说,像Coulanges这种人,绝对相信科学的历史,他说爱国与不爱国,与历史没有关系,爱国是一种道德,一种德性,可是另一方面,他说历史是一种科学,所以这两者不能混而为一。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但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也受到影响。中国也有人认为,我们讲历史就是讲历史,不管什么民族的情绪,不管什么Coulanges所讲的爱国的问题。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史实,一谈到爱国就卷入情感了,也就可能不够客观了。
所以我想,兰克这一派的理论发展到极端,也有好几个方面的流弊。一个方面是太重视小的考证,就是主义太多的小问题,而常常忽略了大问题。换言之,就是把分析看的很重要而把综合看成轻易,或者看做不重要,或者觉得危险,或者觉得不值的做,其中必有一个。
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这个理想的本身,我也不能说它错,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上,也应该有些学者,像这样把全部精神灌注在学问里面,精神生命都在里面。这是一种了不得的精神,这种精神绝不可以轻易地加以批评。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史学全部跟现代人生没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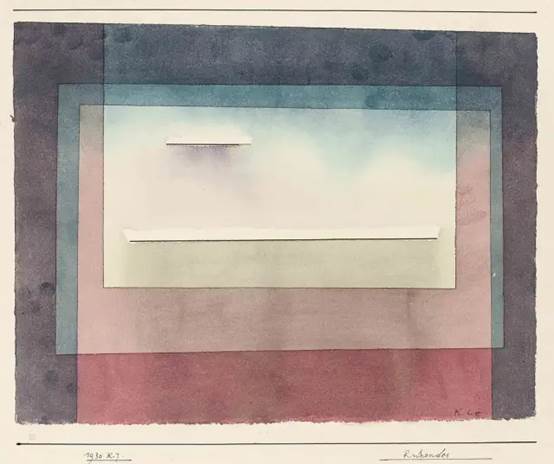
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因人而异,可是照我个人的看法,照我涉猎到的几十年来讨论史学问题的书(我在这方面主要是看重职业史学家自己写的书,我不太看重哲学家对于史学的分析。
哲学家对史学的分析,近二十年来,因为所谓分析哲学与英国的ordinary language这一派的影响,著作很多。大体上是对历史的语言进行精确的分析,同时也讨论到历史的通则或历史知识的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哲学家的问题),发觉有一个问题,大家都似乎很注意,就是说,历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的。
所谓人,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换言之,历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
这一点,许多史学家都同意。比如,E. H.卡尔是研究俄国史的,他有一本很重要的书,1962先出版的,叫《什么是历史》。这本书是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讲演,相信在座多数先生都读过了,我这里也不必详细介绍它的内容。
后来许多人(从美国到英国,从哲学家到史学家)对他的批评,有一个共同点,便认为他还是新实证主义的一个代表,相信历史是进步的,社会是可以越来越好的,这本书的最基本的观念就在这里。但卡尔也承认,历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也承认,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不可分。为什么?他说,你要将历史的事实与价值完全分开的话,那只有在一个静态的世界里才能做得到。
在动态的社会里面,你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不能说这是事实部分,那是价值部分,所以根本是分不开的。卡尔很强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的,史学家影响到事实,事实当然也影响到史学家对问题的考虑,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一个动态的关系。第二个方面,他特别强调,对于史学家,人生是最重要的。这又牵涉到古今的问题,我们下面要谈到。
学历史的人不能完全忘怀现实生活。所谓历史学家的主观就与他的现实生活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史家的主观问题上,他和Charles Beard见解一致。不过,他强调,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一个观点,有一个一偏之见,那就应把这个观点、这个偏见提到自觉的程度。
这是一个化主观为客观的必要过程。自觉的主观便不致影响到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于你肯不肯承认有一个看法,并说明这看法是根据某种假定。你要坚持说你没有任何假定,你是骗人的。你一定有假定。有许多史学家,明明有假定而不肯想“我有什么假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天经地义。
一般的人,头脑里有许多东西常常不受检讨,不受怀疑,因为这些东西好像是人人都接受的。在史学家来说,没有一种观点真正是天经地义的。除了你自己的看法以外,你还得看看别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要认为你自己的想法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一切问题就无从谈起了,整个门都关上了。即使是天经地义还可考虑,可讨论,这才是史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
卡尔在这方面,我是相当同情他的。每个人既然不能避免主观,那么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主观的问题,把基本的假定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来,提到一种自觉的状态来。假借客观的外形,来隐藏一种主观,这对史学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更早一点,像法国的有名的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1941年有一本未完成的书,后来译成英文,叫作《历史学家的技艺》。我们知道,布洛赫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研究法国历史,尤其是中古封建社会史,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在近代最受推重。另外一方面,布洛赫又是最爱现实的,最爱人生的。他因反纳粹而被捕,后来关在监牢里,到1941年被纳粹杀了,还不到六十岁。当时许多人劝他离开法国,但他不肯去,坚决抵抗德国,反对纳粹,终于牺牲了生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于人生,是极严肃的。他极爱他的国家,极爱他的理想。
在史学方面,他还受到兰克这一派的历史主义相当大的影响,也受到philology的影响,因此,在他这本著作中,客观主义的气氛还是很浓。可是这本书是在监牢里写的,写的时候手上也没有参考书,是凭记忆写的,所以这本书没有什么旁征博引的地方,完全是一个史学家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自己当然不知道)反省史学上的许多问题。
这书中牵涉很广。他是一个职业史学家,他对于人生所表现的热情,和他对史学工作所采取的客观态度,可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我们史学家所最关心的就是人。他引他的朋友Henri Pirenne,也是一位大史家,的一句话:我是历史家,我爱人生。他把史学家比喻为童话中的一种妖怪,只要闻到哪里有人肉香,就在那里出现。
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史家应重视人生,在这方面,他与卡尔是采取相同的看法。这两个人在思想上没有关系,也没有渊源,但两人都认为人是史学家的中心问题。这里面又牵涉到史学研究对今天有什么用处这问题,当然这是很难答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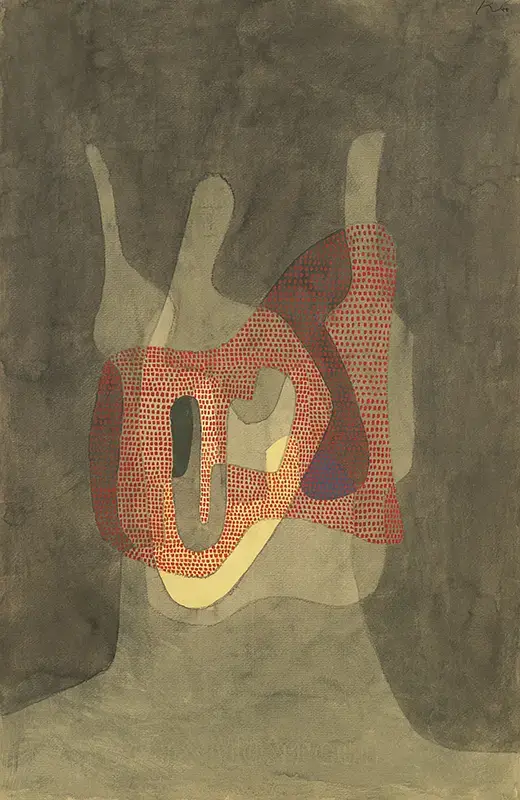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历史上看,史学一定是有用的,在政治上尤其有用,其实所谓“古为今用”,在中国自来就这样说。说得最清楚的,比如请朝初年的魏禧,就说“考古以证今”。在中国,在西方,传统史学都是以政治为主,以自己的国家为主。中国是以古为鉴,这当然是很早的话,后来变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就是在历史上照照镜子。这个照照镜子的思想在西方也一样有。中古时有所谓“国王的镜子”,就相当于中国的通鉴。
讲历史应注意什么问题,才对于我们国家有帮助,这是今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历史是镜子,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历史在以往确确实实发生过作用。比如做皇帝的人,往往要读历史,包括像乾隆这样的人,也读历史。在早一点,历史地位相同的人,总要回头看看历史,看看前人用什么方法处理相同的难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记得好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研究宋史,有一次谈天,他说宋高宗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我问怎样个了不起。他说,宋高宗有许多地方是有开创性的,比方以柔道治天下,以前的皇帝就好像没有说过。我说我记得汉光武本纪上就有这句话。汉光武是一个中兴之主,宋高宗也是一个中兴之主,一个是东汉的开创者,一个是南宋的开创者。一个南宋的中兴之主,很自然地会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兴前例,也很自然会读点史书。不过我当时虽查出汉光武的确讲过柔道治天下的话,但是我还不能找出证据,证明宋高宗真正看过汉光武的本纪。后来,大概过了一、二年的时间,我偶然看了王明清挥尘录,里面有一条,说宋高宗曾手抄汉光武本纪送给臣下。这是一绝对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宋高宗一定好好读过汉光武本纪,不但读过,还手抄了一遍,可见他确确实实把历史当做一种有用的东西。
我们讲史学有用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如此。我刚才说过的“国王的镜子”,这可算是外国的资治通鉴,虽然“国王的镜子”不是纯粹历史。在近代,如十九世纪英国的seeley,他认为历史知识是可以造就政治家的。他的名言是所谓“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历史”,从这方面看,至少历史对于统治者,对于负责最高权力的人来说,它是发生过作用的。
像二十世纪的丘吉尔,就是大史家。记得杜鲁门女儿写过关于他父亲的回忆录,其中提到有一次英美最高统帅开军事会议,商量诺曼底登陆,丘吉尔对法国北岸的小村镇的历史如数家珍,什么地方以前打过仗,胜负如何等等,大家惊服不已。甚至于眼前我们还可以看到统治者运用历史的例子。毛泽东就是这样。历史对他还是有作用的。至少我个人的看法(这说法当然还需要证明,我不过是随便的说说),至少他是有意无意地有些地方是在学明太祖的。1950年左右他看过吴晗的朱元璋传,并且有批评,这事似乎可靠。吴晗的那部传记对他有极大的影响。比如红卫兵,好像是新兴的东西,其实明太祖就用过,明太祖用监生,用国子监的学生,就可以说相当于毛在文革时代对红卫兵的运用。明太祖诛戮功臣,一再整肃干部,动以万计,到后来的政治上无人可用。
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研究。我相信可以找出找出不少证据来证明历史对统治者有作用,一直到今天为止。或者也可说,历史的影响,不一定直接来自史书本身,还可以从小说如三国演义来。三国演义可说它是小说,也是历史,是用小说的形式写历史。三国演义对中国人也很有作用的。西方的史学家,也都承认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对于许多西方读者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些方面看,历史确是有用的。
今天我们讲历史的用处,当然不只是为了少数人,更不应该是为了统治者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写历史,是为了大家看的。我们的时代是民主的时代,如果我们还承认,民主本身是个价值的话,那么历史本身也应该经过民主化,不能为了少数的人服务的。
司马光的通鉴诚然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可是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写新资治通鉴了。因此,史学和时代是有一种很明确的动态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就要看史学家对于他的时代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深入进去,是不是时时注意现实人生上的问题。
史学家关门来不问世事,固然也有。不过我们不必担心。这种人的比例只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社会上总要有少数的学者,他的生命,就是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他全不管。对于这样的人,这种态度,完全不必担心,不但不用担心,并且还要尊重。
应该担心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把专门的史学知识,从学府里面,传播到社会上去。这倒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有很好的的办法来解决,比如他们的教育制度好,他们的教学方法也是认真的,所以许多第一流的史学家,不仅是做研究工作,同时还肯花时间去写教科书,或者相当于教科书的这一类书,把最新的历史知识随时推拓到社会上去。这对于一般人的历史教育是有很大的作用。今天的学院里面档案性的研究很多,如果没有一些人将它综合起来,这些千千万万的专题研究,都没有了生命。
这不是我说的话,是一个富有天才而不幸早夭的人类学家Philip Bagby的说法。他认为今天散在无数种专门性刊物中的历史论文,如果没有人把它们的结论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那么这些论文便只能是历史的研究,而不配叫做史学。
这一点,中国十八世纪的章学诚,也有相同的说法。章学诚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在清代有这样的看法,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他明白地分出史考(今天所谓的考证)或者史纂(今天所谓的编辑)与史学不同。
所以今天大家说编史料,这是一种,如大陆上编了很多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这都是史纂。另一方面,千千万万在各种学报中的论文,都是史考,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应该有人随时做这类工作。我相信,中国过去讲通史,如司马迁,或西方如兰克,也讲universal history,都是人为史学本身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那图书馆里。

写通史,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得很多,而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做综合工作?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部通史,或全面的历史,你可以写一个时代,你也可以写一个专门或者政治制度史或思想史或经济史,这也是一种综合工作。所以综合不限于一个全面的,当然全面的教科书不断也会有人写,社会上也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这几十年来在教科书、通史的编写方面,可以说成绩很有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至目前为止,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钱先生的书,当然有人批评,这是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的。但你要从看问题的深度方面、广度方面,从见解方面来了解这书的价值。如果你要我介绍一部通史给你读,我只能介绍钱先生这一部。
钱先生这部书,不是真正的教科书,这里包括了他的许多特殊的心得。不过,他是希望成为教科书,而且实际上已经被大家用为教科书好几十年了。这书在大陆引起了许多批判,这就证明它有影响。比如研究王安石,大陆有许多专门研究王安石的文章,可是他们也还是把国史大纲中讲王安石的一段特别提出来,加以批判,可见钱先生的观照,是有他的独到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好的史学家,第一流的史学家,除了做分析的工作,还要注意综合的工作。
最近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认为最和标准的历史,过几十年就要大事修改。举两个例子,阿克顿勋爵十九世纪末叶为了编制剑桥近代史写过一份报告书,他说,我们希望将来(他说目前还不可能,要过若干年,等历史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能够写出一部最后的历史。这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事。
第二个例子是,到了1959年,过了差不多六十年,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编了“新剑桥近代史”。好,你看他书上所说,历史是不能绝对客观的,历史是要不断改写的。过了五六十年,史学的气候全变了,同样一部书,旧的编者的说法与新的编者的说法,可以说相差万里。这就说明,第一,史学里面有主观因素,有个人的因素,第二,历史永远没有办法写出所谓最后定本。
有人说可以写一部历史,使后来的人没法再更改一个字。我想这是文人的夸大说法。历史永远是变动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需要,每个史家都有每个史家的个别的性情。换言之,历史时时要修改,这是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很简单,任何时代的思想或者社会的运动,都影响史学,如法国大革命对史学的影响就很大,是不是?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新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对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度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但是Fisher在A History of Europe的序言上有句名言,历史有时是进步的,有时是退步的,没有一定的方向。这又是史观随时代而变的一个例子。
我到香港后,听到“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种说法,当然,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看得太严肃。什么是“历史潮流”?你怎么知道它是“不可抗拒”的?这问题要是问下去的话,我想没有人能答复。相信这句话的人,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以赛亚·伯林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本小书。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相信有客观的事实;这些客观的事实,通过考证学的整理和鉴定,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这是史学的一个层次——科学层次。可是,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这又是因人而异。根据同样的事实,不一定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因为史义属于另一个层次——即哲学的层次。现在有人说,乾嘉的史学,是一种科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研究历史,是研究古代呢,抑或是研究现代?什么是今?什么是古?这也很难说。我刚才讲的一句话,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我的整个演讲还未终结。历史是要讲连贯性,是根据“事”来讲的,比如我在这里演讲,你不能把我的演讲词切成许多片段,这样,就失去其连续性。
讲历史的连贯性,一定要讲事,事本身没有完,历史便还在延续之中;即便事本身完了,还有它的余波。所以,讲古讲今的界限很难分,研究古代的历史比研究现代的历史为重要,这种说法是一偏之见。其理由大体是,眼前的历史,材料不易收集齐备。我想,这还是根据兰克一派的说法推出来的。
这种说法,认为要研究历史,必须将所有的材料搜集完全后再下判断。又说要将某阶段的历史的每一部分都弄清楚之后,才能写那个时代的历史。这说法很成问题。如兰克派的名家,英国的阿克顿,一生都在史料搜集和准备阶段,因此终不能写成一部历史。
从另一个方面说,历史对人的影响,不一定越近就越重要,这并不是与时间成正比例的。近代的历史,如果没有重大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一定很大;反而,有些古代历史上的大事,对我们的影响,对整个后代的影响,却有时是很巨大的。所以治史不必存古今之见,要看个人性之所近。
同时,我们要写什么样的历史?怎么写?这个问题也同样没有一定的答案。我想,还是得根据个人的兴趣,自己找题目,找自己有兴趣的题目,比如你研究某一个人物,可是你自己不喜欢他,对研究的对象不能有同情的了解。这样你研究也不会精彩。所以这里边有个情感的因素在内(即所谓emotional tie)。
我记得郭沫若以前写“十批判书”的研究韩非,说我越来韩非子的树就越不痛快。如果越来越不痛快,那你根本无法研究,是吧?你能把你的感情跟历史结合,你便有了写出比较好的作品的条件,不管是那一方面的,研究一个人物,研究一种制度,研究一次战争,或是研究一个朝代。所以这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完全是视乎个人,跟他的个性有关系。
我们说历史里面有主观的因素,史学家与时代、与他们的学识修养有很大的关系,这就引起关于史学家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史学家本身就是史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史学家写史本身就是一个史实。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记得李济之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年到华盛顿去看蒋廷黻先生,蒋先生问他一个问题,说:你看司马迁伟大呢,还是张骞伟大?我想也许蒋先生晚年有些怀疑他是否应该丢掉史学去改行为外交家吧!这问题显然没有一个答案;不过,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司马迁的影响恐怕要大于张骞。
司马迁写史记,本身就是一个史实,通过写史而创造历史,所以史学家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本身已经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所以我讲史家的恶人,是因为史学里面特别有主观的因素,个人的因素。
在外国人讲自然科学的来说,并不觉得科学家个人的道德、修养、品格的重要,或对学问有什么重大关系。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科学家本身修养坏得很,可是他可以得诺贝尔奖。这事情并不稀奇。
自然科学家也许可以如此,可是,在史学家来说,似乎并不一样。史学家的主观既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则他个人对人类、对社会很有影响,如果本身修养坏,本书的缺点不加以克制,对自己不能加以纪律,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坏的。
所以,西方的史学家现在也提倡这一点。像前面举的例子,认为史学家要重视人生,热爱人生,其涵义即在此。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绝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与我不相干一样。这虽也是一种态度,不过这样的史学家毕竟是少数。
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刚才我们讲兰克,事实上,他反映时代是很深刻的,如果他对当时的时代没有感情,没有对时代的密切关心,他便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来。又像王国维,他研究甲骨文,与现实好像没有多大相关,可是他的殷周制度论,大家要是看过的话,便可看出这是他在清末民初之际,在社会大变动之际,他所受的感觉的一种反应,绝不是与时代没有关系的。他认为殷周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是不是最大的变化,现在的考古学家提出疑问,可是,我们要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却反映了他对时代的敏感。
王国维的自杀,也是由于他对时代的敏感。他的敏感,使他看到他所处的社会的巨大变化,所以他又注意到历史上的有没有最大的变化,变化在那里,这就是他的殷周制度论的真正背景。表面上,他是研究甲骨文,好像和时代没有联系,而事实上,他对时代却有极大的敏感。
就是其他近代的中国历史学者的作品,比如钱穆先生、陈寅恪先生,他们选择的题目,跟他们的对时代的乐观、悲观、希望、失望,以至跟他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Mazzinini说,看一部史书的头二十页,便可看出一个史学家的面目,我想这不是夸张的话除非他是抄来的,否则,只要经过史家自己思考过的、经过创造的真正好的作品,这是可以看出来的。
另一方面,正因为史学上主观因素的重要,史家也特别重要,因此他自己特别应该自律,不要随便放笔乱写。放笔乱写的结果,影响可以是很坏的。所以章学诚特别提倡史德,今天的史德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人而异,不过,至少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有人说历史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看你如何给她打扮,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历史是活人对死人开的玩笑。史料那么多,你要建立任何理论都可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今天因时间的关系,我想不多谈了。
最后的结论,就是史学跟史学家是分不开的。而史学、史家同时又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应该强调这种关系。
史家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在今天,我希望大家多做综合的工作。我并非说具体的分析工作不重要,而是综合工作现在尤为迫切需要。我们不要以为,对一个时代写了二十篇、三十篇的考证论文,就可以综合那个时代,这是错误的。因为考证题目是做不完的,并且也永远可以再做过。所以,这两种工作并不属于同一层次。
如果说我在每个方面都做过研究,我的历史综合就一定比别人可靠,这也不见得是“天经地义”,还要看你综合的才能如何。从前蒋廷黻先生在清华时说过,有位同事会背全部汉书,但是并不懂得汉代的历史,这句话也许说得过火了,不过里面却包含着值得思考的问题。
甚至没有在学院里工作的人,一样可以成为史学家。没有经过学院式的、繁琐考证训练的人,如果自修得法一样可以写出好的史书,这在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并不是我在这里乱说话。有时候,你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太钻到里面去了,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在外面看,也许会更清楚。
总而言之,我以为史学工作是今天第一要务。我说第一要务,当然本身便是一种偏见,在哲学家如在座的唐君毅先生看来,也许哲学是第一要务,心理学家则认为心理学才是第一要务。不过,我是从史学的立场上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学院里面和社会上的史学家都能为史学综合工作而努力。因为历史对今天还是十分有用的,即所谓“古为今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多注意历史问题,不要认为历史过去了的。过去与现在,这我刚才说过,是很难区分的,我这里讲完了,是不是过去了呢?还是没有完全过去?当然我是希望还没有过去,那么,历史还值得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