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 4月28日
每星期我和渡边浩总是有一回共进午餐,品评时下学术与人物,交换有无。两个东方人的共同观感是:美国的汉学轻灵有余,厚重则不足。

上一世纪,欧美学者经常假道日本汉学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特征已经是学术界的常识了。而在我问学的过程中,有几位日本学者在心目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容值一志。
第一位便是岛田虔次(1917—2000)。1982年的夏天,缘陈荣捷前辈的推荐,我得以参加在夏威夷举办的“朱子会议”。当时日本的代表团阵容坚强,例如:东京大学的山井涌(1920—1990)、沟口雄三(1932—2010),日后都变成忘年之交,容后再叙。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京都大学的岛田先生。此翁在国际汉学界久享清誉,向来罕见露脸会议,因此一出席便惹起些微骚动。
因为他曾在大陆读过中学,因此,中文口语相当流利,颇便交谈。岛田为人温文儒雅,对后进亲切有加。记得在几次会谈中,他毫不保留地推崇余老师的学问,允为当代中国学人的祭酒;即使他与余老师在个别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举个例,“文字狱”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二位便有不同的估量。他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意在与余先生当面切磋,拟如朱子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可是余老师日常作息,属于晏起一类;几日下来,二位竟无缘会面,经小辈奔走其间,方才促成了中日“朱陆之会”的情谊。
日后(1988),岛田先生曾到新竹清华大学给予一系列的演讲。有回刚好我也到清华上课,碰巧落脚同一学舍。晚上骤雨,远处传来阵阵的闷雷,岛田教授和她夫人衣衫微乱,匆匆从住房冲出来,问我是否打仗了?经我解释后,方才释然,满脸尴尬。此一唐突的反应,不知是否和他在战时经验有关?该时颇为纳闷。后来仍有鱼雁往返,向其请益。晚年他身体欠佳,1997年,以耄耋之龄荣授日本学士院院士,很是替他高兴;虽说实至名归,却是迟来的荣誉。按日本学士院院士乃依科目逐一递补,非随时得选。毋怪后生的田仲一成(1932— )竟以自己“七十少院士”自豪。
在日本学界,东大和京大乃是人尽皆知的劲敌,长期两相抗衡,人文领域自不例外。该时岛田先生被视为京都学派的掌旗者,沟口先生则是东大阵营的佼佼者。他们的学风从各自的代表作,得略窥一二。岛田的成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 1949,改訂版 1970),以理念分析见长,驰誉学界;沟口则擅长以社会、经济背景,衬托思想的流变,他的名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 1980)即是例证。他的思路显然与岛田针锋相对。而后,沟口一再强调应把研究中国当作一种别有特色的方法(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显然带有另辟蹊径的用心。
1984年,新竹清华大学举办“中国思想史会议”,日本方面除了沟口,另外以阐发“气的哲学”知名的山井涌先生等均来与会,遂愈有机会与其多接触。尤其在我研究孔庙文化的过程中,倘有成著,便呈请二位先生赐教,他们也投桃报李回赠彼此的新作,毫不介意日本书籍的昂贵。有天,沟口回函,嘉许孔庙课题意义非凡;却为日本学人所忽略,很不可思议。可见他对后辈从不吝惜予以鼓励。有次,他来新竹清华大学客座。陪他到街上闲逛,发现他逢庙必拜,十分虔诚,与他平时论学的理性执着,截然两样。据说,有回上台北宴会,碰到日本方面人员责难他既为国立东大的教授,应属“公务人员”,到此地来讲学,为何事先没通报?惹得他十分不悦。逢假,返回日本,他竟到外务省拍桌子,其对学术独立的坚持盖如是。在日本学界,他亦是以特立独行著称。
我担任史语所所长时,田仲一成前来洽谈与“东洋文库”之间合作的事宜,相谈甚欢。田仲先生一望似乡下士绅,居中他提到当选院士已年近古稀(七十)。我稍显讶异,他遂解说平均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多必须到八十左右,不啻等于中国科举的“五十少进士”了。之后承蒙他赐阅不少中文的译作,才知道他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权威,以结合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著称,研究取径独树一帜,甚有建树,在日本研究古典中国文学举足轻重。
在哈佛求学的期间,结识友人——渡边浩(1946— )。他适获日本基金会的奖助,前来从事两年的研究;虽说他已是东大助教授,我才是博士生,因一见如故,常相往来。每星期我们总是有一回共进午餐,品评时下学术与人物,交换有无。两个东方人的共同观感是:美国的汉学轻灵有余,厚实则不足。
美国结业之后,造访东京,甚受渡边先生款待。东大教授薪资有限,他竟不惜破费,招待我去银座享受高档的怀石料理,让我吃得心惊胆跳,惴惴不安。完了,二次会又去小乐坊倾听法国香颂,盖渡边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渡边先生还曾带我至家里品尝夫人亲手做的鹿儿岛料理,令我受宠若惊。鹿儿岛料理有点像台菜,焖煮的东西居多,也是人生另番的“美味关系”。
1984年,我在台北参预会议筹办,原有邀约渡边先生前来共襄盛举,但大会复邀了当时声名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 ),让渡边一改初衷,遂来函婉拒与会。原来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甚不以为然,竟似全为西方资本主义张目。我自然是尊重他于学术一丝不苟的坚持。
不久,获知他接任恩师丸山真男(1914—1996)的讲座。案,丸山真男乃是二次战后,日本最受瞩目的人文社会学者,地位崇隆无比。有趣的是,渡边的贡献却是以解构、修正丸山的假说而大获盛名。之后,他一路晋升东大法学院院长、副校长,又展现了他行政方面的长才。有回,再次和他在银座用餐,该食堂以天妇罗远近驰名。店老板获悉渡边乃东大名教授,从头到尾陪侍,极尽礼数。东大学者的魅力,于是充分体会。
2017年他受邀到史语所担任“傅斯年讲座”,复发生一件趣事。讲演之前,我跟他提及当今日本史学泰斗斯波义信(1930— ),在2003年给完“傅斯年讲座”,返日不久,随即膺选学士院院士,他也有可能步其后履。渡边断然以英语回答:“Absolutely not !”(绝对不可能!)有幸我一语中的,事实是渡边回去不到一星期,日本友人就电传了他当选学士院院士的捷报。斯波、渡边两代学人前后辉映,不啻为学坛佳话。
初次和夫马进(1948— )教授见面,是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庆祝成立六周年的纪念会。我虽久闻其大名,却从未谋面。席间,夫马先生告诉我,他早就认识我了,令我非常讶异。原来他的业师刚好是岛田虔次。有次他拟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和岛田辞别;没想到他老师一转身,取了一本小册子:《哈佛琐记》,嘱他临行前参阅,因此他便知道无名的我。由于他在明清史,声誉卓著,属于直言无碍型的学者。之后我便邀请他担任史语所的学术咨询委员。有次在每两年一度的学咨会中,有两位美国学者侃侃建言,夫马闭目养神,状似睡着,突然醒来发言,迳谓我们应该多多吸收日本汉学的成果才是,气氛突然异常凝重,颇是尴尬。
后来我便从善如流,在所长任内最后一年,敦请他与渡边浩教授担任年度的“傅斯年讲座”,以增进对日本学术的了解。两次系列讲座,果不失所望,见解新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听者受益良多。
要之,夫马先生勇于开拓新领域,具有高度的原创力。二十年前攸关“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即一新学界耳目。这回朝鲜燕行使、通信使的探讨,贯穿东亚文化区的研究,自是不意外。有趣的是,夫马此番致赠我的礼物仍是他的《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2016版)。其实,之前他已经致赠过我一册(2015版),唯一不同的是封面上多了一条书签,赫然印着“德川赏”,这乃是日本史学会首回奖赏中国史的著作,委实为殊荣。但夫马私下偶有感发,目下日本汉学青黄不接,难以维持往日荣景。我对己方也有同样的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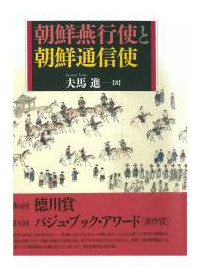
夫马进《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
哲学方面,除了前辈山井涌,我只认识吾妻重二(1956— )一人。1995年,我以傅尔布莱特(Fulbright)资深学人身分,受邀至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刚好遇到吾妻夫妇也在普大停留。他曾到北大问学冯友兰(1895—1990),算是冯门弟子吧!他的专业是宋明理学和日本儒学,思路清晰,行文严谨;撇开己身的著述之外,也日译了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自传》,其对先师的敬重若此;故获授冯友兰学术研究奖。后来接续又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的典籍,若《朱子语类》(部分)、朱子《家礼》、甚至是新儒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这种扎实的功夫,非有极娴熟的中文底子绝难成事,令人佩服万分。吾妻也是胸前挂满了勋章,得奖连连的学者,例如“日本中国学会赏”。
有回到关西大学讲演,好友吾妻明了我贪吃日本食物,参观完祇园之后,遂前去一家预约许久的小馆,品尝京都料理,中有一道鲜烹小鱼,美味可口,唇齿留香,至今回味,仍垂涎三尺呢!概可谓为“理性与感性”之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