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各地山林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的不同地位,造成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差异。无税山产的确认以契约为主要证据,而有税山林的鱼鳞山册,以及在册书手中掌握的私册,也构成了纠纷和诉讼中主要的证据。浙江省龙泉和建德两县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因此,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对两地山林的确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原来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以及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都遭遇了挑战,国家与山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关键词:山林所有权、确权、契约、册书
一、 山林所有权法律的变迁
林业史对中国历史上山林的所有权,常常只是笼统地将其定性为“官有林和私有林”、“朝廷和各级官府占有”、“私人占有”或“地主阶级所有制”、“农民阶级所有制”等。[1]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山林所有权的观念和实际占有的状况;也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区域差异。唐长孺依据历史文献,梳理了山林川泽从国有(天子所有)到被迫承认私人占有的过程。他指出:山林川泽在古代一向不承认私人有占领的权利。……在中国似乎维持山泽公有更久,直到出现了国家以后,便算作天子所有,私家还不能占领。……随着皇权的消涨与禁令的宽严,对于山泽的控制虽不能常常十分严格,但山泽王有的法律依据却始终保存。根据他的研究,南朝刘宋时期,羊希立法承认私人(主要是豪强、品官)对山泽的占有。这是在山泽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试图对豪强大族以及山泽之利进行管辖的一种努力。[2]但是,唐长孺也证明了这些限制和管理都是不成功的。
唐宋以后封禁或弛禁山泽的政令,所针对的主要是皇陵、园囿、名山等一些特殊的山林,它们被认为是“国有”或皇家专有,设专门的官员管理。但对于其他广大的山林地,国家并没有常态化的管理机制。与田土很早就因为赋税而进行了清丈,并建立起砧基簿、鱼鳞册等官方档案相比,山林的赋税记录相对较少。因此,在漫长的帝制时期,有大量的森林都处于法理上“国有”(天子所有)和事实上“失管”的状态。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明清时期民间在山林开发的过程中,自发以契约的方式形成林业的产权市场和经营秩序,即林产的占有、转移和买卖都仅依靠契约为凭据。这在清水江等林区的研究中,已经一再被证明和强调了。依靠近20年来在该地发现的大批清代林业契约,张应强、梁聪、罗洪洋等人,对这一地区的林业开发、经营习惯和规则,以及社会组织、文化形态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3]其中梁聪和罗洪洋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梁聪对文斗苗寨契约的分析,特别利用了“法秩序”的概念[4],分析林业契约在一个苗寨社会中的作用,也探讨了契约所代表的“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明清政府和法律对于山林的干预和“权利”保护都是非常薄弱的。《大清律例》中涉及平民的山产林木的法律,仅有“盗卖田宅”条下对盗卖坟山、告争坟山的规定,以及“弃毁器物稼穑”条下对“毁伐林木”的量刑等。特别是《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凡民人告争坟山”例,虽然只针对坟山,但在很多山林诉讼的理断中都被援引。也有很多山林纠纷为了能与法律相合,当事人会以是否在山上有自己祖先的坟茔作为重要依据,甚至多有毁坏、涂改墓碑的控诉。薛允升特别说明:“此等案件南省最多,与北省情形大不相同。”[5]龙泉司法档案中“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八日金林养等为控吴礼顺势欺占砍越界混争事呈状”中就有“界内又有身家坟茔赤凿”的申述。[6]又如,“光绪三十二年洪大猷与沈陈养互争山业案”,两造供词中均强调山产内有自家坟茔:据洪大猷供:“监生坟茔有几十穴。据沈陈养供”““(山里他无坟茔,就是小的墓多。”[7]不论法律是否承认、不论是否有契约对山界进行过描述,在纠纷诉讼中,坟茔总是会作为证据而被强调。这种“籍坟占山”的观念和行为在乡民中是普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告争坟山”例在承认近年山林的买卖转移以印契为凭的同时,还否定了远年契约的证据效力,而是诉诸于官方档案,即“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换言之,山林只有开发为山地纳粮升科之后,才能获得官方的认定和保障。晚清新政,清廷设立农工商局,并屡屡颁布各种诏令,振兴林业作为一种求治之道进入各级官员的视野。山林地的开荒植种和所有权确认,也开始成为一些地方官关注的事务。光绪年间陕甘、福建等地的官员在劝民种树的各项规定中,都提出过所有权保护的问题。例如《福州府程听彝太守劝民种树利益章程》中就说:“九、民间契管山场,听其自种。如无主官荒,有能开种各项树木者,准其呈县立案,以杜争端。十、有主荒地,自此次开种后,定以五年为限,勒令本主随时种植。如五年后尚未种植者,即以无主论,听凭他人开种管业,旧时地主不得出而阻挠。”[8]这个章程,一方面承认了原来民间自发形成的、以契约管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荒山官有”的理念,并鼓励人们开垦荒山,以到县“立案”的方式获得林地所有权。同样的章程在陕甘等地也有颁布。但我们还并不清楚它们在晚清的施行效果。

民国初建,无主荒地、荒山的国有化成为最早宣布的法令之一。民国元年(1912),农林部制定的林政方针里就说:“凡国内山林,除已属民有者由民间自营并责成地方官监督保护外,其余均定为国有,由部直接管理,仍仰各该管地方就近保护,严禁私伐。”[9] 1914年11月《森林法》颁布,确认无主森林均编为国有林。民国4年(1915)6月30日农商部颁布了《森林法施行细则》,第一、二条也规定公有或私有森林之所有权之变更,均须于三个月内逐级上报政府。[10]这些法令在承认已经存在的、有确切证明(主要是契约证明)的私有山林的前提下,将无主山林、林地都划归国有。最关键的改变是,这在法律上中止了过去民众通过垦植开发,纳粮升科,自动占有山林,获得山林所有权的做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森林国有化进一步加深。1931年5月《实业部管理国有林共有林暂行规则》停止了国有林、公有林的发放。1945年的《森林法》继承了北洋时期《森林法》确定国有林的基本方针,并且规定,国家认为必要时,可以给予补偿金的方式征收公有林和私有林为国有,等等。根据这些法律,国民政府对森林所有权的确认,仅限于民国之前有契约登记的林地;对森林他项权利的确认,则限于承领执照等官方证书,承领荒山不等于获得该荒山林地所有权。直到1948年2月28日农林部修正公布《森林法施行细则》,才承诺荒山荒地造林完竣后,由地政机关依法发给土地所有权状。[11]
民国时期林业国有化的趋势,以往林业史学者也有所论及。戴丽萍认为,近现代林权制度变迁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林权供给主体的利益(国家或政党)在林权制度变迁过程中居于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而林权需求主体的利益在林权制度变迁中则相对居于次要地位,但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有上升的趋势。总体而言,近现代中国林权制度变迁始终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12]中国近代的林权法律是一个由国家强制推行的制度,并且在制定过程中甚少考虑林区原有的习惯和民众利益。但它们却对传统林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与以往同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梳理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颁布不同,本文将把注意力转移到传统林区山产确权方式的变化上。一方面,国家确认国有林的行为以及提倡开荒造林、鼓励承领荒山的法律和运动,激发了这些林区民众新的“占山”行为,从而对旧有的山林产权和经营秩序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国家加强对契税和山林所有权确认的控制,也开启了林权凭证从私契到官方登记、官颁证书的转变过程。这两方面的变化,不仅是传统“管业”概念向近代产权概念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例证,同时也展现出现代国家林政在不同的林区产权传统中的初步实践。本文将利用民国时期的浙江地方档案资料,从山区民众的行动和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变化的过程,探讨这些法律和制度实践对于林业秩序和山区社会的实际影响。
二、无税之山的纠纷和确权
民国年间的多项调查都强调,丽水众山无山税,没有官方的山产档案可供稽查,相关纠纷只能依靠契约作为证据。
1920年植物学家胡先骕到龙泉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
九月二十七日午往晤赖丰煦知事少春。晚,赖君招饮。席次谈及县中状况,知米食不足者约二成。而竹木出产,年逾百数十万金。此间山林与山田皆无税。盖在明初朱太祖以刘诚意伯故,免处州全境山税。清季与民国皆仍其旧也。亦以此故,至官厅无存案可稽,诉讼遂极夥,且十九皆须上诉至三审始止云。[13]
20世纪20年代《浙江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称:
遂昌县民间买卖山场先由卖主检出源流旧契,照其所载经界四至,订立卖契连同源流旧契付与买主管业。买主并不问其山地之字号、亩数及粮额。契上亦不载明前项字样,惟记载某某山场一处,以及东西南北界至,出卖于某某永远照契管业而已。倘遇山地毗连经界之讼争,如一造提出源流旧契及买契,所载界至与系争山场界至相符,彼造则俯首无词,并不主张以字号亩数及粮额为凭而加以攻击也。按前项习惯系遂昌县公署程、温会员所报告。据称遂昌山粮究系何年截止,年湮代远,无卷可稽详考。前清光绪年间,实征堂簿内则载有山额永不加赋之语,核诸全县民间户册仅有田地塘之粮额,亦无山粮之记载,故民间买卖山场向不以推收粮额及山地字号为凭也。又是项习惯不独遂昌一县为然,即旧处属十县亦一律相同云。[14]
李盛唐在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报告中也说:“丽邑民田,可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山、塘现均无税,并入田地内科征”[15]概言之,龙泉县所在的原处州府山场因为没有税粮,在官方并无登记,因此山场本身并没有字号,也没有官方档案可以查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山林诉讼都依赖私人间的契约,作为确权的凭证。这是山林诉讼难以决断的重要原因。
(一)凭契管业与据契判决
民国年间,历任政府进行了多次不动产登记,如浙江军政府在民国2年(1913)颁布不动产登记修正案[16],民国11年(1922)北洋政府颁布的《不动产登记条例》[17],民国32年(1943)后,龙泉开始推行土地测量和强制性的登记;但这些法规和行动或者因为依赖民众自动申报因而不能有效执行,或者只限于土地房产而不及山林。因此,整个民国时期龙泉的山林仍然没有统一的官方登记。除了个别官山承领和山主申报,由政府发给执照外,山林各项权利的证明主要仍然依赖各类契约,司法机关对山产、林木诉讼的判决,也以契约为主要证据。
司法机关以契约为证据审理山林案件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验证契约本身的真伪;二是实地勘验对比契约的记载与争执山场、林木的实际位置是否相合。以“民国八年张元兴等控叶樟护等盗砍坟木案”[18]为例。该案经龙泉县公署、浙江永嘉地方审判厅和浙江第一高等审判分厅三审判决。永嘉地方审判厅和浙江第一高等审判分厅的判决理由,都主要围绕双方契约进行陈述:
审究该山之所有权应归谁属,尤当以两造之凭证孰系确凿为准。查被控诉人提出周仁盛买契在前清时曾经投税,盖有官印,而契载四至与第一审堪图丝毫不爽,并于山内葬有伊祖张承翼墓,其墓碑所刊四至与契载又属相符。证据确凿,毫无疑问。至控诉人提出张姓宗谱载有张昭墓图,指称张昭葬在系争坟山之西,并称张昭为宋时人,然提出叶春茂之卖契却在康熙五十七年,是葬坟在宋而买地在清,此中情弊已难索解。本厅查阅该卖契在前清时又未遵章投税,则该卖契之本身究否足凭,尚滋疑窦。[19]
这份判决理由,既强调了原告(即被上诉人)契约的真伪(其中清代已经税契是重要的证明),也论证了契约和实地勘验之间是否吻合的问题。被告的契约则因为无法和葬坟的年代相匹配,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而且契约所载四至范围与查勘情况不符,因此做出驳诉的判决。当然,契约在产权诉讼中的证明作用并不像这个案例的判决所展示的这样简单,由于传统契约本身的问题和理讼的性质,只有部分纠纷能够完全凭契约裁断产权。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20]
在山林确权的问题上,山林契约不仅和田土契约一样存在着伪契和上手契不完整的问题,而且契约对于山林的定义和描述方式也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龙泉的诉状和契约中对于山产的界定和描述,都是以地名、土名和四至构成的,无字号,也没有亩数。所谓“本县山场,向以土名片段四至为重,绝不记载亩分,全县同此习惯,不仅一地一姓为然”。[21]其中,土名又有大土名和小土名的分别,大土名中的山林可以分属于数个小土名。大小各片山林的东南西北四至几乎是划定山场范围的唯一标准,但四至一般都只以地形的自然形态,如山岗、分水岭、巨石、溪流为界,是相当粗略的。因此,契约对于山林界址范围的描述本身,常常成为争讼的焦点。民国10年(1921)叶水根与叶有绍因山产争讼。原告叶水根以嘉庆年间的买契以及和息约的草稿为据。被告叶有绍则提出有乾隆年间“投税之印契”,以及民国3年(1914)“山皮”买卖的契约。[22]被告攻击原告之契,所载土名与所争之山不是同一处山产。原告叶水根继而反击,称被告所提供的民国3年的契约“立字民国三年,直至本年始行投税,显系临讼捏造,倒填年月,不问可知。”而且,“民间置买产业,入手契之土名界址必根据于上手契而来,以证明其权原真实,莫不皆然。查叶有绍所呈乾隆四十九年之契及民国三年之契,土名界址,南辕北辙,判若天壤”。[23]被告所提供的上手契和卖契记载的土名、界址也都不相同,难以认为是同一处山场的上手源流老契。最后,该案以亲族调解,两造和息结案。
此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论辩相当典型,即两造虽然都有契约作为凭证,但这些契约证据都有瑕疵,各件契约(包括历次买卖契约、分家书、租佃契约、出拚契约或者合股合同等)中描述的山产土名、四至各不相同,无法证明这些契约是同一处山林的证明文件。回到契约的生产过程,尽管在签订契约时,有“必照源流老契土名界至填写”的习惯,但山林的界址在开发、买卖、分家析产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传统契约格式中以描述四至的方式定义山场,无法记录这个复杂和长期的变动过程。有关的纠纷和诉讼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层出不穷。
“民国三十五年曾贤谦等与李振汉确认山场杉木所有权案”所涉山林原为曾姓兄弟五人所有,后其中一部分被一人出卖于李振汉。从两造的言词辩论和状词可知,虽然两造都有契约、宗谱等为证据,但前代数件契约所记载的土名、四至都不完全相同,契约所记与当时人们口头上称呼的土名、四至也不能吻合。被告李振汉的辩诉中就说:
原告呈崇祯二年王德政卖契土名为白(石玄)路后,与其状称土名白石玄口已不相符,而系争山为土名白石玄底外竹山安着,又与原告之契载状称均不相符。又其契载四至为东至岗顶,南至梅树湾,西至坑,北至大溪为界,与其庭供系争山四至为东至横岗、南至湾,西至小坑,北至火路大岗直下坑为界,亦两不相符。足见该契对其起诉原因不能为相当之证明。[24]
这类在状词或言词辩论中的语言,当然只是一面之词,但其中所反映的契约对山场的描述与状词、口述之间的差异,却是常见的事实。从法院的判决来看,曾贤谦要求确认所有权的请求也被认为因为契据不足证明,而被驳回。[25]最后龙泉县法院不得不以调查人员的主观推断,对山界的进行了重新划定。
上述案件都与山林契约中对山产的定义描述方式有关。由于契约的书写格式,它对山林的描述、定义并不严密,也不统一。在民国22年(1933)测丈张雨亭山场案的一份查勘报告中,测勘人员曾写道:“又张姓受买各该山场,其卖契所载之四至,均系依据界址形势、俗称,详载于契,其字句冗长衍蔓,非目睹该山形状者,几不解所载是何意。”[26]这恐怕不仅是龙泉的情况,而是多数山区社会山林契约的共同特点。在山产木业纠纷中,即便有充分的契约证据,这些契约也必须回到山林现场,实地查勘山界,查访当事人的村邻、亲戚,以对契约中出现的山名、界址,进行实地的指认,才能被法官所理解和判断,甚或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抛离原有契约,对山界重新划定。
(二)“傍田立名”与田土的鱼鳞册号在山林确权中的作用
尽管在龙泉山林本身无税额、无档案记载,契约构成了山林所有权保护和诉讼判决的主要依据,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晚清乃至民国的诉讼判决中,看到司法机构对于田赋档案证据的依赖。
龙泉档案“宣统元年郭王辉等控叶大炎等涎谋凑锦案”[27],是一起两村郭姓族人之间的山林族产纠纷。原被两造所呈交的契约只记载了某几次的交易,无法依据这些契约追踪山产自明代至清末400多年的管业、买卖过程,也就无法确定它在清末的权利归属。民国2年(1913)二月二十八日,浙江省第十一地方法院判决文中说,“两造所呈契据均无何等价值,难以即凭契断案。”判决书中说:
讯得两造所争之业,既无别项确实证据,自应即以官册为凭,如官册原文之名为车盘坑族太祖,即为车盘坑族原来之业。如官册原文之名为地畲村族太祖,即为地畲村族原来之业。但官册只载既垦之田,并无载未垦之山。本院因是推定,以自己之山垦田为原则,买他人之山垦田为例外。如他人无确凿之反对证据,则田为谁家原丈,即推定田旁之山为谁家之业。至原丈后,田有出入,当仍以契据为凭,不在此例。[28]

这份判决书认为,不完整的或难以判断真伪的契约,无法作为裁判的依据。可以依据的是所谓的“官册”,也就是官府对田土的登记,根据田土的权属来确定它们邻近山林的归属。在民间似乎也有相似的说法。“民国十八年吴继德与李亦梅山业纠葛等案”[29],被告人在辩诉词中说,根据当地习惯,契约中山名、四至的命名方法,也和附近田土的登记字号、名称有关:
山业应凭源流契据。乞察龙泉习惯买卖山业必照源流老契土名界至填写,方为有效。辩诉人契管之山均有源流老契为据。阅原告人状称土名圳古后,究竟从前有无此种名称。假如有此种名称,应照上手源流老契填注,方为证实,无则捏造矣。查龙泉山场之土名向无册号,傍田立名,田名甲者,田上之山名亦为甲。此为成立山契缘起一定之方式。辩诉人契管山场以下之田均名窑上地,与山相符,并无圳古后土名之名称(有必字号官册可查)。[30]
但被告所称的这一“习惯”,却并没有被法院所认可。判决理由中说:“虽该被告攻击原告所执系争山场契据,其上手契与黄陈宝徐承发出卖之契据土名四至,两有异同,此点已由本院票传黄陈宝徐承发到案讯明……即核与本院勘验时所得情形,大致亦互相吻合。”[31]被告人指责原告契约中的土名、四至名与上手契不同,且在官册中无据可查的。龙泉地方法院的做法是票传立契人(也就是卖主)到案质询,证明契约所描述的山场四至究竟对应着实际山场中的哪一处。
以田土“官册”作为附近山林所有权的参考证据,显然有很多缺陷。在长期的开发管业过程中,经过多次的产业转移,毗邻的山林和田土属于不同业主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而且由于民间田土买卖,存在很多“私推”的情况,田土的实际管业并不能在“官册”上得到反映,因此由田土的所有情况推定附近山林的所有权属,也不可能准确。但在上述案件中,司法机构和当地民众在为山林确权时,的确有依赖附近田土赋税登记档案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反映出山林契约本身在确定山林权利、界址上存在的缺陷。
(三)民国契税与登记对山林产权秩序的影响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时期龙泉山林的产权证明仍以契约为主要依据,因此,对于山林产权秩序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契税和验契。民国元年浙江省军政府提出契约登记的要求。最迟在民国2年(1913),浙江各县就已经设立了契约登记所。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的山产诉讼中,都出现了与契约登记的相关内容。
“民国二年张仁钱等与张德财等互争山业案”[32],张仁钱在状纸中说,宣统三年(1911)自己在祖遗山场上砍伐的木段,民国二年(1913)在放排运售的途中,被张德财等强盖斧印,计图抢运。在述及这些木段的所有权证明时,张仁钱等是这样表述的:木段所来自的山场“界址零清,前清契税,历管至今,毛无异议,其契据早交登记所,因证书未到,契存登记所,一时无从呈电。”[33]而张德财一方随即宣称,张仁钱(田)等人不过是他们的山佃,这些山场是自己的祖先在清道光年间受买,“受买契据已送登记所登记。”[34]。双方都宣称拥有该块山场的契约,并且双方的契约都正在“登记所”进行登记,等候政府发放“证书”。县知事令双方向登记所领回契约呈阅,再行核办。根据此后县知事的历次批词,双方的契约均无法证明对山场的所有权。因为张仁钱一方山场买卖的正契遗失,而只有之前两次出拚的拚批。张德财等虽然持有乾隆年间的一张买卖契和出当反赎契,却缺乏能够证明将山场出领给张仁钱的领契。更重要的是,双方所提交的各类契约中,山场的四至、地点的叙述,均不相同。契约的来源、与所争山场之间的契合度、可信度,也均存有疑问,甚至承发吏和法警两次调查报告的结论也完全相反。

这起山场争讼,仍然反映了前述在凭契管业的“制度”之下,山林所有权证明的困境:契约链的不完整、契约写作的不规范、白契、伪契、契约对于地方熟人社会网络和“地方知识”的依赖等等。这些问题在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山林诉讼中频繁出现。但民初的验契和契约登记要求,成为山区民众提供了争夺山产或为存有争议的山产确权的一条途径,他们纷纷将有瑕疵的契约提交登记,希图获得官府在仓促之下的一纸证明。这在短期内激发了更多的山产诉讼。民国2年(1913),龙泉县还有以“藉废(契)混争”而起的“徐永炎与章学伦互争山业案”[35]和“陈秋亭与徐世克等互争山业案”[36]等案件出现。
与龙泉相邻,同属于浙南林区的遂昌县,档案中也记录了民国初年契约登记政令下达之后的两起山产登记申请。这两份登记申请也都是以“契约遗失”为由而提起的,其中一件呈请登记的山产是在晚清争讼未决的产业。申请人显然看到了这次登记是一次“合法”占有的机会。知县的批词说明,按照民国元年的登记法令,只要将申请“榜示”一个月,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登记处就可以为这些山产进行登记、发给证书。[37]这说明当时民众对此项政策的反应是极为快速和积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可能存在有“瑕疵”的契约和山林产业来说,这种登记不啻于一个让契约和产业获得合法性的机会。
随着民国时期的验契和契税运动,在司法审判中,对稅契的要求也在严格化。“临讼投税”受到了更严厉的指责和禁止。在民国18年(1929)的一起山产纠纷的判决理由中说:
兹查本案被告人主张,系争山木为其太祖蔡玉星所受买,只能提出临讼投税之季世业远年卖契一纸,并无他项上手老契可资证明,殊难信其所持之契即为管有系争山场之证凭。且核其契载四至,又与勘图内载全山界址不符。……反之,原告主张系争山木为其所有,既呈民国十一十二年王心聪先后卖契以为入手产权之证凭,复提康熙年间季云翔夏允臣出卖之印契,以证明其上手之权源,手手衔接,源流正确,其契载四至,复与实地勘图,形势符合,自属征而有信,应认原告人之请求为有理由。[38]
这份龙泉县政府的民事判决,从契载四至与实地勘图的相符度以及契约本身的可信性两方面论证山林产权的归属。后者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契税,一是上手契的完整性。该判决后,败诉的被告针对前次判决对“临讼投税”的指责进行辩护:“窃龙泉山契,古时遗下未曾投税者多,判后临时投税者亦复不少。官厅解决契据,只研究其所持契据之真伪,并不因其临时投税之故而失其契据之效力。”[39]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但龙泉县政府在该案第二次审判的判决书中,再次强调了税契在证明山林产权上的重要性:
按现行法例,我国不动产登记办法未施行以前,现行税契允为证明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之要件。被告所提康熙年间契据,当时既不投税,即不能为取得该系争山所有权之证明,亦不能断定该契确为康熙年间所订立。[40]
这一判决理据显然与《大理院判决例》七年上字第五七六号例相违背,七年上字第五七六号例说:“税契乃是国家一定征税的方法,而非私权关系成立的要件。故不动产让与契约虽系白契,未经过印投税,苟依其他凭证,可认为真实者,法律上仍属有效”[41]。但在民国财政部门不断强调契税征收的背景下,这类判决常常出现,这不能不对民间以私契管业的做法产生影响,也使得官方产权凭证的权威性更加受到认可。
但是,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北洋还是民国时期,验契、登记的真实目的只在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上并不对所涉山产进行查勘,甚至并未对所验契约中的山产进行登记,各类官颁执照在证明山产权利时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民国七年季仙护等控季盛荣等乘阅抢据案”,该案中的一件契约证据,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季仁教出卖梨树岗契,粘有民国6年(1917)二月的补税执照和验契执照。但是在民国7年(1918)的诉讼中,却被披露说立契人季仁教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就已经去世,这张契约是是季庆堂专门伪造并到县署投稅的。[42]“民国十二年项祖适控蒋保藻山场纠葛案”,其中附有数份验契执照。这些被要求重新契税的契约,有清代“白契”,也有清代“红契”。这几件验契执照,不论对应契约交易所涉金额为多少,都只征收二角的登记费,而没有查验费。验契手续在地方的执行是徒具形式的,颁发验契执照时,并未经过真正的查验手续,以至于一些获得“验契执照”的契约,在诉讼最后却被认定为伪契。[43]
概言之,明清至于民国,龙泉山林没有官方的档案凭证,其所有权证明都以契约为基础。但契约对权利的保护并不周全,诉讼中的查勘和判决也不完全以维护和执行契约为目的。田土赋税档案有时作为附近山林的所有权证据而被参考。民国政府出于财政目的的验契、契税和登记,为争夺山林所有权的民众所利用,出现了很多有关的山产诉讼。一方面,判决中对契税和登记的强调,提高了各类官方证书的权威和效力,对私契管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对呈请登记、查验的契约进行调查核实,山林契约在确定产权、定纷止争上的瑕疵和局限,并未因之而改变。
三、“鱼鳞山册”、官产承领与山林纠纷
与上述浙南山区依靠契约为主要凭证的情况不同,浙西严州府在清代的山额即已占相当比重,大部分山林造有鱼鳞册图。但是1860—1861年,太平军两次占领严州,私人契约和保存于官府的鱼鳞册图都遭到破坏。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田、地、山、塘的赋税、交易、推收,都由乡村中的庄书、册书所把持。他们手中保存和编制的私册,成为私人契约之外,最重要的田地山林权属的证明档案。
晚清民国严州府的山林开发和所有权状况,也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当地人口大量损失、逃散,1865年戴槃任严州知府时,即招募各地棚民前来开荒。尽管他的《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主要吸引棚民下山开垦田土,但显然很多棚民到了严州之后仍然以种山为业。他们对山产的占有起初并没有契约凭证。直到民国末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才为自己垦种的山林向政府申请管业凭证。居住在麻车上庄陈村乡第10保的周土金等19人,在民国36年(1947)9月呈递申请,其中就说:
民等原籍缙云,自祖手或父手迁居建德山中,垦辟荒山。至民国廿四、五年间均已成熟,现可栽植山木及各种杂粮,理合依照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但书之规定,开列清册,报请钧府核准给发土地所有权状,并照章课税,以便完纳田赋。
根据他们开列的山产清单,每人名下有2—6处山产,这些山多则40余亩,少则1亩,均已有土名、字号。换言之,在报请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之前,应该已经在庄册那里有过登记。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到官府登记。直到新土地法颁布,承认开垦者的所有权之后,才到政府申请土地所有权状。[44]
在太平天国之乱后,除了上述一部分外来的棚民占有开垦了大量的山林之外,还经历了当地人回乡收回或者霸占山林的过程。1949年之后的调查和档案经常谴责原来的地主通过伪造契约或绘制鱼鳞图册,占有山林。如《建德县山鹤乡山林情况调查》:
山鹤乡为山区,山林面积较多,在全乡土地中占有很大比重。……原先这些山地本是无主的,后为地主凭藉势力勾结旧官府强行霸占,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后,逃亡地主陆续归来,伪造假契来欺骗农民,或依仗恶势力诬指农民开垦的山地地权是他的,而将这些土地从农民手中掠夺过去,再通过租佃形式来剥削农民。[45]
相邻的分水县王秉融所主持的“清山”曾被作为典型批判。
地主由对土地的兼并发展到对山林的霸占,有钱有势的人向官府“报粮认税”领取山林,有的则依靠势力“指山为界”,将大片“无主”的山林归并在自己私造的契约之内。如分水县蠡湖乡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人口特别少,许多山林无主经营。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执政时,并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众领山认税。清山局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该乡清山局即是本乡的满清拔贡王秉融任总董事,王曾任淳安县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书,父子二人总揽大权,霸占了该乡四分之一的山林。[46]
王秉融这次清山所编订的鱼鳞山册,现仍存于浙江省桐庐县档案馆。这些调查和档案证明,在山林无主或者因战乱失管的状态下,人们通过创造契约和鱼鳞册图,为山林确权,重建山林产权秩序的过程。
在上述背景下,民国年间该地发生了几次官产承领的纠纷。如前文所述,晚清民国政府均鼓励开辟荒山造林,但是由于官方林业档案的缺失,哪些山林属于“官荒”可以被承领?哪些是“有主”山林?并无统一可靠的官方记录。承领或承买“官荒”,也就成为民众占山的一种手段。
民国17年(1928),建德县东关统捐局的职员方梅庵(即方琦),以其兄弟的名义承领该县东乡杨家庄的一处“官荒山”。他在声请书中称,自己早在民国7、8年间就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这片山上开荒种植树木。这份申请经田赋征收主任查勘、绘图、定价、山邻保证等程序,上报至浙江省财政厅。省财政厅重新定价并两次要求重新绘图后,在民国17年(1928)9月9日颁发给承买执照。但到了民国19年(1930),方梅庵以`“承买官山有照,被册书串同蔡姓私收强占”,对蔡德松等人和杨家庄册书朱逊德提起呈诉,方梅庵这样指责册书的行为:
从前民间报荒,必以逃亡绝户、废弃无粮之产为限,其手续亦当由报户呈县批令该坐落地册书前往查明,确为无主者,而后丈量绘图具复,钧府据以核准承垦升科。自民三清理官产处机关成立,凡有民荒亦同官产,其处分则给以布照。前项报荒承粮之例,因抵触而废除。今册书朱于已卖官山重为处分,既不须呈侯钧府之示,又毋庸报部请照之烦,直截令蔡姓承粮。所谓目无成案,处分自由,文墨之吏,权大若此,能不骇人。[47]
但根据册书朱逊德的具呈,当方梅庵拿着省财政厅给予的执照到他那里要求晰册时,他发现在执照中所开列四至内的山产,早已有人完粮。根据之前习惯,这些已经完粮纳税,在籍册中已有登记的田土山林,就是民有私产,而非官荒。
缘杨家庄清理书向书故父承当,自民国十七年七月间父故,即由书接管。奉公守法至今无误。乃该民方仰宋(即方琦)前因省买得荒山,令书晰册,无如查得底册,该所买之山,按照来图四至,实越出范围数倍。且均系有人完粮之产,无从再晰。……此种荒山,准民间认粮,虽未奉有明令,但建德各庄习惯,为顾全国课起见,照此办理者甚多。况前知事张任时,并因提倡森林,曾有面谕,准各书照办。书故父手内晰出似亦与违法飞洒者不同。[48]
方梅庵和朱逊德的具呈都证明,在民国官产承买制度出现之前,人们获得荒山所有权的合法途径是承粮纳税。首先,业主需要向县衙提出申请,县衙责成册书进行调查,如果为无主之山,即报告县衙,由县衙出具执照,业主凭执照回到册书那里登记入册,从此开始每年交纳税赋。在这个程序中,册书本来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但是由于赋税征收也由册书把持,人们往往绕过县衙这一层级,直接在册书那里登记,即所谓册书的私推私收。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种私推私收的情况更加普遍。正如朱逊德在具呈中所说,它成为一种在国家制度之外的“习惯”。
蔡德松是这次纠纷中另一方的主要人物,他对自己的山产权利声称:
曩时张知事提倡森林,民国七八年间发贴布告,无论官荒私荒,都准农民垦植森林。至民国十四年由先父手晰收户册是实。溯民国八九年间,蒙前知事张以提倡森林为急务,明示煌煌,劝谕人民垦荒造林,因此益知注重林业,计全县四十余庄,凡开垦者无不一律众多。森林发达,国课增加,早有明效。民故父见此情形,故于十四年间,敢将上述各号山场出立认字,向庄认垦,迄今完粮已阅五年之久,其取得之产权,自系遵从本邑惯例及官厅认可之办法,与其他私晰者不同。况各号按照鱼鳞册籍,均载明系民蔡姓祖业,燹后失管,今仍由原业主认明纳税,更属恪遵理法。[49]
与方梅庵一样,他们都将之前县知事提倡整理荒山的布告,作为自己权利的来源。而且,同样他们也都声称自己早年已在开荒种植,却没有即时申请执照,将山晰入户册。所不同的是,蔡家在民国14年(1925)由庄册私登入册,他也声称这是当地的“习惯”。
在讯问记录里,其他林产占有人的回答也非常有趣,很直接地反映当时人们对于林权来历的认识。其中一名叫陈顺桃的山主,当被问及“小坞的山你有多少税”时,他回答说:“是民外婆家遗下的坟山,土名徐湾坞,计税五分,民家经管数十年了。”一名叫郑福培的山佃则说,他是仙居人,在建德为他的娘舅照料这片山和几亩地,每年娘舅会派人来一次(收租)。陈兆余则强调自己的山产“还是洪杨前管起,今呈上老册一本”。[50]在他们的观念中,祖传的山产(尤其是坟山),长期实际的占有和管理以及承粮登记等等,仍然是林产权利最重要的证据。
方梅庵作为一名外来的地方公职人员,挑战当地庄册私推的“习惯”和旧有的山林占有方式,他的“武器”是民国3年(1914)7月31日颁布的《官产处分条例》。“迨民三以后迄于今,兹凡无人承粮之产,国家为收入起见,一律划在官产范围,必须经过国家处分价卖给照,方可取得产权。”[51]根据此条例,以报荒承粮获得所有权的制度,已经被新的官产承买制度所代替。正如他在呈状中说的:“对于册书职权论,民三以后,清理官产条例未奉废除。凡遇荒山荒地只有官厅处分,毋再准民间报荒升科理,今册书为蔡陈等姓晰收,而时间又明注民十四年之后,此项晰收显属与条例抵触,当然根本取消。”[52]《官产处分条例》对官产的处分分为三种形式,一变卖、二租佃、三垦荒,并且在第十八条规定“以前私垦之官荒自本条例施行后应补缴荒价,照章升科。”[53]换言之,报荒升科之前,需履行承买的环节,才能获得所有权。这在产权获得方式上是重大的变化。
在这场纠纷中,只有外来人方梅庵利用新的法律,并刻意回避原来的地方习惯。在被问及承买时为什么没有到册书那里查询时,他说:“我们查不来的。”后来,他又在清折里这样解释“查不来”的含义:“无主之产,册书利在民间收付,于官卖非其所愿,盖一公一私绝不相容者也。承买官产而曰必先查庄册,是犹夺食于虎口,……民间同一出钱,恐将乐于册书私人之拨付,又何事报官勘查缴价请照,作种种麻烦之手续乎。”[54]

正如方梅庵指责的,之前册书私晰的所谓“习惯”,不过是当地人们规避国家制度的方法。不仅该案的各方当事人在刻意回避与己不利的制度或习惯,民国17年(1928)方梅庵承买荒山的一系列程序中,负责的田赋征收主任和作为上级最终核审机关的浙江省财政厅,也都没有要求其向册书核实官荒。这种对旧习惯和旧地方制度的漠视,与民国新政权对册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套在国家之外的旧体制的恶感有关,但这种漠视并无补于清理林地所有权的目标。
政府、册书和不同的人群之间,围绕旧规旧习和新法律之间的纷争,是通过不断地竞争和磨合而得到改善的。民国25年(1936),建德林场森林学校同学会的12位成员提出承领杨家庄的另一块山林。县政府下令清理书(即前案中的册书朱德逊)详细查明这块山林的归属。这次承领申请,同样出现了与附近山主之间的纠纷。县政府即饬传朱逊德带同庄册及原图,在规定时间内到府接受讯问。[55]朱逊德的讯问笔录记录如下:
问:你管的庄有田地山塘多少?
答:二千余亩山,田千七百余亩,塘四十余亩,地约二千亩,一共六百余元正税。历年没有很大进出。
问:你管的庄有无无税山地?
答:不甚清楚。
问:你管的庄册有无鱼鳞?
答:土地陈报时,造过新册。老鱼鳞已经不齐,所有推收根据他们的户册推收。
问:现征粮的山税,照老号还是照新号?
答:老号新号都有,在三昃地,自一号至四十号均照新号,余照老号。
问:鲍吴氏的地土地陈报时曾否编过新号?
答:编过的。
问:鲍吴氏在吴锦荣等请领官荒内管有山地多少?
答:依照土名所在计算三昃,(苏州码)在龙门顶有十四亩,(苏州码)金鸡岩有二亩八分三厘,(苏州码)西坞殿二亩六分六厘六毛,(苏州码)毛竹里三亩三分三厘五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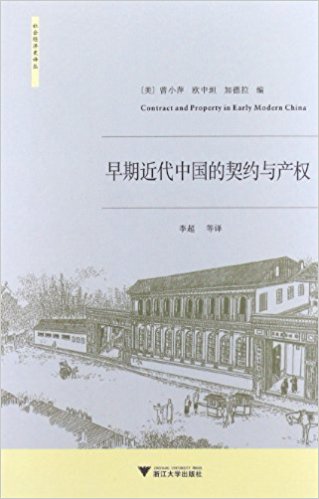
根据朱逊德的供词,册书手中的山林记录也是根据人们的开垦报税而逐步积累起来的,这在民国年间仍在继续。只不过这时候,新的法令规定,新承垦的山林,即便经查证原属无主荒山,其性质也属于“官荒”,即为国有。在这个民国末年的案例中,虽然政府本身仍没有能力对山林进行全面的清丈、建立官方的山林档案,但是通过对“册书”群体的整编和控制,政府将山林确权的最终权力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中,册书回到了中间人和执行者的角色上。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面对着国家层面上同样的林业政策和法律,浙江龙泉与建德两县林区在山林所有权获得与证明方式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其根源在于两地山林在旧有的地方赋税体系中的地位有根本的不同。建德最晚在南宋经界之后,已经对大量的山林征收赋税,并且留下了记录。《景定严州续志》中记载有1258年举行的经界法,其时即已丈得“山若桑牧之地以亩计得五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七”,超过田亩数四倍之多。[56]而在处州现存最早的明成化《处州府志》中并没有山税的专项记载,至嘉靖《浙江通志》处州官民山额数远低于官民田数的格局就已经定型。[57]清代雍正《浙江通志》记录严州府建德县,田额仅1667余顷,而山额达到了5125余顷。[58]而在同样以山区为主的处州府各县,山额的比重却小得多;龙泉县实在田1699余顷,而实在山仅为133余顷。[59]每年征收的山银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差异,造成了建德的林产确权以纳粮升科,登入鱼鳞山册、获得字号为主要方式;而龙泉的山林产权证明主要依靠私人间的契约,在契约无法确证时,参考山林附近的田土赋税档案。
对明清山林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契约和地方习惯的作用,即认为各种林业权利的来源、获得和保护是来自于并仰赖于契约的。同时也承认“国家法律在这个法秩序体系中有着保障社会稳定、肯定和维护民间规范并对民间规范进行调控改造的功能” 。[60]以往学者对清代产权的研究也强调“官府本身尽管对财产权进行确认,然而在权利的执行上无所作为,以至于人们打赢了官司只后,还要使其权利得到地方社群的承认” 。[61]龙泉和建德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林业产权秩序确立的历史过程,与国家权力的进入、赋税制度的设计和推行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赋税制度不仅是提供产权凭证那么简单,如果放在一个长时段来看,它为地方社会经济规定了一套基本的制度结构,所有权观念、习惯的演化都与这个结构的变化有关。仅就浙南和浙西这两个相邻的小区域来说,山林赋税历史传统的差异,影响到两地确权方式、纠纷形态和审理过程等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统一化的造林运动、林产国有化、契税和验契、土地陈报、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我们今天在档案中看到的大量山林产权纠纷和案件,是两地民众应对甚至利用这些新政的结果。例如,前述龙泉县民国19年(1928)的张雨亭山场案和建德县方琦承买官产案,其直接背景都是当时浙江省疾风暴雨般推行的土地陈报。这次土地陈报在各地掀起了一波确权纠纷和诉讼的浪潮,其效果在当时已经饱受批评。但由于两地山林在古代国家赋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这些新政所激发的地方反应、山林纠纷和确权方式的变化都有差异。
民国龙泉山区的山林确权纠纷和诉讼,主要是围绕着契约进行,验契和契税新政对其影响最大。但这种影响仍然与契约本身在山林确权中的弊病有关。传统的山林契约对山界的描述模式,为山林确权带来很多隐患。从契约动态的使用过程来看,确定山界的并非仅是一道道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而是人们围绕着这些地理标志物以及契据、查勘报告、判决书等,建立起来的对山林的认识。这种认识永远是动态和变化的,在认识过程中充满了各方的解释、协商和斗争。因此,尽管赋税档案在龙泉的山产纠纷中不如契约使用广泛,但人们对契税凭证等官文书和官方确认的需求一直存在。民国时期政府一系列新政相当密集地制造出了各类官方凭证,尽管它们并不是经过实地测丈的林权证书,但仍然被民众追逐和使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私契在确权中的效力。
对比龙泉县的情况,在上述建德县的林产纠纷中,并没有契约出现。在方梅庵承买官产案中,不管是试图通过新的官产承买制度而获得林产的方琦,还是以坟山、祖产、开垦有年或在册书那里已经登记等理由而声称拥有林产的人,他们都没有提出一张契约作为证据。这种情形也许是太平天国之乱后,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又经过重建的结果,却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个案,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契约为中心的产权秩序之外的另一种情形。
由于鱼鳞山册的存在和庄书册手把持山林的升科、登记和纳税、推割,他们手中的私册成为建德山林所有权证明的主要证据。战乱之后人们对山林的争夺,也主要围绕着鱼鳞山册的再造而展开。册书和它代表的地方“习惯”,成为民国林权新政推行过程中,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焦点。虽然直至民国末年也未能建立官方的山林产权档案,但新的法律挑战和否定了过去人们通过开荒升科获得山林的所有权的方式;政府通过对册书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将山林所有权的最终确认权,收归至政府的手中。
概言之,由于山林在传统时期国家赋税体系中的不同地位,造成两地确权方式的差异,并且衍生出以契约为核心和以鱼鳞山册(或私册)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山林产权证明体系的架构。民国时期国家在契税、契约管理、林地丈量和登记、林业国有化等方面的不断进取,在这两种架构下呈现不同的面貌。在民众应对、利用新的国家权威和法规的过程中,国家和民众在合力创造一种新的国家与山区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本文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资助,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13&ZD151),浙江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重大项目“从契约到土地产权状:近代浙江地权证明的习惯、诉讼与司法”(14YSXK04ZD—1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正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1]参见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33页;樊宝敏《中国林业思想与政策史(1644—2008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2页。
[2]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7页。
[3]张应强:《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罗洪洋:《清代黔东南锦屏人工林业中财产关系的法律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法学院,2003年。
[4]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为中心的研究》,第21页。
[5]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第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77页。
[6]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5页。
[7]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上册,第96—99页。
[8]《农学报》,1902年第185期,第1—3页。
[9]陈嵘:《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林业推广部1934年版,第65页。
[10]陈嵘:《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第68页。
[11]《森林法施行细则》,《浙江省政府公报》1948年第3454期,第37页。
[12]戴丽萍:《近现代中国林权制度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2009年,第46页。
[13]胡先骕:《浙江采集植物游记》,张大为等合编:《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7页。
[14]《浙江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会第二期报告》,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第4页。
[15]李盛唐:《丽水田赋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3页。
[16]《浙江公报》第21册,民国元年二月廿三日,第3页。
[17]《浙江公报》第三千六百十九号,民国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1页。(《浙江公报》的标注请统一)
[18]该案收录于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22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70—1098页。
[19]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22册,第1041—1044页。
[20]参见杜正贞《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辑。
[21]《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龙泉县卷宗土地类三号一件为关于测丈张雨亭案由》(1933年),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10/1/170/1,第125—127页。
[22]《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761,第45页。
[23]《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761,第54页。
[24]《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9181,第64页。
[25]《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9181,第127—132页。
[26]《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龙泉县卷宗土地类三号一件为关于测丈张雨亭案由》(1933年),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10/1/170/1,第125—127页。
[27]该案收录于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上册,第324—400页。
[28]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上册,第378页。
[29]相关档案保存于《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M003-01-1160、1711、4810、6171、8030、9941、14524。
[30]《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4810,第71—77页。
[31]《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4810,第35—39页。
[32]该案收录于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3册,第115—161页。
[33]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3册,第117页。
[34]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3册,第119页。
[35]该案收录于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4册,第355—416页。
[36]该案收录于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4册,第619—661页。在这个案件中,县知事也采用了与山林相邻的山田赋税粮册作为证据。“查粮亩田段字号册,内载三百七十九号后坑突,三百八十九号上攀儿。田垦于山,突上有田,田名则本山名而呼,事所常有。” 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4册,第651页。“此案判决系根据粮亩田段字号册,并非专凭承吏之勘覆。” 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4册,第657页。
[37]《民国遂昌县政府司法处档案》(1912—1949),浙江省遂昌县档案馆藏,M415/2/719。
[38]《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8351,第25—30页。
[39]《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8351,第37—42、46页。
[40]《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1912—1949),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M003/01/8351,第70—74页。
[41] 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42]该案收录于《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17册,第1—127页。
[43]该案收录于《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2辑第32册,第837—992页。
[44]《建德县田粮处关于清查粮仓存赋谷、垦荒成熟山地的升科、发所有权证等的报告、批复、训令、表报名册》(1947—1948年),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15/20/237。
[45]华东军政委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建德县山鹤乡山林情况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出版机构不详,1952年12月,第257页。
[46]华东军政委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天目山区农村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9页。
[47]《方琦为承买官山有照被册书串同蔡姓私收强占事呈请书》,《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48]《杨家庄清理书朱德逊为声明事呈》,《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49]《蔡徳松为陈述承粮造林经过请求察核排除侵害事呈》,《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50]《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问讯笔录》,《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51]《方琦为补充简明意见仰祈鉴察施行事呈》,《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52]《方琦为再行呈明事清折》,《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53]《官产处分条例》,《浙江财政月刊》1933年“现行财政法规专号”,第61—62页。
[54]《方琦为再行呈明事清折》,《建德县府办理方琦承买官产纠葛文卷》(1928—1930),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14。
[55]《建德县吴锦荣等请领官荒造林卷》(1936—1937),浙江省建德县档案馆藏,1808/7/61。
[56]方仁荣、郑瑶撰:《景定严州续志》第2卷,《宋元地方志丛书》第11册,大化书局1980年版,第14页下。
[57]薛应旂纂修:《嘉靖浙江通志》第17卷,《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4册,上海书店??年版, 第17页下—第18页上。
[58]嵇曾筠、李卫等修:《雍正浙江通志》第69卷,“田赋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24页。
[59]嵇曾筠、李卫等修:《雍正浙江通志》第70卷,“田赋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37页。
[60]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为中心的研究》,第257页。
[61]安.奥斯本:《产权、税收和国家对权利的保护》,曾小萍、欧中坦、加德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