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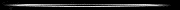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

▲彭小瑜
前言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1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
17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1596 —1665)和马比荣(1632 —1707)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 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2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汀(1800—1859)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
梅特兰(1850—1906)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国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除了实证,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观点和理论,是一个依靠“自我参照”就可以建构的运作体系。但是这样一种经验和实证的研究所提出的结论却具有很关键的理论意义。他不再以英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神秘特殊性来解释英国普通法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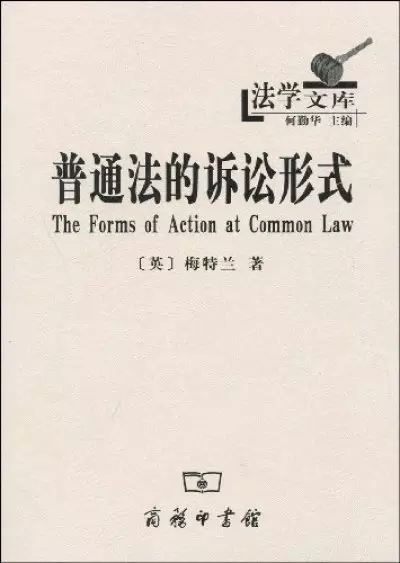
▲《普通法的诉讼形式》 梅特兰著
譬如,针对陪审团问题,他提出,从史料来看,关键的人物是亨利二世(1154—1189)。亨利推行令状的购买,其动机是基于财政和行政的需要。改革法律制度可以增加国王收入和扩大国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扩展陪审团和巡回法庭的作用,时间大体在1160年到1270年。国王的巡回法庭由四人组成,审案效率较高,容许当事人双方当庭抗辩,法官起仲裁作用。世俗律师成为专门的职业,在法国和意大利受教育的神职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下降。

▲ 陪审团制度
1215年,教会正式禁止神判法的施行,英国普通法开始使用陪审团裁决诉讼,由此发展出大陪审团起诉陪审团和裁判陪审团,成员都是当地居民,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法官的主要动机是快速判案,为国王收集金钱和财富。因为政府没有像样的监狱制度,犯罪嫌疑人经常脱逃,加快定罪速度是必要的。“重石压迫处罚”被用来“说服”当事人接受陪审团裁决不服者的胸口被压上巨石,直到他同意为止。
大约到1325年以后,嫌犯不再有拒绝陪审团裁决的权利。陪审团制度的弊病也开始出现:青年、妇女、老人、名誉高尚的初犯等受到宽大的处理,他们的定罪率大约只在35%,并形成认罪求情制度。黑社会还常常威胁陪审团成员。这些也都是现代普通法体制下常见的问题。
梅特兰的实证方法打破了对普通法的神秘崇拜,同时指出这是一个有缺陷有变化的制度,从而为英国法制的改革理清了思路。梅特兰所描述的其实是所谓“普通法文化”,其重要特点是强调司法是国家运作的重要手段,政府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平台,而是借助法律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机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保证人世间的和平。虽然梅特兰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史实考证,他的成果比起那些从日耳曼人民族性出发的著作显然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3世界历史的“正名”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世界历史”这一学科划分本身就暗示着,我们的外国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定位问题。这一名称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着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人类历史呢?如果是这样,世界历史很容易和历史哲学混淆。“外国历史”应该是更合适的学科名称。在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中,旨在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是不多见了。
但是历史哲学的思维范式依然还残留着。逻辑演绎方法的片面使用还是比较流行的,求证的规则往往有意无意替代了发现的规则。譬如说,有些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去寻找论证的材料,而不是先阅读文献,然后再提炼出研究的主题。这类常识性的问题还依然存在。
这里当然涉及世界历史研究的主客观条件的问题。图书馆的有关文献收藏情况的确是不理想的,学生的外语准备往往也不充分。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给予这些困难足够的重视,没有动用恰当的人力物力来解决这些困难呢?可能在思想上还是有点满足于历史哲学类型的世界历史研究,觉得细节和微观的问题不重要;或者觉得,不经过考据和事实的发现,单单凭借理论的推演,附带地穿插一些史实,就可以得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结论。引入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给予史学突出的理论色彩的确有助于推动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以及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事实的发现、具体问题的考据并没有矛盾。在很多情况下,深入的具有切实和建设性理论意义的历史研究恐怕难以脱离小心的求证和细心的考据。
所以,“世界历史”还是应该首先被分解为国别地区史、断代史和专门史来处理。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都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但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途径可能主要是借鉴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是热衷于构造新的世界历史体系。当然,并没有谁在热衷于构造新的体系,但是我们显然还不够重视世界历史上具体的微观问题的研究。现在大家开始重视世界历史研究对处理国际问题的借鉴作用。
我想,真正能够有益于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真相的研究应该是实证的,洞若观火地把握国际形势走向应该是以纤毫毕现的具体研究为基础的。如果连树叶的细部都看不清楚,指责他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家是否自己也在痴人说梦呢?
作为学科划分,“世界历史”还有另一个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副作用。由于世界历史被列为相当于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二级学科”,这一本来就基础薄弱的年轻学科在师资和资金的配备上明显处在不利的地位。比较合适的学科划分似乎应该是具体到地区和国别的,并且考虑某些重要的专门史,譬如古希腊罗马史、古代西亚埃及史、东欧和俄罗斯历史以及中世纪西欧史等等,似乎都应该作为“二级学科”来处理。要求外国历史研究更具体一些,学科的划分就应该更合理一些,人员和资金等资源的配备也应该更充足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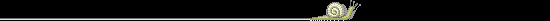
文本来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摘选自“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系列笔谈
实习编辑:翁文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