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民间文献作为“新材料”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大量民间文献被整理出版。但民间文献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或缺憾,诸如民间文献的解读不规范,调查不深入,以及缺乏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因而,民间文献研究应该有较大的历史视野,处理好区域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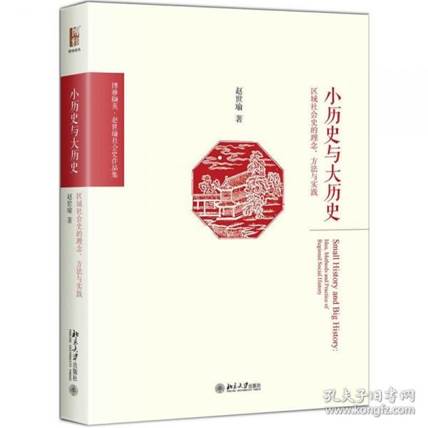
各类民间文献的挖掘、整理、出版和研究,这在全国范围内蔚为大观,而且也给了很多地方包括地方院校,申请比较高档次的科研项目,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大范围的关注。我们知道,过去无论教育部、国家社科等重大基金项目申请,都集中分布在比较好一点的学校。但近些年,很多围绕地方州县档案、契约文书、碑刻等地方文献项目的首席专家,许多是原来不大了解的地方院校的年轻学者了,这个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也是很好且难得的机会。当然如郑振满教授所言,已有一些地方文献,比如族谱、账簿,甚至包括碑刻等,都陆续出版了,但还有很多不容易出版的。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学术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无论对高校还是对学术界,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仍是主要的。但它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所以需要去很认真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及挑战。很多问题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从小的来讲,我们都知道,去很多地方搜集资料,不同地方、不同高校、不同学者的做法可能很不一样。据说,“黎平文书”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基本上是把“原始的”资料从老百姓家里弄进档案馆系统,只是照相、扫描、出版,这是一种“原生态”的方式。也有一些单位及人员收到各自的单位收藏,无论是公藏的档案馆、图书馆,还是学校建立的研究中心、资料库,当然各有各的道理。民间保护、保存的情况可能有问题,除非国家或当地政府给予大力投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些资料原来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现在这些东西被逐渐地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剥离出来了,变成学者研究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个背后可以有很多考量。
无论从技术上,还是道德上,我们应担负一定责任,在几十年前大家都没有做,近十年来呈现大规模生产的图景,我们开始注意这个东西时都还没有考虑这个后果,一下子文物贩子都知道了这个民间文献的价值。
以前,一张徽州文书卖10块钱,现在估计100块都不止,而且,盗、偷、抢、造假等等之类的情况现在开始出现,有些仿造得很逼真,包括元代的、明初的一些地方民间文献比较少,现在也有了。这类东西的大面积出现带来很多问题,扰乱了很多原有的生态系统,所以对地方民间文献,是不是还能说是一个“原生态”( 样本) ,或者“原生态”状态是否陆续被打破,我都有了一些怀疑。值得这些利用者、收集整理等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现在不思考恐怕不行了。当然这只是相对小的问题,至于大的问题,学者们都已经讲过了,我不再赘述。
刚才老师们也讲,民间文献多被视为“新材料”,所以很多不同学科的研究都依赖这些材料。新材料的出现吸引很多学科睁大眼睛来关注,不光是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包括法学做法史研究的。最近我看到一些法史方面的研究,但是做法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利用州县档案做研究,他们关注的问题跟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的有很大区别,它们有不同的视角,回答不同的学科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比如在询问这些研究者在做具体研究时,一个官司、一个诉讼、一个案子,为一块土地、坟山等涉及地产问题在打官司,甚至两个家族一打打很多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可以从传统社会打到现代社会。很多学者对于打官司的两家人及其住的地方,在那些档案里都提供了很多证据,都看的很清楚。关键是坟山在哪里? 土地在哪里? 打官司的人住在哪里? 研究者是未必去考察过的,主要根据这些档案来做判断,离开了事情发生的历史情境,我有点怀疑是否能解释清楚或者判断准确。问题的背后,当然包括刘志伟教授说的“语言”的问题。
还有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比如文献本身的问题,也就是郑振满教授他们一直在做、很多现代学者也关注的问题。这些地方民间文献,尤其是不同文类的民间文献出来之后,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或者历史文献学造成何种冲击? 因为传统历史文献学是经历了上千年的传统,形成了自己一套固定的方法和分类系统,它甚至有自己解释的脉络,甚至包括具体的记述以及记述的基础,比如刚才所说的“语言”,音韵、训诂等,都跟语言有关系,也都是跟文献学相关的,都是文献学的基础。但是,新的材料出来以后,有没有很好地系统地从具体问题出发,去讨论对传统历史文献学的冲击,它不可能不形成冲击,冲击已经造成了。但是,传统历史文献学的这套系统里面,其实基本上没有办法纳入现在发现的各类不同的地方民间文献。
其实,除了地方民间文献之外,看到更多的情况是,应该怎样理解和解读文献。我每个学期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读一些很基本的文献,有时候也被其他高校请去带他们的学生一起去读,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读到年轻人用民间文献写的文章,发现读不懂、误读,或者忽略其中信息的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像做地方历史研究的,首先接触的多半是地方志。我往往是从地方志的封面开始读起,会问学生从这一页上看出什么问题,学生们大多说不出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脑子里已经知道的那些问题去看相关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就不管了。但是从封面上的书名,加上编者、版本,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接下来就是地方志的序,逐字逐句地问,大多数学生是回答不出来的。像地方志这种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都这样,新发现的材料就更难说了。所以,我对现在的研究,常常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很多研究是在对一些非常基本的文献阅读和理解上不求甚解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经常会把看似不相干、无法与关心的问题建构起链接的东西跳跃过去了。所以,对于熟知的东西现在还不能理解和搞清楚,那些陌生的、不熟知的东西怎么办? 一是无法抛开“旧材料”,单抱着“新材料”就去打天下了; 二是对新材料不是用我们原来的那一套做法就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需要狠下功夫。
很多学者,包括刚才发言的老师们讲到怎么展望未来研究之类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敦煌文书被发现已有100多年,为什么它一经发现就被人们认为很重要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唐、五代以来、包括以唐、五代为主的历史资料太少了。但是这些资料拿出来以后,虽然重要而伟大,但它能解释唐、五代的历史吗? 它只能解释唐、五代那时的一个很小的区部的历史,比如西州的历史,不能解释整个中国或者唐朝版图内其他地方的历史。
我们还知道考古发现的汉简也很重要,很多学者做过出色的研究。但是,以居延汉简为例,它所反映的也主要是汉代居延一带的情况,即使是王朝制度,也是王朝制度在居延这个地方实行的情况,别的地方也不一定相同。当然,发现那个时代的这类材料已经很不容易了,只是用它们来说明汉代、唐代的历史,需要谨慎,需要有些限定。但是到明清以后就不同了,各种区域性的民间文献变多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区域的历史,再进一步去重构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历史。所以,区域性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讨论某一个地方,要有更大的观照。
如前面反复提到的徽州文书,包括“徽学”,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研究,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观察,虽然徽州文书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是依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叙述当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我们去找那些通史来看,有哪些重大结论是从徽州文书研究出来的? 有些重要的局部性的研究结论,但也没有被重视和写进去。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通史的书写者不重视; 二是徽州文书的研究者在研究文书时没有思考刘志伟刚才所提到的重大问题。比如,刘志伟他们做的珠三角的相关研究,没有一个名字叫“珠三角学”,也没有一个“珠三角文书”的说法。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不管是什么材料,都可以拿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去强调这是什么“学”,或者那是什么“文书”。但是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华南研究呢? 我个人认为,他们讲的这个区域的历史过程已经体现在中国历史的叙述当中了,尽管他们的研究从整体上是要比徽州文书要晚一些的。如果大家比较一下这两个区域的研究,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所以叫“什么学”,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意义上的,广告意义上的,不能当真。将其建立成为一个学科是可以的,用它来争取项目、搭建平台等,都没有问题,但要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策略。不能最终做得不好,口号也喊了,钱也花了,材料也整理出版了,但在学术的意义上却变得悄无声息了。我们有很多很多好的材料,但也要好好地把问题思考清楚,这是个大问题。
比如,我为什么说清水江文书的出版——不管是锦屏文书、黎平文书,还是以后其他别的文书的继续出版——是很震撼且有意义的呢! 虽然我没研究过黔东南,但还是会引起我整体的思考。比如,张应强以前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但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答案,就是木材流动到哪里了? 人们把木头卖到哪里去了? 用来干什么了? 我始终不大明白,买木头的这一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大家似乎认为这跟清水江及其研究没有多大关系。但恰恰要打破这种观念,清水江的木头流出去了,流到天南海北,在中国,在世界,怎么能跟我们没有关系呢? 研究那些地方只能让清水江相关研究的意义变得更重大,而不是手伸得太长。
刚才刘志伟也讲到清水江木材贸易背后的机制问题,他没有得出答案。再比如,很多学者看到材料都已经知道,在清水江木材贸易里面,徽商和晋商都参与了,但这里是不是可能有两种套路? 究竟是徽商和晋商代表的那种商业模式把清水江木材贸易拉入一个原来的传统套路里面,还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的套路? 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思考。又比如,包括刚才两位老师提到清代的3件大事和苗疆的事情,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个是这三件事是相互孤立的吗? 第二个是这三件事只是清代的事情呢,还是明代的延续? 其实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总之,清水江研究是一个研究的起步,而不是它的终点。
本文原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2期
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