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崗 道教和宗教史研究資訊 今天
我的生活閱歷並不算豐富,局限在學術圈內。由於長期求學及任教海外,又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對我學術經歷有重大影響的一些前輩大多活躍于海外,算是漢學家,我的這篇小文就用「我所相識的幾位漢學家」為題,聊一聊我在海外相識的幾位漢學家。不過,在講述他們之前,我先要追憶一位在國內給予我重要啟蒙的尊師。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有兩位前輩學者對我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按時間先後,第一位是復旦大學的章培恒師。章老師在追求學術的嚴謹方面,為我立下了的楷模。在這種治學精神的感召下,我認識到不求做出有多響亮的成就,而是踏踏實實做一些有益的研究,哪怕題目很小的考證,只要解決或甚至僅澄清了具體問題,就算是貢獻。章培恒師另一個對我的啟迪是學者也應該是性情中人,學術也有人格個性。章老師正是一位文中豪士,儘管桃李滿園、日理萬機,但我每次回滬,他都會興致勃勃地邀我吃飯,煮酒論學,而我所得益的有學問,也有人生經驗。章培恒師並非我的導師,但對我一向很好,在學術追求上給了我最重要的引領,在個人關係上也情同師徒。只是到了章老師臨終前一、兩年,由於他身體欠佳的關係,我才沒有機會見到他。2011年章老師仙逝後,門下不少弟子屬文,追述章老師的治學與為人,不必我來贅言。 2012年6月7日-9日復旦大學舉辦了紀念章培恒先生逝世一周年系列學術活動,我有幸應邀參加了作為此次系列活動重頭戲的「實證與演變:中國文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了以「明代中篇傳奇小說的傳播及其文化意義」為題的論文,得到點評者黃霖教授和其他與會學者的佳評,會後該文經過修改,收入《實證與演變:中國文學史論集》,即將出版,聊以表達對章培恒師的紀念。而章老師在學術上的啟迪,已為我在海外吸收漢學研究的豐富成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其餘幾位對我學術經歷有較大影響的學者都活躍于海外,所以是漢學家,我按結識他們時間的先後為序,來談他們對我的啟迪。這裡談的第一位漢學家同時也是另一位對我影響最大的學者,這就是我的導師余國藩先生。余老師是芝加哥大學唯一的神學院、英文系、比較文學系、東亞系及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兼聘教授,執教鞭垂四十年,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巴克(Carl Darling Buck)人文學講座傑出教授,現為巴克人文學講座傑出榮休教授,是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和臺灣中研院院士。余老師桃李滿天下。有幸的是,我是余老師門下中國大陸學生中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弟子。余老師畢生從事宗教與文學研究,在他的點撥下,我也進入了宗教與文學研究之門。余老師常說他自己精神上屬於「五四」時代,這意思是說,雖然他對宗教的研究是對「五四」反宗教的極端的修正,但他骨子裡是一個人文主義者,關注文學和宗教對人的精神解放和靈魂救贖的作用。在他2001年出版的重量級著作《重讀石頭記裡的情欲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題記獻給了為中國民主奮鬥的青年學生。其他方面,余老師是個品酒行家,他長於鋼琴,也燒得一手上佳的廣東菜。他還喜作舊體詩詞,我也偶爾湊數,和過幾首。
余國藩師對學問涉足的範圍之廣及其研究之深是令人震驚的。上文講到余老師畢生從事宗教與文學研究,而中西比較則是其學術靈魂。任職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的師兄李奭學用「兩腳跨東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來概括余老師的學問,恰到好處。予生也晚,浸淫老師學問的時間尚短,也限於才力,不能曾得老師學問之萬一,不敢涉足老師致力於的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但余老師寬廣的學術視域和敏銳的理論批判度,對我始終是個鞭策。余老師是《西遊記》研究的權威,他從宗教與文學的角度研究《西遊記》,讓我看到了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全新的解讀。2012年12月,余老師的《西遊記》四卷譯本修訂新版問世。在修訂過程中,我也一直關注老師的工作,也盡了綿薄之力。早在1993-1994年修讀余老師所開設的「《西遊記》研究」課上,我就寫了《「西遊記」:一個完整的道教內丹修煉過程》一文作為學期論文。余老師非常欣賞拙文,到處向其他學者推薦,並敦促我去發表。此文1995年發表於臺灣新竹《清華學報》,獲得較好的反響。1998年,我當時尚未畢業,蒙劉再復先生不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在劉先生主編的「文學中國叢書」裡,出版我的一部專著。余老師知道後,專門為我開設了「獨立研究」課程,以便我有時間撰寫此書。此書從道教方面對《西遊記》和《金瓶梅》等小說的研究,就是運用了余國藩師的「宗教與文學」研究的方法。書稿完成後,余老師又撥冗為我寫了序言。1999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了我的這部書《浪漫情感與宗教精神——晚明文學與文化思潮》,該書列入香港商務印書館統計的香港2003年度百部最佳書排行榜,為其中為數極少的學術類書。
我對宗教學理論的關注,以及最後投身道教研究,正是得益于芝加哥大學宗教學的學術氛圍和余國藩師的教誨。這幾年我更把主要精力放在明代道教的研究上。余老師2005 年出版的近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歷史與文本的角度》(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就對我明代道教方面的研究有直接的參考價值。不僅如此,無論是在我撰寫拙著《明代王府與道教:一個精英層的制度化護教》(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The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還是以「明代的道教和地方社會」為題申請美國學術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研究獎助的過程中,余老師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修改的建議。前者由英國的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中文譯本也已翻譯完畢,不久就能與國內讀者見面。後者獲得了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提供研究金的美國學術聯合會「2013-2014年度中國人文研究獎助」。算是向老師呈交的過得去的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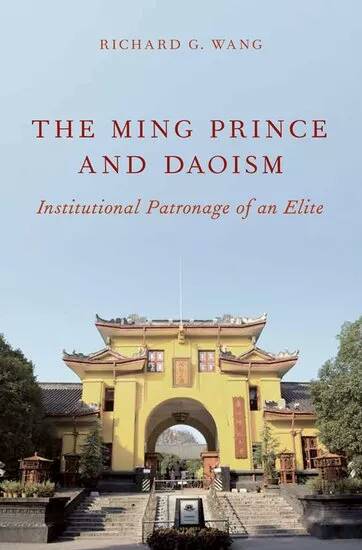
第二位我要談到的漢學家是已故陳學霖(1938-2011)先生。陳先生是宋金元明史專家,他接續了吳晗、羅香林以來的中國史學的學術脈絡,也秉承了西方漢學的批判精神和視野廣闊的特點。他是羅香林先生門下「四大金剛」中學問最厲害的,又師從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教授,得益于西方漢學中最優秀的史學傳統的薰陶。陳先生于典章、制度、禮儀、學術源流,無不網羅胸中。更重要的是,陳先生治學不拘一格,尤其對劉伯溫、鐵冠道人張中、流傳於市井間的讖謠《燒餅歌》、白蓮教、乃至月餅與抗元秘密義舉的關係,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學術界僅有的嚴肅研究,這大大投合了我喜歡「怪力亂神」的口味。我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時,就不僅搜羅了陳先生已出版的所有中英文論著,而且參考了陳先生196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論文《劉基(1311-1175):一位中國皇家軍師的雙重形象》(「Liu Chi (1311-75): The Dual Image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這些對我研究明代豔情小說中的道教向度有直接的啟迪。2012年出版的拙著《明代豔情傳奇小說:文化操作中的體裁、消費和宗教性》(The Ming Erotic Novella: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一書,就繼續參考了陳先生這方面的論著。
我與陳學霖先生的相識,則要等到我1999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但我與陳先生也並不十分熟悉。陳先生歷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明代名人傳》編纂處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及歷史系教授。余國藩師作為臺灣中研院院士,有資格提名新的院士人選。余老師曾表示,他要提名陳學霖先生為中研院院士。可見學者之間的惺惺相惜。
我去香港工作時,陳先生任中大歷史系的歷史學講座教授和系主任,並從1995年起就一直擔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的主編和編輯委員會主席。我當時仰慕陳先生的學問,但對這位大腕級的學者,不敢隨意打擾。在學校同事的社交場合,陳先生知道了我是余國藩師的學生,又從事明代文學研究。有一個偶發的機會,使我對陳先生有了更多的瞭解。當時,中大歷史系另一位明史專家朱鴻林先生在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暫時未回,而陳先生忙於多項行政事務,無暇教授本科生,歷史系的明史課程因此無人開設。而恰好我所任職的宗教系也經費不足,能否給我續約也是一個問題。陳先生就找到我,讓我在歷史系兼職,上兩門課「明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史」。雖說他請我給歷史系上課,是幫我解決了在中大的續約問題,但他卻向我表示是請我給歷史系幫忙。這更讓人由衷感激和敬佩這位簡易、隨和的謙謙君子。我2003年離開香港去美國任教。說也奇怪,以後凡有機會回香港,或參加學術會議,或由於私人事務,都能在中大校園裡邂逅陳學霖先生,總是適逢他匆忙趕去參加會議之類的時候,他見到我,總是很詫異地說「王先生!」看來,我與陳先生還有緣。
在中大歷史系工作之後,就與陳先生有了較多接觸,也有時間向他討教學問。他每次總是非常謙遜,一直以「王先生」來稱呼我,而在言談不經意間會點撥我幾句,而又不給人留下他以長者的身份說話的印象。他曾告訴我,他為了治元明史,專門學過古蒙古語,所以他在研究過程中能閱讀古代蒙古文獻。這對我觸動很大,看來外語是做學問的前提。由於有近距離接觸陳先生的機會,對他的學問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陳先生的名文《「真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披露了明永樂皇帝大規模營建扶持的道教聖山武當山上的真武神塑像,帶有永樂帝本人的面貌特徵,從而顯示出永樂帝認為自己「靖難」登基有真武的佑護乃至自認為是真武下凡的宗教心理。而他1996年出版的中文書《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和2008年出版的英文書《老北京建城的傳說》(Legends of the Building of Old Beijing),神奇地向我們展現了劉伯溫依哪吒的形象建造北京城傳說的來龍去脈。這種對明史中神秘面向的探討,極大地激勵了我對從明史角度研究道教的信心。《「真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一文收入陳先生的《明代人物與傳說》。承蒙陳先生惠賜一本此書,至今該書是我對陳先生珍重的留念。
陳先生請我給中大歷史系授課,對我來說還有一至關重要的影響。我雖一直研究明代文學,對明代史實多少有些熟悉。但我從未正兒八經地研究明史。在歷史系教書,我有趕鴨子上架的感覺,心裡直犯毛,不得不臨時抱佛腳惡補。雖然教得蠻辛苦,但也收穫極大。我因此明白了我們學文學出身的人,瞭解的歷史只是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對歷史的典章制度是隔靴撓癢。也進而理解了過去人說二十四史最重要的是「志書」而非「列傳」,蓋對制度史的把握可以提綱挈領地對一個時代有總體的瞭解。正是在中大歷史系教明史的這段經歷,使我在學術上有了徹底的脫胎換骨,現在我會從典章制度的角度看待明代的道教。這都歸因於陳學霖先生的提攜和給我一個機會。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陳先生有關明代典章制度的一系列論著,舉凡《劍橋中國明代史》第4章「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明太祖與其諸子的關係、解縉(1369-1415年)為永樂帝篡改《明太祖實錄》的研究等,都成了我的重要參考文獻。前述拙著《明代王府與道教:一個精英層的制度化護教》,就是這樣一個從明代制度史的角度探討道教的嘗試,得到國際明史專家魯大維(David Robinson)教授的充分肯定,而其中我引用了陳先生論著達五部之多。
說起本人從事道教研究,必須談到道教學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先生。施舟人又名施博爾,法國人,祖籍荷蘭,是迄今為止對道教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也是當今歐洲三大漢學家之一。1962年至1970年他在臺灣留學期間,來到台南,學習閩南話,拜第63代天師張恩溥(1904-1969年)為師,又跟著陳榮盛道長的父親學習道教儀式,正式入道,是一名正一派受籙道士,最終成為一名師公,與陳家一起進行道教儀式表演。他對道教科儀、道教經典、道教人類學考察、道教史和道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等都有精到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有《道藏通檢》(Concordance du Tao-tsang)、《道體論》(The Taoist Body)、《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等,著作等身,不勝枚舉,堪稱現代道教學的「教父」,他的論著是道教研究者的必讀物。我除了收藏他的專著外,還用滿滿一紙箱,收集了他的論文。施舟人先生長期同時任法國高等研究院中國宗教教授和荷蘭國立萊頓大學中國歷史教授。他的學術職務與榮銜包括法國國家科學中心東方學主任委員、法蘭西科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荷蘭國立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法國榮譽騎士勳位。從2003年起,他又先後受頒中國福建省友誼獎、中國人民共和國友誼獎、「感動中國」國際友人。現又在主持由國家漢辦組織的大型國際漢學合作專案——《五經》的翻譯工作。
我早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時,就傾心于施舟人先生的著述。萬沒有想到,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就職後,居然有機會與施先生近距離交往。我是1999年1月到中大工作的,我所任職的中大宗教系以文學院人文科學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 Humanities Professor of the Arts Faculty)的名義請施舟人先生來中大從1999年九月至十一月駐校講學。施先生的太太袁冰淩博士是復旦歷史系79級畢業生,算是師姐,也對我能多與施先生接觸提供了幫助。在此期間,無論是施先生在中大演講,他在香港道教學院的講座,還是我們私下的聚會,我都有機會多次向他討教。嚴格來說,我真正走上道教研究之路的學術轉型,是施先生啟迪之下的產物。
在講述施先生對我的影響之前,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1976年九月,在巴黎的歐洲漢學會議上,施舟人先生提議成立一個研究計劃來研究《道藏》(Tao-tsang Project),這一計劃隨即彙集了歐洲幾乎所有漢學家,在他的主持下啟動。該計劃持續展開了二十幾年,終於到2000年,該計劃完成,以《道藏通考》為名交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考慮出版。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找的匿名評審就是余國藩師。余老師當時跟我講了這事,並十分欣賞,打算極力向出版社推薦出版該部巨著。本來這匿名評審制度,被評審作者不應該知道誰是評審者。但我還是很激動,想也無傷大雅,就私下告訴了施先生余老師是評審者。施先生十分高興,因為他知道余老師是內行,相信余老師的慧眼。2004年《道藏通考》出版了,並於2005年獲得了全美宗教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學術最高獎。2005年芝加哥大學東亞系舉辦了慶祝出版《道藏通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施舟人先生也去赴會。2005 年余老師也剛好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歷史與文本的角度》。余老師向施先生贈送了一部該書,施先生立刻在會議期間一口氣將之讀完,興奮地對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有許多其他學者不敢說的洞見。余老師事後很欣慰地告訴我,只要有這樣的知己,這就夠了,是他最大的滿足。這種頂級學者間的彼此賞識,非常感人,讓我體會到做學問中的人性關懷。
施舟人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廣泛的。施先生有次對我說,行政的事儘量不要擔任,這沒有什麼意思。但是如果系主任要我教各種課,不要推辭。雖然開設新課程很辛苦,但對我長期的學養積累是很有好處的。我正是聽取了他的告誡,在中大期間我先後或同時在宗教系、歷史系、語言文化系、中文系任教,開設了不少新課程。我也被迫開拓新的知識視域,這些對我都有很大的裨益。如前面說到的在歷史系開設的「明史」課,至今讓我受用無窮。
講到道教研究,記得我曾向施舟人先生談到我對明代道教的研究興趣,他當即說,「好極了!明代道教是那麼的重要。但現在研究明代道教的人是那麼的少。你是唯一一個研究明代道教的人。」我不敢說我當時對明代道教研究有什麼心得和成果。但施先生對我的鼓勵,卻讓我確定了對明代道教研究的方向。研究明代道教的確人數極少,結識施先生十五年來,我是沿著他所設立的典範摸索前行的。上面提到的拙著《明代王府與道教:一個精英層的制度化護教》,是長達十年研究的結晶,就是對明代道教的一個探索。就在今年(2014年)3月3日,施先生給我發電郵,褒獎了拙著,很多是前輩的鼓勵之詞,但有一句獎掖的話卻跟我受到的學術薰陶和研究進路有關,讓我感觸很深,我摘錄下來:「你對明代歷史的深度博學讓你發現了在明代絕對重要但實際上被忽視的道教史實的如此巨大的豐富寶藏。」從2011年六月至去年九月,我先後參加了在美國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舉辦的「明代地方宮廷」學術研討會和在法國濱海大學(Université du Littoral Côte d'Opale)舉辦的「紫禁城、皇宮和王庭:東西方皇權∕君權的象徵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好幾位中國和歐美的明史專家也都對我的研究表達了濃厚的興趣。我從事明代道教研究,這些年來幾乎在單打獨鬥中度過,沒有同行的交流,十分寂寞。施先生的話,是對我從史學角度研究明代道教的肯定。這是施舟人先生道教研究典範的激勵所致,也與陳學霖先生讓我有機會踏入史學的殿堂分不開。
施舟人先生對道教和中國文化的熱愛是舉世皆知的。他的名言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研究是世界大事,不能讓中國人獨立承擔。」而他對道教的尊敬也對我有深刻的影響。施先生具現了宗教學者對研究物件「同情性理解」的金科玉律。我近年來對茅山道教的研究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結。拙文《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和《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就是這種對道門內部關照的產物,也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而且,正是由於拙文《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茅山道院住持、江蘇省道教協會楊世華會長稱茅山道教的歷史需要重寫。
施舟人先生的典範,使得我對法國漢學家的道家研究心往神迷,因此我堅持閱讀這些法國漢學家的道家研究論著原文,不但讓我在道教研究上收穫極大,而且體會到法國學者的治學性情。與施先生的交往,開啟了我隨後與法國漢學家中的勞格文(John Lagerwey)、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德寶龍(Pierre-Henry de Bruyn)、戴文琛(Vincent Durand-Dastès)、方玲等道教學者建立了友誼。也為我領會法國道教學者的學術精髓提供了契機。我於去年十一月在上海道教學院的演講題目是「法國道教研究」。而今年五月至六月受邀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舉辦的「海外優秀學者講座專案」中,系列講座的題目也是「西方漢學——以道教學為中心」。名曰「西方漢學」,聚焦其實就是法國道教學者的研究。不僅講這些學者的道教研究成就,也談他們的品性、堅執與境界,讓復旦學生瞭解研究道教的法國漢學家是如何從對歷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一路走過來,闡發多元學術思潮的激蕩,實踐人文關懷,完善人性的巔峰狀態。
對我有影響和幫助的漢學家還有多人,本文並非是漢學史,對他們的介紹要留待其它場合。只是講到我從進復旦以來所走的路,章培恒師和上述漢學家塑造了今天的我和我的追求。在我學術上的逐漸積累和改進中,時時都銘刻下了上述前輩學者的垂訓和我對他們的感恩。這是我學術心路歷程中我最深切的感受。
原文刊於張安慶、楊植峰、任家瑜主編《1980我們這一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頁139-148。
關於作者:

王崗(Richard G. Wang),祖籍安徽壽縣,1962年出生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1984、1987),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文學碩士(1993),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哲學博士(1999),2004年至今任教於美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語言文學文化系和宗教系,著有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The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明代王府與道教:一個精英層的制度化護教,2012);Ming Erotic Novellas: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 (明代艷情傳奇小說:文化操作中的文體、消費與宗教性,2011);《浪漫情感與宗教精神——晚明文學與文化思潮》(1999)等。

